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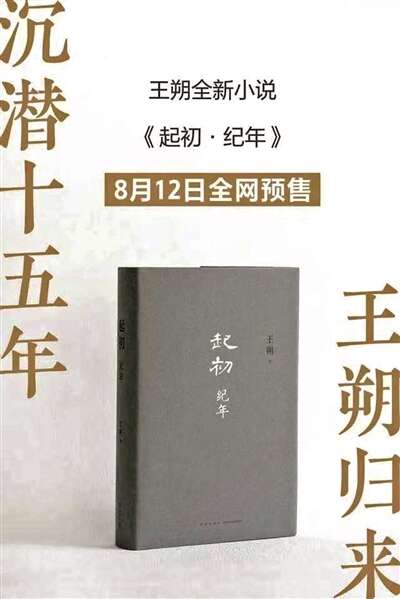
2015年4月26日,汪國真逝世。在一個群裏,同齡人紛紛發言:70後的共同回憶啊balabala……這讓我很尷尬,要不改身份證,要不退群。我選擇了後者。
誰也不是生下來就老了。年輕時候迷上誰都不是罪。只是(一)別自信到覺得自己的資訊繭房就是全世界;(二)都這麼多年了,還無節制地抱著青春回憶且無節制地表達,是不是太不思進取了?
王朔新書《起初·紀年》出版,造成了一時間的刷屏。想起有同齡的朋友勸我對王朔“手下留情”,因為朔爺啟蒙了他的青春——大哥,啟蒙了你的,沒啟蒙我的呀。再者説,朔爺多強大霸氣一主兒,他會在意你我晚輩留不留情?
作為當代文學研究者,我從不低估王朔的意義。在《傳媒時代的文學重生》裏,我將1997年定義為文學20世紀的終結點。那一年中國失去了三位“徵候式”的作家:4月王小波去世,5月汪曾祺去世,而1月,王朔去了美國。
王朔一直是一個外表張揚兇猛、內心靦腆悶騷的作者。他的巨大影響力,是個人與時代湊巧的結果。用流行的話説,王朔其實是很多當時苦悶壓抑的讀者的“嘴替”。風光無限的1990年代,也埋伏著時過境遷的風險。1997年王朔出國,對於他自己與時代,這都是一個終結。所以面對王朔的新作,咱們不必總沉浸在青春啟蒙期裏,就小説談小説好了。
看著熟悉與陌生交雜的王朔新作,我總想起日劇《孤獨的美食家》裏的主角五郎先生。五郎先生在都市裏尋覓美食,但他從不聽店家或專家的推薦,一切從心;旁人看上去,他都是在沉默地享受美食,偶爾抬頭看看周圍,只有觀眾才知道,五郎內心澎湃著萬般吐槽,千種驚嘆。而每一個觀眾,聽這些內心旁白時能否共情,又不相同,像我看五郎吃日料都是大寫的羨慕,但五郎去吃中華四川料理那集,看他一邊咕咚咕咚喝泡菜魚的湯一邊讚美川菜的辣,真讓四川人哂之不已。
王朔在《起初·紀年》自序裏説,他知道自己不擅長敘事,所以寫小説喜歡用對白——這自然勉強可以説是風格,但其實是電視劇本與綜藝臺本慣常的套路,主打是對話者自身的附加魅力。因此王朔早期作品能否引發共情的關鍵,在於讀者能否與他的人物産生認同感。《頑主》裏的于觀馬青楊重可以,《過把癮就死》裏的方言可以,但《千萬別把我當人》的唐元豹就不行了。離開人物的代入,王朔的貧嘴油舌,就會止于語言的狂歡。
《起初·紀年》將敘事動力交給了歷史,繁多支離的漢史資訊到處流淌,經過朔式語言改造的古人用對話交代漢匈的天下。王朔的野心是傍著自己曾經迷戀過的西漢世界,想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建立另類的歷史敘事。問題是,怎麼去代入一個話癆漢武帝與記錄者馬遷呢?讀者可能集體無語,而漢史研究者與小説評論家應該都會發出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
代入不代入,除去人設的親和力,更重要的是王朔要與讀者共同面對一個龐然大物。所謂“讓二老(老幹部、老百姓)都高興”,那就是一手弘揚真善美,一手消解假大空。王朔小説與他擔任策劃的《編輯部的故事》《我愛我家》不同,小説主打的是消解、躲避與戲倣。如果失去了共同針對的龐然大物,王朔小説就會像堂·吉訶德失去了風車。
失去了風車的堂·吉訶德下了馬,長槍一轉劃了個圈,他開始了賣藝!天哪,當騎士加入了馬戲團,觀眾是該失望轉身還是慣性喝彩?很多人年輕時將王朔當成屠龍的少年。很慶倖我從未如此想過,我知道他也是龍子龍孫——我們都是,只是有的後來化身取西經的白龍馬,有的始終還是馱石碑的赑屃。
我們要在《起初·紀年》裏看什麼?看王朔以學問代替文章嗎?看他承諾會加上的各類注解嗎?看出版方宣傳的“百科全書式寫作”嗎?百科全書……這是王朔該幹的事嗎?
還記得王朔的《我看老舍》,説老舍最好的小説是“一耍大刀的”“懷抱大刀,望著月亮自言自語:不傳,就是不傳!”但誰會指責王朔將“五虎斷魂槍”記成大刀呢?他以小説家的敏感,主張《斷魂槍》是老舍最好的作品,遠勝於一般人推崇的《茶館》,這才是重點吧。
覺得王朔變了的人也是想太多。五郎還是五郎,依然在從心地尋找合自己口味的食物。不如仔細想想我們還在期待什麼?為什麼期待?憑什麼期待?
我在2007年的長文《王朔六連拍》結尾,用魯迅的一段話總結剛剛推出《我的千歲寒》的王朔:“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十五年後,我比那時要寬容,或者世故。從字裏行間能感覺老王朔其實沒怎麼變,這是我願意去讀他這部750頁的長篇小説(接下來還有三部)的理由。讓白龍馬撒歡兒跑吧,王朔願意怎麼寫就讓他怎麼寫吧,畢竟他還不屑以作序與站臺為業,畢竟取西經只是唐僧的夢與責任,而奔跑與遊蕩,是時代給那些龍變成的馬唯一的自由。
2022-8-27
(作者係作家)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