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人小傳
唐弢(1913—1992),原名端毅,筆名風子、晦庵、韋長等。浙江鎮海人。作家,文學史家。16歲考入上海郵局任郵務佐,1933年起發表散文、雜文,曾參加1938年版《魯迅全集》編校。上海解放後,被選為郵政工會常務委員兼文教科長,後進入高校、文化部門工作。1959年,調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有《推背集》《海天集》《文章修養》《晦庵書話》等,編有《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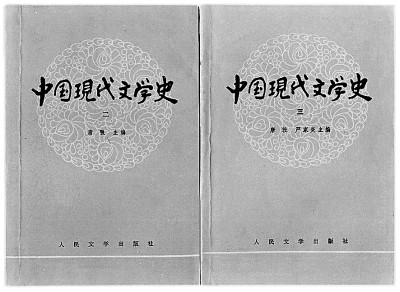
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圖片
【大家】
學術史上最令人心動的時刻,莫過於一位有積累的學者遇上了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唐弢轉向現代文學研究,恰值這樣一個歷史當口。
從鄭振鐸的遺願談起
唐弢赴京進入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故事,大概要從鄭振鐸先生的遺願講起。1958年10月18日,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鄭振鐸先生,在出訪途中,因飛機失事殉職。鄭先生生前有兩個未曾完成的願望:一個是他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古本戲曲叢刊》此時剛剛出到第四輯,而何其芳建議的《古本小説叢刊》,尚未實施;另一個就是調唐弢進京,主持文學所的現代文學研究工作。鄭振鐸為何如此信任唐弢呢?這恐怕與二人的治學理念接近以及在中共領導下的左翼文化界的合作經歷有關。
唐弢本名唐端毅,浙江鎮海人,中學時便因家境窘迫而失學,但憑藉刻苦自修考入了上海郵政管理局工作。唐弢的興趣廣泛,尤其對於野史雜著頗有心得,深受章學誠“六經皆史”思路的影響,對於文章的文脈章法也有細心的揣摩。20世紀30年代初,他投稿于《申報·自由談》的一系列文章,酷似魯迅的文風,迅速引起文壇關注,批判者將其作為魯迅的一個新筆名加以圍剿,稱讚者驚訝于作者文字的老練從容,這對於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説是莫大的榮耀。魯迅本人也注意到了唐弢,在第一次見面時,就戲稱:“唐先生寫文章,我替你挨罵。”稍後,魯迅注意到這個年輕人和自己相倣的閱讀趣味,意識到了這個年輕人溫和謹慎的外表下所包含著的和自己類似的熾熱情感與鮮明愛憎。在有限的交往中,魯迅給了唐弢極為坦率且有針對性的建議,如對自修外語的重視,對外國文學的有益補充,對長文章的駕馭和堅持,嘗試撰寫一部近代文網史,用現實的關切去引導和組織自己文史閱讀的重心和方向,自然也包括對當下文壇活動和人事選擇的斟酌……雖然在那個變動的時代中,這些建議並未能悉數落實,但對於唐弢的提升無疑助益良多。事實上,正是在魯迅的提點和關照下,到抗戰全面爆發前,唐弢已經成長為左翼文化陣營中一個較為成熟的戰士。對於三十年代的文壇,唐弢是親歷者,對其成就和局限都有切實的體悟,諸如此後對文壇和研究界影響深遠的“兩個口號的論爭”等問題,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中國人向來有“知人論世”的傳統,他在新中國成立後轉向學術研究,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特質,這種親歷者的優勢是其他研究者無可比擬的。不過唐弢當時並未加入左聯和中共,這同樣出於黨組織和魯迅等人的關照。根據徐懋庸等人的回憶,魯迅建議不要急於擴大左聯盟員的範圍,有些人留在組織之外,更便於在複雜的鬥爭中為左翼事業貢獻力量。黨組織和左翼為了應對特務的郵件檢查,多在郵寄信件和刊物時,請郵局的進步人士待檢查結束、郵包封口之際再將材料放入;而來信則用“存局候領”的方式,確認無特務發覺,再安排人領取。在這個過程中,唐弢等人作出了巨大貢獻。唐弢曾寫過一篇短文《同志的信任》,講到魯迅如何冒著風險保護和傳遞方志敏的信件和手稿,他説“魯迅先生不是中國共産黨黨員,可是,在所有共産黨員的心目中,他永遠是一個能以生命相託付的、最可信任的同志”——這樣的話,同樣適用於革命鬥爭時期的唐弢本人。
唐弢和鄭振鐸的交往在三十年代日漸密切起來。相對於唐弢的審慎週密,鄭振鐸更加熱情直率,所有的愛憎均展露無遺。鄭比唐年長十五歲,是名副其實的兄長,在進步文化事業中,兩人愈發接近。尤其是魯迅逝世後,許廣平、鄭振鐸、王任叔等人以復社的名義,主持《魯迅全集》的編纂工作,如此豐碩的著作,如此緊迫的時間,所有的審校者均是懷抱著對魯迅先生的摯愛義務工作,唐弢正是其中的一員。每天在繁忙的郵務工作後,他來到編委會默默地校讀,這個經歷也是唐弢日後從事魯迅作品輯佚及研究工作的開端。1944年,當魯迅北平藏書將要出售的消息傳到上海,為之奔走呼號最有力的是鄭振鐸先生,而受命北行去與朱安交涉阻止出售事宜的正是唐弢。這趟行程中,唐弢切實看到了朱安等人生活的窘境,聽到了其發出的“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要保存我啊”的吁求,也徹底看穿了以“贍養老母寡嫂”為名滯留北平的周作人的冷漠和慳吝。正如有的研究者注意到的,唐弢的文學氣質,實則介於周氏兄弟之間,從理智上,他欽佩和追隨魯迅的戰鬥精神,而文學口味則因其性情,更偏重於周作人的舒緩從容。北平之行在其情感上是一個分水嶺。唐弢的“弢”字,本義為“弓衣”,既有內斂平和之意,又有深藏其中的激情與鋒芒,在民族大義的激勵下,他愈發貼近於魯迅式的沉毅熱烈、鄭振鐸式的愛憎分明。
和鄭振鐸一致的,還有二人對於文獻資料的眼光和熱情。鄭先生在抗戰期間為民族搶救文獻的事跡盡人皆知,而唐弢這個“小兄弟”也在默默地貢獻自己的力量。當時有報道稱,在淪陷的上海,唯有兩個人在盡力收書,大手筆的是鄭振鐸,各類孤本珍本,無論是個人傾盡財力,還是靠社會力量提供支援,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買下來,使之免遭毀於戰火,流失海外;小手筆的是唐弢,受財力和所能夠調動的社會關係的限制,他的重點並非古籍珍本,而是新文學的期刊、圖書。那時,大量新文學圖書、刊物流入了廢紙收購站,而唐弢常常整日泡在廢紙收購處,完全靠著自己的節衣縮食,每天僅用兩個燒餅充饑,從中搶救出了大批期刊和書籍,如成套的《新青年》《小説月報》《現代評論》《文學》,部分“覺悟”副刊、“學燈”副刊,北平的《晨報》《京報》副刊等,以及大量新文學圖書的初版本。由於國民政府的圖書檢查制度,有些書籍期刊出版即被查禁,偶有流出的即為孤本;某些書局財力薄弱,發行渠道單一,圖書印量少,售賣範圍亦窄,能夠保留下來的數量極為有限——看似所收均為當代的刊物,但文獻的稀缺度、搶救的緊迫感,實則並不比古籍的蒐購要弱。此前,趙家璧主持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時,藏書家阿英的收藏確保了這一工作的順利展開。而唐弢,則是阿英之後,又一位對於新文學書刊的保存和甄別具有自覺意識和切實成就者。正是在這種大規模的資料搶救工作中,唐弢的文獻能力、版本意識遠遠走在了同時代人的前面。
鄭、唐二人不光都有收書的熱情,對於文獻價值的理解也頗有相通之處。鄭振鐸寫過《中國俗文學史》,在國內較早印行過民歌的集子,致力於雜劇和敦煌變文的收集和整理,也和魯迅一起刊印過《北平箋譜》等圖集,用唐弢的話來説,鄭先生是有意“從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觀點去研究歷史的”,唐弢本人同樣有此方面的自覺和慧心。抗戰勝利後,他開始書話寫作,除了重視闡發傳統的文獻學價值外,也極力保存相關歷史掌故,力圖將每本書所附帶的時代資訊、人文情愫保留下來,所秉持的較為寬泛的文學理念與鄭振鐸等人極為相似。前面提及的郵局文獻傳遞工作,唐和鄭更有長久的合作。據他們的密友劉哲民回憶,上海淪陷時期,僅鄭振鐸和藏書家張咏霓之間的通信便有三百多封,均和文獻的搶救整理相關,這些信件悉數由唐弢代為寄送,一旦被日偽查獲,株連甚廣。三百多封郵件,唐弢所冒的風險可想而知。鄭振鐸這位老大哥和唐弢這位小兄弟,他們的友情和信任,學術上的相通與理解,正是在中國革命鬥爭的試煉中,在中國現代學術的探索體悟中,牢固地建立起來的。
文學所的建立及其對中國學術道路的探索
鄭振鐸兼任所長的文學研究所成立於1953年2月。該研究所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先後挂靠于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但其工作方針的確定和高級研究人員的管理始終由中宣部直接負責,尤其是1958年後,文學所的政治、思想、業務均由中宣部直接領導,所從事的工作被納入了國家中長期科研及意識形態規劃之中。對該機構的系統研究目前剛剛展開,但此前已有研究者敏銳地注意到了社科院系統、作協系統和高校系統在新中國成立後科研實力的起伏消長。簡單説,隨著1952年的院係調整,新中國最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力量並非在高校,而是集中于社科院與作協,這種情況直到90年代才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據王平凡的回憶,《文學研究所計劃》中所列建所方針和任務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對中國和外國從古代到現代的文學的發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進行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整理和介紹。”研究所人員的構成,主要包括兩部分,一為如鄭振鐸這樣已經取得公認學術成就的名家,像俞平伯、王伯祥、余冠英、孫楷第、錢鐘書等,二為來自延安有著較好馬克思主義學養的知識分子,如何其芳、陳涌、毛星、朱寨、王燎熒等。至於具體的工作,1957年年末確定的在國家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需完成的七項任務講述得最為詳盡:1.研究我們當前的文藝運動中的問題,經常發表評論,並定期整理出一些資料;2.研究並編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數民族文學的多卷本的中國文學史;3.編選出一些中國文學的選集和有關文學史的參考資料;4.外國文學方面,研究各主要國家的文學,並將研究成果按照時代編出一些論文集,作為將來編寫外國文學史的準備;5.編訂漢譯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每部作品都冠以幫助一般讀者理解和欣賞的序文;6.研究文藝理論,並編寫一部較為通俗、結合中國實際的文藝學;7.編訂漢譯外國文藝理論名著叢書。
在這七項工作中,文藝時評和文學史是重點,而後者則要從資料的收集整理入手,前面提到的《古本戲曲叢刊》便是鄭振鐸等人于1954年開始陸續影印出版的,這樣的工作是此後文學所倡導的“大文學史”“學術型文學史”的基礎。調唐弢入所,同樣是一個切合文學所工作思路的舉措。此前他已在魯迅作品的輯佚、辨偽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書話寫作也獲得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評論文章更是漂亮之極,作為一個有著出眾資料功底的研究者,唐弢進入文學所,意味著那種重史料、重文獻,同樣兼重馬列主義理論指導的學術思路,從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貫穿到了現代文學學科之中。
從大的時代背景看,唐弢調入文學所恰逢新中國學術轉型的一個關節點。新中國成立之初,各類教材的編訂有著濃厚的“蘇聯模式”的痕跡,理論家日丹諾夫、畢達可夫的著作、季莫菲耶夫的《蘇聯文學史》給了探索現代文學教材的中國學者可資模倣的範例;同時,又由於現代文學史和現代革命史的高度同構性,更早普及的《聯共(布)黨史》同樣是文學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籍。1951年出版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朱自清等人開始的現代文學考察與蘇式教材書寫相結合的産物。王瑤以新民主主義理論作為闡述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基本邏輯,將文學分期與政治分期盡可能地加以協調;在各時段中,對於不同文體的發展情況分門別類地加以介紹。《中國新文學史稿》是現代文學史編寫的開山之作,也正是因為得風氣之先,所涉及的作家作品的體量具有此後各著作無可比擬的優勢。五十年代中期陸續出現的張畢來、丁易、劉綬松的著作,則向蘇式模板進一步靠攏,基本延續了蘇聯文學史中“總論+分章”“思潮+文體門類”“重點作家+普通作家群體”的模式。而這些著作中大量採用以革命史敘述代替文學文體解讀辨析的做法,無形中降低了文學史寫作作為一門科研工作的門檻,使之具備了批量複製的可能。
此後文學史的編寫進入“大躍進”狀態,一些高校的學生索性甩開專家教授自己動手編寫教材,這裡面最有名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和北師大中文系學生編寫的《中國民間文學史》《中國文學講稿》。這批著作存在極為嚴重的簡單化、概念化、庸俗政治化的傾向,而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則成為他們的重點批判對象之一。1959年年中,在文學所與作協、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聯合召開的研討會上,何其芳的發言極為引人注目。他以《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為題,明確提出一部文學史應具備三個基本特點:一、準確地敘述文學歷史的事實;二、總結出文學發展的經驗和規律;三、對作家作品評價恰當。在發言中,何其芳委婉但清楚地批評了上述文學史試圖用“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這組公式去概括複雜的文學現象所帶來的弊端,並以北大55級文學史為例,對該書中存在的概念混淆、評價標準混亂、脫離歷史苛求古人以及簡單套用馬列主義的表述、缺乏必要的歷史常識等問題均有具體説明。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何其芳提到文學研究所也有文學史的寫作計劃,但其目標是學術性的。
隨著五十年代後期中蘇關係的鬆動,編寫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學史被提到議事日程。主管部門有關領導提出,文學研究所的定位應著重于“提高”而非“普及”,要求文學所要“大搞資料”,建立從古至今最為完備的資料儲備。在1960年年初中宣部確定由文學所現代組負責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之後,這項工作並未匆忙開工,現代組的成員按照要求,對1958—1960年各地高校編寫的十幾部文學史進行了研讀和評述,對於本學科的發展概況做了全面普查。更為重要的是,唐弢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直接幫助下,邀請了茅盾、夏衍、羅蓀、黎澍、陶然等現代文學運動的親歷者來所座談,或介紹他們了解的文學運動的史實,或對如何撰寫一部文學史提出建議。這批作家學者所談內容使得編寫組中的那批年輕人深感震撼。如當年還是青年科研人員的樊駿在回憶中講到,夏衍在座談中一方面坦陳二三十年代所提倡的“無産階級文學”犯有“左傾”錯誤,另一方面也談到左翼運動能在國民黨的嚴酷統治下獲得蓬勃發展,應該在文學史編寫中有辯證的分析;歷史學家黎澍對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極為推重,而這部作品在新中國成立後實則並未引起研究界的重視;羅蓀提醒青年科研人員,文藝為政治服務,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何兼顧兩者的關係需要細斟酌……這些談話極大地拓展了編寫者的視野,也活躍了他們的思路,使他們認識到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所包孕的巨大的歷史文化含量——這展現了中國共産黨人實際具備的學理修養,也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現代文學的政治內涵和歷史品格。
作為文學史家的唐弢和現代文學研究“門檻”的確立
1959年秋,唐弢由上海作協調入文學所,擔任研究員和現代文學組組長。入所之初,他便向何其芳表示自己的心願,一是寫一本魯迅傳,另一個就是獨立編寫一部有特點的現代文學史。唐弢的經歷和知識結構與王瑤、丁易、劉綬松等一直成長于高校的知識分子不同,作為作家的敏銳的藝術感悟力和文字才華,作為藏書家對現代文學期刊、著作的精熟,以及作為現代文學親歷者對文壇歷史的理解和體貼,都使他成為編寫現代文學史的不二人選。不同於當時流行的“思潮+文體”的基本模式,唐弢有自己的角度,正如他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按我的設想,最好是以文學社團為主來寫,寫流派和風格”。但個人著史在五六十年代並非主流,而文學所又是一個具有示範意義的單位,很快個人寫史的想法讓位於文學所學術性文學史的集體計劃,但如上面提到的,這個夭折的項目在籌備期展現出來的視野和雄心仍然令人為之心動。
可事情很快又有了變化。1961年,周揚受命主抓高校文科教材建設,現代文學史的寫作是重中之重,唐弢及其團隊的骨幹成員無疑是最受信任的人選。無論是何其芳,還是唐弢本人,在經過短暫的躊躇後,他們的黨性原則使其堅決轉向了作為文科教材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誠如較早從事學科史研究的黃修己所言,為了編好這套教材,國家投入的力量是空前絕後的。唐弢為該書的主編,此前有文學史編寫實績的王瑤、劉綬松、劉泮溪等人悉數參與,而參加此書撰寫的中青年學者,如北師大的李文保、楊佔升、張恩和、蔡清富、呂啟祥、陳子艾、王德寬,文學所的樊駿、路坎、吳子敏、許志英、徐廼翔,北大的嚴家炎,廈大的萬平近以及華中師院的黃曼君等,多在日後成為該學科的關鍵人物。教材要求的是知識性與穩定性,它不必是最具探索性、先鋒性的,但必須紮實、準確,作家作品的評價要經得住推敲,最大限度地傳遞真實的歷史資訊。換言之,就著史的角度而言,這部文學史為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底線,或者説是現代文學研究應該有的“準入門檻”。
根據多位當年參與者的回憶,作為主編的唐弢與團隊成員共同確立了五條編寫原則:一、必須採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發表的期刊,至少也應依據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防轉輾因襲,以訛傳訛。二、注意寫出時代氣氛,文學史寫的是歷史衍變的脈絡,只有掌握時代橫的面貌,才能寫出歷史縱的發展。報刊所載同一問題的其他文章,自應充分利用。三、儘量吸收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個人見解即使精闢,在沒有得到公眾承認之前,也暫不寫入書內。四、復述作品內容,力求簡明扼要,既不違背原意,又忌冗長拖遝,這在文學史工作者是一種藝術的再創造。五、文學史盡可能採用“春秋筆法”,褒貶要從敘述中流露出來。
除了第三條是教材所不得不具有的保守選擇外,其餘四條均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也體現了唐弢等人建立現代文學研究技術標準的決心:熟悉原始期刊、回歸歷史場域,意味著文學史編撰歷史品格的回歸;從寫出作品的時代氛圍到梳理清晰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是唐弢一再提醒青年研究者“點、面、線”遞進的研究邏輯,既呼應了當時對文學文化發展規律的探索,也使得每一個判斷均言之有據。而對春秋筆法的強調則可避免簡單粗暴的政治批判,是對當時流行的“以論帶史”以至於“以論代史”編著方式的摒棄。正是因為堅持了上述原則,這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有正本清源之效,如開篇談五四文學革命,對胡適、陳獨秀的貢獻都有必要的肯定,由對李大釗、陳獨秀當年思想發展情況的考察,連帶出對五四運動的定性,這些問題處理得有理有據,展現出了極大的學術勇氣;對兩個口號論爭等敏感話題,也如實地敘述了論爭的過程以及積極和消極方面的影響,採用了魯迅主張的“並存”之説,體現了編撰者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深入理解。這部著作在最大的範圍內,將黨性原則和史家精神有機地統一起來,既旗幟鮮明,又言必有據,且措辭婉轉,給讀者留下了充足的思考推敲的空間。尤其是唐弢親自執筆的魯迅兩章,是全書水準最高、也最能體現出作者論從史出、含蓄蘊藉風格的章節,即使現在讀來,亦有歷久彌新之感。學術研究所依據的觀念多變,但學問本身永不過時。
作為寫過《文章修養》和《創作漫談》的唐弢,同時也是一位文體家,他重史料,但反對堆砌資料,要求文學史撰寫者以簡潔優美的筆觸去復述作品,批評褒揚,所用文字都要經得住咀嚼。很多人都回憶過唐弢對文字的講究,如吳子敏、藍棣之、嚴家炎所言,一個文題的設定,一篇文章的開頭,改易六七次極為常見,文字或大筆直寫、或精雕細琢,揮灑輕盈若行雲流水,偶有四六駢對,古意森然,所關注者均在文氣的自然流動,時時刻意經營,卻又力求無跡可尋之化境。當下我們強調的是學術的“研究”,古人相對更看重的是“文章”的分量,在唐弢,他是有意將兩者加以融合,如1956年所寫的長篇論文《魯迅雜文的藝術特徵》,是經得起郭小川在紀念大會上朗誦的,表演者感情充沛,所讀文本圓潤暢達,令聽者讚嘆不已——這種對學術論文的美文追求是唐弢的一份特殊貢獻,其立意之高,即使放在當下,也近乎奢侈。
唐弢本文學史的命運多舛,無須再行贅述。它的正式出版和普及已經是新時期以後了,那時,現代性的話語方式已取代了以往單一的革命視角,這部凝聚了唐弢及其助手無數心血的著作,註定只是一個“歷史的中間物”。不過它對現代文學學科的意義遠超出了文本自身,從某種角度講,這部書的編撰可以視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學者與第二代學者在學術方法和知識培養方面最為集中的一次交流,尤其是對第一手資料的強調和系統閱讀,使得參與此項目的年輕學者對於現代文學學科的家底和研究方法有了切實的了解,並在新時期推廣開來,“讀期刊”成為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必修課。而唐弢所看重的資料整理、社團流派研究思路,也成為80年代學科再出發時最可倚重的資源,前者有馬良春、徐迺翔、張大明主持的大型文獻項目“中國文學史資料彙編”,後者則有嚴家炎的《中國小説流派史》、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説史》等豐碩成果。從改革開放到80年代中後期,不到十年的時間,現代文學研究界的成果呈井噴之勢,在內容體量和對文學理解的深度廣度上都迅速趕上並超越了海外漢學界的成就,亦可看出唐弢等人學術思路所蘊含的巨大潛力。
我們今天討論唐弢學術研究的價值和貢獻,著眼點並非榮譽權的分配。我們應該注意到,唐弢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進步文化事業中的成長經歷,注意到他所在的文學所這個機構所負擔的使命,以及主管部門對他的信任和支援。唐弢把作家作品視為解讀時代的“點”,其實,他本人同樣是一個點,我們應該從他身上解讀出時代風雲的影響,梳理清楚他如何將個人的學術積累和興趣與探索中國學術道路的宏大命題結合起來,為現代文學研究從傳統中汲取資源,從現實中找尋依託。
(作者:冷川,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