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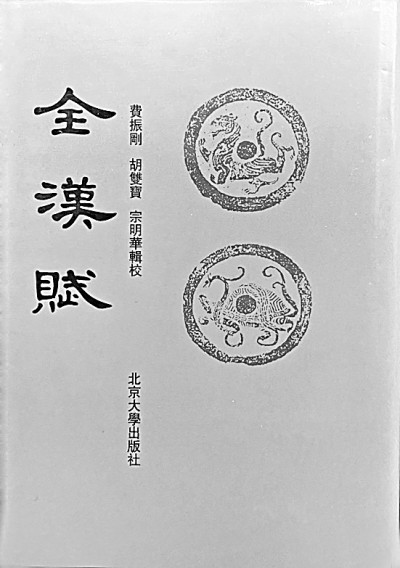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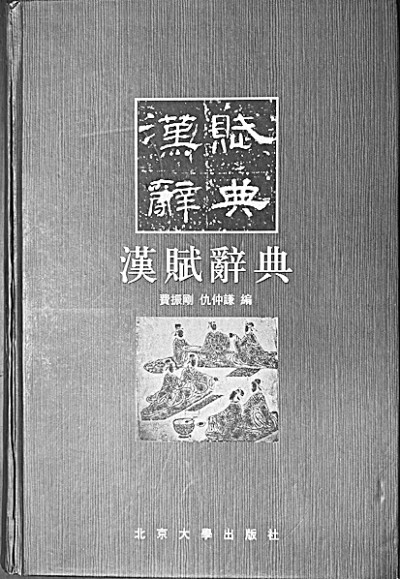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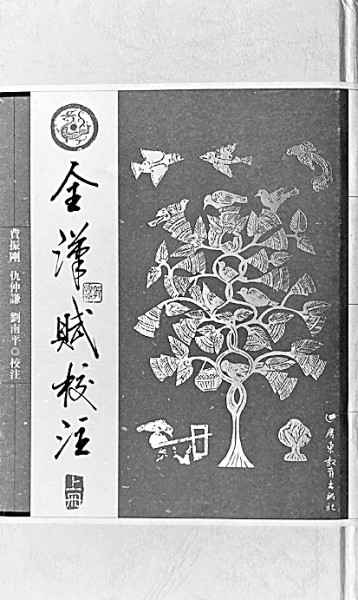
【述往】
費振剛,1935年出生,2021年去世,遼寧鞍山人。文學史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0年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學黨委委員。1958年至1959年,兩次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中國文學史》的集體編寫。1961年至1962年,參加全國高校文科教材《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為五位主編之一。還編寫、整理了《漢賦辭典》《全漢賦》《全漢賦校注》等著作。
業師費振剛先生長眠千山,倏忽已兩載有餘。兩年多來,先生的音容笑貌時在眼前,我常想,怎樣才能準確描述先生的道德文章?日前,再次聽聞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鳴教授説到先生“熱愛學生,敬畏學術”的八字準則,不禁心有慼慼,以為此言或許可以反映先生作為終身執教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師的風範。
作為北大中文系55級學生,先生先後參與兩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並成為其中的代表。尤其是與遊國恩等四位著名教授一起主編的部頒《中國文學史》,影響深遠,先生的名字也因此與之緊密相連。先生致力於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數十年,在《詩經》及漢賦研究等領域也頗有成就,只是多少有些被“文學史主編”的光芒所遮掩。
回顧先生教學、科研的歷程,細數其學術成果,漢賦研究,無疑是其學術重心所在。《漢賦辭典》《全漢賦》《全漢賦校注》三書,不僅是先生的名山事業,也展現了先生的學風與精神。尤其是暮年時節,先生對“重修增補全漢賦”的執著,頗有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悲壯之氣,更成為其視學術為生命理念的生動寫照。
教學相長,以教促研
對漢賦的評價,歷代一直存在著較大分歧。五四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是毀多譽少,漢賦研究並不受重視。1978年之後,隨著思想的解放,學界漸歸正途,漢賦研究也由簡單的概念化、標簽化轉向真正的學術探討。
先生是國內較早研究漢賦的學者之一。能夠從事漢賦研究,先生認為這首先是因為趕上了一個可以安心讀書做學問的時代。自1960年畢業留校任教開始,先生就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動蕩,直到“文革”結束後,才真正走上講臺。“作為一名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大學教師,如果不是新時期,我也很難把漢賦研究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我是燕園北大人》,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先生讀書的20世紀50年代,北大中文系分語言和文學兩個專業組,大三分組時,因對古典文學較感興趣,先生選擇了文學。留校後,先生擔任遊國恩先生的助教,在編寫《中國文學史》時,又執筆過《詩經》《史記》等部分,因此,教學及科研便主要在先秦兩漢一段。古代文學研究中,先秦部分研究較為充分,兩漢部分則相對薄弱,作為“一代文學”的漢賦受重視程度也不夠,結合教學需要,先生遂把漢賦作為研究的重點之一。
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先生就先後在北京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香港樹仁學院開設“漢賦研究”專題課,直至退休離開教學崗位。為使教學內容更具學術性、前沿性,解答教學中産生的疑惑,先生撰寫了一系列漢賦論文,涉及賦作為文體的産生、辭與賦的關係、漢賦的興起與發展等許多漢賦研究的緊要問題。
1981年,先生發表《漢賦的形成和發展》一文,敘述賦體的形成、發展及其特點,並分析漢賦産生的社會條件(《文史知識》1981年第2期)。因開設專題課需要確定課程的研究對象,1984年,先生撰寫《辭與賦》一文,辨析“辭”與“賦”的界限(《文史知識》1984年第12期)。2000年,先生又以《辭與賦的區分》為題,進一步申述“辭”與“賦”的區別(《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5期)。先生認為,從文體上説,楚辭是詩,以抒情為主;賦,雖間有韻語,總體來説是散文,最初當以狀物敘事為主。二者文體的不同,主要與其不同來源有關。
1990年10月,首屆國際賦學學術討論會在濟南召開,這是賦學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國際性學術會議,先生提交了《略論漢賦繁榮的社會背景》一文,從漢代社會發展的角度,探討漢大賦形成的原因。先生認為,一種文學樣式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潮,既有它對前代文學的繼承和發展,又受到特定時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發展的制約。漢大賦寫作高潮在漢武帝以後的幾十年間,司馬相如、司馬遷都産生在這一時期,並成為這一時期文化高度發展的標誌,“他們成就的取得,固然與自己的努力奮進分不開,而從另一方面説,又可以認為是時代玉成的”(《文史哲》1990年第5期)。
此外,先生還對重要的漢賦作家進行個案研究,以點帶面,剖析漢賦在不同時期的特點,研究其演變規律。先生曾撰文對枚乘、司馬相如、班固及劉安這四位重要的漢賦作家做了深入分析,此外還有《可悲的地位 可貴的人格——漫談東方朔》《梁王菟園諸文士賦的評價及其相關問題的考辨》等文章。先生在課堂上曾指出,漢賦研究中,對具體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夠,這也是“重寫文學史”呼聲雖高,但做起來難的原因之一。先生的這些個案研究,很有針對性,應當也是為編寫《秦漢文學史》所做的準備。
這些論文,角度不同,風格不一,但都為全面而客觀地評價漢賦,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意見。當日撰寫這些論文,先生並非出於“考核”的要求,而是與教學有關。先生的教學活動,主要在1978年之後的20餘年間。此時,高校中以論文數量、以期刊級別論英雄的做法尚未成風。教師普遍視教學為天職,信奉教學相長,教學與研究相互促進。終其一生,先生都把教學看作天大的事,也是最快樂的事:“師生相互論難,相互啟發,曲徑通幽,豁然開朗,我認為這是作為教師的最大樂趣。”1994年,先生接任系主任後,曾向學校領導做過一次專門彙報,回顧這次會談,先生説:“在中文系,作為一名教師,無論年長的,還是年輕的,他們都知道在上課之外,還要做好科研工作,要在一定的學術範圍內(這範圍有的是導師、領導劃定的,也有自己選擇的),勤加耕耘,做出成果。這成果看似與教學無太緊密關係,但它是教學工作的基石,是一名高等學校教師安身立命之所在……這種把學術等同於自己的生命、也看作是辦係的根本的理解是中文系幾代學人心血鑄造的寶貴財富,也是他們的共識。”“教師的本職工作是教學,教學的基礎和根本是科研,教師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這上面。”(《以不變應萬變——一次彙報會的回憶和現在的思考》)
今日看來,先生有關漢賦的這些文章,既非“核心”,也非“重大”,但它們都沒有游離于教學之外,也都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與“項目學術”“課題學術”,實大異其趣,不是“數量”“級別”等標準可以簡單衡量的。
十年一劍,三書立萬
最能反映先生漢賦研究實績的,無疑是《全漢賦》《漢賦辭典》及《全漢賦校注》三書。這皇皇三書,可以説是先生用三十載青春年華鑄就的偉業,也是他一輩子教書育人中“教書”部分的答卷。
賦是兩漢最為流行的文體,漢賦數量當不下兩千篇。但在漫長的歲月中,其中的許多篇章逐漸失傳,漢賦總集的編纂更是長期闕如。編纂一部漢賦總集,以反映漢賦的總體面貌,並便於研究之用,實屬必要。《全漢賦》的編纂,始於1987年春。經過數年艱苦爬梳,先生與胡雙寶、宗明華兩位先生一起,從浩瀚的各類文獻中輯錄出漢賦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約100篇,存目者24篇。1993年,《全漢賦》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斷代文體總集的新品種,受到學界推重和歡迎,“全漢賦”之專名,由此得到普遍認可。
椎輪為大輅之始。漢賦全集的編纂,具有開創性,想畢其功於一役,並不現實。“賦”之界定,“漢”之下限,一直就有許多不同意見。漢賦僻字、古字多,當時排版技術相對落後,在文字校訂方面,《全漢賦》也存在不少問題。這一點,先生從不回避。翻看2000年我選修“漢賦研究”時的課堂筆記,先生當時講的一段話赫然在目:“學術研究需要認真、仔細。《全漢賦》出來以後,(我)越看越害怕。本想提供一個研究漢賦的全面、準確的資料,但現在看,‘全面’談不上,‘準確’也難説,但有一點,就是都註明出處。”對一些公開的批評、商榷意見,先生不僅虛心接受,還心存感激。事過多年,2018年10月,先生舊事重提:“《全漢賦》出版後,獲得了學術同行的認可。但由於當時電子排版剛起步,工人操作不熟練,加之校勘不夠仔細,錯誤很多,也招致學術同行的批評。特別是廣西師範大學的力之先生,發表多篇文章批評《全漢賦》各方面的錯誤。力之先生也曾和我面談過,意氣勤勤懇懇,讓我十分感動!他的來信和一本標出問題的《全漢賦》,我仔細地讀過,珍藏至今,它是在學術道路上催我不斷自省、奮力前行的動力之一。”(《我是燕園北大人》)
《全漢賦》出版後,先生即不時修改,以期彌補缺憾。1995年,《全漢賦校注》被廣東教育出版社納入出版計劃,修訂進程為之提速。在接下來的近十年中,先生與仇仲謙、劉南平兩位教授合作,在充分吸收《全漢賦》校勘成果的同時,對其進行全面的勘誤、修潤和增補,並增加了註釋和歷代賦評。2005年,《全漢賦校注》出版,共收集兩漢賦作(包括殘篇)以及非賦名篇而實為賦體的作品,總計93家、319篇(含存目39篇)。今人能見到的漢賦作品,基本盡收於此。先生在《後記》中表達了自己的願望:“期望它能夠成為收錄完整、文字準確的漢賦文本,供研究者進行選擇、比較、取捨。我也借此答謝多年來讀者和專家對我和《全漢賦》的關切。”《全漢賦校注》以其收文完備、校勘精審,受到廣泛尊重和好評,基本上實現了修訂初衷。此書普及版《文白對照全漢賦》,也于2006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
早在輯校《全漢賦》之前的1984年,先生即與仇仲謙教授一起,著手編寫《漢賦辭典》。1988年冬,先生曾遠赴桂北,在南方陰冷潮濕的環境中,與河池師專(今河池學院)的幾位年輕教師一起爬羅剔抉,治棼理亂。先生認為,漢賦研究相對薄弱,對具體作品的註釋也頗有分歧,“我們便決定從基礎工作做起,在理解現有漢賦作品的基礎上,析出詞目,在斟酌取捨前人對漢賦研究、釋義成果的過程中,形成對漢賦中字詞的較為準確、恰當的理解。考慮到詞語的相承性,決定以辭書的形式出版。希望它不僅成為閱讀漢賦的重要工具書,也成為閱讀其他古籍的工具書”(《漢賦辭典·前言》)。1993年,先生在接受林慶彰教授訪談時重申兩書的編寫動機,表示主要還是為了給讀者提供一點幫助,希望“漢賦不受重視”的情況能有所改觀(《我是燕園北大人》)。
《漢賦辭典》收單字6170余個,詞目2萬餘條,字數115萬,為閱讀漢賦提供了極大便利,對學術界是一大貢獻。該書定稿于1989年,出版過程一波三折,2002年終由北大出版社推出。先生在《後記》中雲:“儘管這十多年來,社會有許多的變化,但我們不求聞達,不追求轟轟烈烈,只希望本著求真求實的學術態度,願意做一點學術研究的基本工作,為推動學術的發展盡一點心力,也為廣大讀者閱讀古書提供一點切實的幫助。”學術研究原本就是一份寂寞的事業,不是終南捷徑,“求真求實”的熱情,才是內生的驅動力。先生這番話,或許可以解釋,他為何如此不計名利,矢志於學術基礎工作。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前夕,先生在接受校刊記者採訪時感言:“我認為真真正正想做學問的人,就得靜下心來,規規矩矩地多讀幾本書,忘掉許多的功名利祿——少一分光鮮,多一分平淡,才能有收穫。”(《我是燕園北大人》)十年磨一劍,三十年專注于一事,先生用漢賦三書,踐行了自己的學術信仰。
老驥伏櫪,採山不止
與《全漢賦》相比,《全漢賦校注》總體品質有了大幅度提高,就其體例及內容而言,並無多大遺憾。然而,先生還是不滿意,仍決意繼續修訂完善,以期打造一個學術精品。“重修增補”工作,也成為先生晚年生活的重心,甚至可以説,是一種生命的寄託。
由於當日客觀條件所限,《全漢賦》及《全漢賦校注》所收範圍,以嚴格意義上的“賦”為限,所收篇目相對較少。但在漢代,與賦有關係的文體,尚有辭、頌、讚、銘、箴,以及連珠、俳諧文等,同屬於廣義上的賦作。此類作品存世數量亦較大,是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的文學寶藏,有待於進一步蒐集整理。基於這種認識,先生將“重修增補”的工作重點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新篩選底本,對已蒐集漢賦作品重加增補、校訂,完善註釋等;二是補充廣義上的漢賦,加以匯輯、校勘、註釋。最終目的,是將兩漢四百年間賦作集于一編,並加以精校精注,力爭為學界提供一個收錄完整、文字準確的漢賦全本、定本。
1993年,先生就對林慶彰教授談到自己的三項研究計劃:再編一本《全漢賦外編》、編輯《全漢賦譯注》、完成《秦漢文學史》的編寫。先生從北大退休後,受聘于梧州學院,那時他即著手《全漢賦校注》的後續工作。2006年8月20日,他致信北京大學詩歌中心申請工作經費,稱“希望通過這工作,對這裡的從事古代文學教學的中青年老師進行科研能力的培訓,也為深入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物質基礎”。2006年9月,“全漢賦外編”項目獲高校古委會立項資助,2008年結項,可以説這是“重修增補全漢賦”先期成果。
有六七年時間,先生往返北京、梧州及加拿大之間,過著“候鳥式”生活。即使在海外,先生也從未放下書本,時常讓我協助搜尋資料,並分享自己的發現和體會。我責編的影印本《唐代四大類書》,厚厚三冊,足足四公斤,先生也隨身帶去一套,用作常備書。
2009年6月,先生遭遇風疾,留下嚴重後遺症,右手再無法正常書寫。然而,還在康復之中,先生就重拾修訂工作,無論走到哪,都要把資料帶在身邊,考文校字,日復一日。師母等多次勸説先生,將已有的校訂成果吸收進去,做簡單的修改,出個修訂本收尾,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先生一直不為所動。在一篇序文中,先生説:“我還會繼續做我的《全漢賦》增訂修補工作……僅就寫作來説,《全漢賦》的增訂修補工作進度不快,但進展順利,且不時有一些新的認識。”(《我是燕園北大人》)2015年夏秋時節,先生又一次病倒,元氣大傷,即便如此,仍沒有放棄的打算。2016年4月,先生又命我與沈瑩瑩博士參與,一起申報“重修增補全漢賦”項目,幸獲批准,被列為2016年度高校古委會規劃重點項目。這對先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其時,先生已回故鄉頤養。在鞍山郊外、千山腳下孤寂的山村,陪伴先生日常的依然是“全漢賦”。那套笨重的《唐代四大類書》,也還在案頭。當我前去探望老師時,目睹此景,心中之情,無以名狀。但先生則樂此不疲,並充滿著期待。2018年10月7日,先生寫道:“2009年6月3日突發腦中風,限制了我的行動,但沒有影響我的思維。我仍在工作著。由於有了新資料的出現,我希望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增補版《全漢賦校注》,高校古委會、北大中文系在資金上提供了支援,又有兩位博士願意參與,我希望它能成為更新、更全面的漢賦研究資料和讀本。”(《漢賦概説·附記》)遺憾的是,我雖然按先生要求,做了些資料準備,嘗試著做過一些校勘、註釋,但未能堅持下去,先生的體力也日見其衰,這項工作最終沒有完成。每念及此事,我總有一種説不出的傷感!
從北京到梧州,到加拿大,再到鞍山,先生耄耋之年,還如此執著于《全漢賦》的修訂增補,在我看來,主要原因大概有兩方面:首先,是對學術的熱愛和敬畏使然;其次,是想回報北大,回報包括遊國恩先生在內的眾多老師的培養,傳承他們的學術傳統,這是先生植根心中的“北大情結”。在文章中,先生不止一次表達過這些想法;在對我耳提面命之時,先生也無數次講到這些話題。
對學術,先生其實遠不只是敬畏,更是一種宗教般的虔誠。2000年3月,在《北大中文系九十週年係慶感言》中,先生將中文系的發展比作在大河中行船,認為她雖經歷過不少急流險灘,但卻始終沒有沉沒,“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中文系人視學術為生命,以學術相砥礪,互相鼓舞、互相支援,努力使之停靠在平靜的港灣……我不願意看到把學術當成商品去出售,更不願意看到做學術的人在物欲或權勢的驅動下自己去糟踐學術”。2009年3月,在應77級同學之請而撰寫的《當噩夢醒來時》一文中,先生説:“作為知識分子和教師,生活的清苦,物質的匱乏,並不是最不堪忍受的事。最不堪忍受的是不允許我們讀書,不允許我們坐在書桌前思索和寫作,不允許我們上課堂為同學傳道、授業、解惑,更不堪忍受的是那些對我們思想、精神上的摧殘和折磨……我退休快十年了,還在盡力做著我喜歡的事,只要能做,我還要做下去。”生命不息,奮鬥不止,應該是先生這一代人的標簽吧?
對北大、對老師,先生常存感恩之心。對自己能成為中外知名大學的學生和教授,並擔任了中文系自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五屆系主任,先生如是解剖自己的心跡:“我雖然沒有以此驕人,但我的內心常常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也為此,我要感謝母校,感謝中文系,感謝給我以指導和幫助的眾多的師友!”在回答林慶彰教授提問時,先生也談道:“遊國恩及季鎮淮兩位先生是我請益最多的師長。遊先生曾勉勵我好好讀‘十三經’,言做學問首要之務是細究原典,認真讀書,他本人做學問重考證、訓詁、校勘,廣博精深,是我學習、取法的典範。季先生常不言自己是研究文學,而説自己是搞‘史’的,重視學術的先後傳承衍變,這亦成了我對自己做學問的要求。”(《我是燕園北大人》)從這段話中,我們也可以理解先生何以如此重視基礎文獻的整理工作。先生多次與我談到,自己的學問是“接著做”,是接著遊先生的楚辭做;並謙言自己不是好學者,但卻是好學生,要盡力將遊先生的學問傳承下去。先生所撰《遊國恩先生學術成就評述》一文,“表達對遊先生作為學者一生的總體認識以及我個人作為學生不忘師恩的感激之情”,包含著很深的感情。對林庚先生給予的指引、啟發等,先生同樣無法忘懷。在《林庚先生的學術個性》中,先生特意提到自己的漢賦論文,“都是在林先生的相關論述的啟發下完成的,有的還直接引用了林先生的論點。在文學史和漢賦研究的課堂上,我多次引用林先生的論述來説明相關問題”。
在《守望·題記》中,先生動情地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優良傳統會一代一代傳下去。‘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莊子的話,我堅信,也因此我不作‘今不如昔’的感慨,而寄希望於明天。”也許正是這種薪盡火傳的責任感、使命感,使先生猶如愚公一般,採銅于山鑄新器,直至生命最後一息。
以文會友,關注新賦
談到先生的賦學成就,有一點不能忽視,這就是先生所作的十幾篇賦評或序言。這些文字,一方面體現了先生的交友之道,另一方面,也是先生鼓勵賦創作、發表賦見解的一種方式。同時,這也顯示了一位古典文學研究者的時代關懷。
為人作序作評,或出於師友情誼,或出於慕名相求,其情不一,然先生皆本著以文會友的心態,將其視為探討學問之雅事。在文章中,先生也總會提及與作者交往的緣由等,以此作為“知人論世”的一部分。通觀先生所作賦評、序言,感覺不到任何敷衍之意,每篇皆精心傅會,實事求是地加以評説,以鼓勵為主,但並不溢美,也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通過這些文章,先生表達了自己希望賦這種古老的文體能煥發出新的生命,能見到更多反映時代生活作品的美好願望。“我以為較之詩詞,賦應該是更適合現代人來表現我們的時代,表達自己的心志的一種古典形式,應該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出世。這是我的期盼和祝願。”(《初讀〈若水齋賦〉》)先生希望當代人能夠從漢賦大家的寫作中得到啟發,把當代賦的寫作水準提高一步。
此外,先生也借此表達了對當代賦創作的一些看法。關於賦的題材,先生認為,我們的時代較之兩漢時代更富於變化,“我們當代的賦家也要以自己的心態去感受生活,以不同的題材或以不同的視角去表現這些。不應該囿于班固所論,把我們賦都寫成用於‘潤色鴻業’‘雍容揄揚’的歌頌體。當代的賦題材單一,‘好大喜功’,風格又缺乏個性,幾乎是‘千賦一面’。我以為要提高賦的創作品質,這是第一要改善的”(《初讀〈若水齋賦〉》)。關於賦的語言,先生贊同將流行的新名詞、口頭語等融入其中,以改變傳統賦語言的生澀古奧,使之更能為大眾所接受。先生的這些意見,十分中肯,對當下的賦創作,當不無指導意義。
先生早年,身經動亂,而不廢所學。暮年時節,以孱弱之軀,孜孜于《全漢賦》之增補修訂,永不言棄,大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令人感動。此項工作雖未能如願竣事,但先生的治學精神卻足可鼓舞后學,激勵來者。因撰此文,重讀先生華章,對先生為人為學有了更新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先生的形象亦愈加清晰可敬,然天人永隔,請益無門,思之情不自勝,唯有淚水潸然。
(作者:馬慶洲,係清華大學出版社編審)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