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尋文明根脈增強歷史自覺築牢自信根基
——“河套人”發現100週年國際論壇部分專家發言摘登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福友
2021—2022年薩拉烏蘇遺址的考古新發掘
2021年,為配合薩拉烏蘇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聯合進行了薩拉烏蘇遺址新的考古發掘工作,通過歷史地圖對比、科學文獻考證,結合新發掘的考古地層資訊,找到並確認了100年前法國學者首次發掘的舊石器文化遺址的具體位置,糾正了之前有些學者認為該處是王氏水牛化石出土地的錯誤觀點,為進一步的考古研究、文物保護和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證據,解決了長期困擾學術界的問題。
新的發掘對遺址的文化層和遺物的分佈有了比較新的認識,文化層也從原來認為是一個文化層至少增加到兩個,文物分佈的面積也擴大了,為遺址下一步的調查、保護、研究提供了方向。
新的考古發掘,採用當前最新的舊石器考古規範進行,用全站儀對出土遺物進行了三維坐標測繪,有了平面、立面的準確位置,為解決相關的年代測定和分析提供了科學依據。本次發掘出土了數量豐富的打制石器、骨角器、木炭、燒骨、動物化石,為研究舊石器時代薩拉烏蘇區域古人類的文化提供了翔實的考古材料,形成了準確的考古剖面,解決了文化遺物與地層的準確對應關係,為進一步的遺址年代測定、古環境分析等提供了統一的剖面。
新的考古發掘已進入第三個年度,已經在遺址地層測年、植物孢粉分析、木炭鑒定、動物化石鑒定、動物考古等多個研究方向分別取得了進展,為闡釋薩拉烏蘇遺址的全貌更近了一步。
薩拉烏蘇遺址新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研究剛剛起步,後續將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在各級政府的支援下,與國內外一流的科研機構和高校合作,將薩拉烏蘇遺址的考古調查、發掘與多學科的研究推向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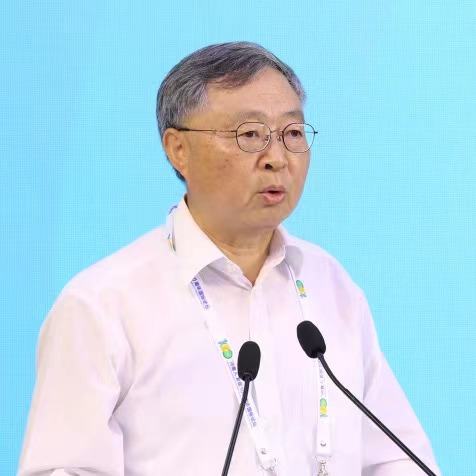
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 周力平
薩拉烏蘇遺址光釋光測年新數據與思考
前人曾經在薩拉烏蘇遺址開展過測年工作,但是這些工作往往缺乏足夠的資訊來對結果進行評估。近年來,測年技術的改進為更為精準的考古年代學帶來了新機遇。
2022年8月起,我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福友合作,對新發掘的薩拉烏蘇河流域范家溝灣和邵家溝灣地點的舊石器考古剖面沉積物進行系統的光釋光測年研究。
我們從沉積物中提取了石英和鉀長石礦物顆粒,分別採用藍光和紅外釋光測量樣品的年齡。初步結果表明,所採集沉積物樣品的光釋光年齡均在晚更新世年代範圍內。
光釋光測年是基於礦物晶體中缺陷、雜質能夠儲存電子這一特性的物理測年方法。礦物顆粒在堆積時受日光照射而被“曬退”,即晶體中儲存的光釋光信號被清零,也就是説這些礦物顆粒一旦被埋藏,就可以開始“計時”了。在之後漫長地質時期,礦物受到周圍放射性元素的電離輻射作用,將電子逐漸儲存在晶體缺陷中,並隨著時間而增長。在實驗室中,晶體受到藍色光或者紅外線的激發時,産生光子,發光強度越大意味著積累的電子數量越多,樣品的年齡越老。光釋光測年工作需要考慮測試所使用樣品的礦物類型及其粒級、激發的光源、礦物的穩定性等。目前,光釋光測年可以對於不同大小的石英、長石礦物顆粒進行年齡測定。
邵家溝灣和范家溝灣兩個舊石器遺址的測年結果顯示,石英和鉀長石的光釋光年齡有明顯差別,這可能與這些礦物顆粒在堆積時受日光影響程度不同有關,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影響造成的。分析這些新數據面臨新挑戰,不僅需要理解兩種礦物的差異,而且需要深化對兩個遺址複雜的沉積環境和沉積過程的認識。接下來的工作,任重而道遠,需要測年專家與考古學專家和第四紀地質學專家的密切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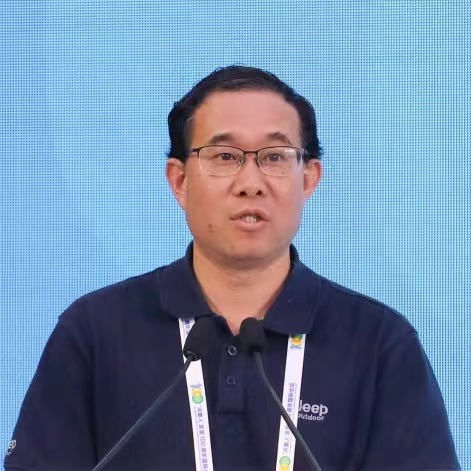
天津自然博物館古生物部館員 許渤松
薩拉烏蘇遺址的發現和早期研究
薩拉烏蘇遺址的發現者是法國博物學家、北疆博物院創始人桑志華,已成公論。但多年來學術界對桑志華首次到達薩拉烏蘇的時間、具體發掘經過、舊石器時代文化層及人類和動物化石出土層位等細節資訊或語焉不詳、或互相矛盾,對薩拉烏蘇遺址的後續相關研究及科普宣傳等工作均産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2021年,薩拉烏蘇遺址新的考古發掘工作重新啟動。我們依據桑志華留存史料,結合現場調查,厘清了相關資訊。
1918年5月,桑志華首次到達薩拉烏蘇,但未進行正式發掘。1922年8月7日至26日,桑志華在薩拉烏蘇河邵家溝灣進行正式發掘,出土大量晚更新世哺乳動物化石,首次在邵家溝灣A點發現舊石器,在J點出土人類牙齒化石。1923年5月,應桑志華的邀請,法國著名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到達天津,在北疆博物院整理化石期間,意外地從薩拉烏蘇1922年出土的動物化石中再次發現那顆人牙,後由步達生鑒定並命名為“The Ordos Tooth”,是中國境內出土的有確切層位記錄的第一件古人類化石。1923年的發掘以“法國古生物考察團”的名義進行,從7月31日持續至8月25日,桑志華和德日進分工協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確定了A點是一處“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居址”。從1924年至1927年,桑志華、德日進發表的與薩拉烏蘇遺址有關的重要論文共6篇。1928年,他們與法國著名古生物學家布勒、法國著名考古學家步日耶合作撰寫的《中國的舊石器時代》一書出版,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史上第一部綜合性學術專著,成為日後中國古人類——舊石器研究領域多學科綜合研究的範式。
桑志華和德日進在薩拉烏蘇的工作是開創性的,與當時其他地域取得的科考和研究成果一同構建起中國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第四紀地質學和古哺乳動物學等學科發展的基石。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 同號文
薩拉烏蘇動物群——“河套人”的親密夥伴
薩拉烏蘇遺址最早由法國專家桑志華發現,該遺址地理位置特殊,正好處於荒漠草原與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該遺址的出土物,尤其是哺乳動物化石十分豐富,因此,具有重要科學研究價值。薩拉烏蘇遺址記錄了歐亞地區古人類最早適應荒漠環境的生存行為,是研究人類進化及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歷史的重要場所。
薩拉烏蘇遺址發掘的動物化石發現于1922-1923年,是由桑志華和德日進主持發掘,在該批化石材料中,鑒定出34種哺乳動物。此外,還有1顆人類門齒及幾件層位存疑的人類肢骨化石。新中國成立後,國內專家也在此進行過多次考察和發掘,但新增加的動物群成員只有老虎1種。目前,公認的薩拉烏蘇動物群名單中包含了35種哺乳動物和12種鳥類。
儘管傳統的薩拉烏蘇組地層被進一步劃分為下部的薩拉烏蘇組和上部的城川組,但地質學家將這兩組地層所代表的地質時間段總稱為“薩拉烏蘇期”。因此,薩拉烏蘇河地區晚新生代哺乳動物群仍然可統稱為“薩拉烏蘇動物群”。
薩拉烏蘇動物群以野驢、野馬、披毛犀、羚羊、駱駝及跳鼠等荒漠草原動物為主,此外,還有諾氏古菱齒象、王氏水牛、原始牛及河套大角鹿等喜濕暖的動物,説明這些動物是在溫暖時期或者溫暖季節遷徙到本地區的。
薩拉烏蘇動物群不僅物種多樣性高,化石數量也很豐富,並且保存完整,有不少披毛犀和野驢的完整骨架,該動物群一直被視為我國北方地區晚更新世動物群的代表。
儘管薩拉烏蘇動物群的生物地層、人類活動證據及古環境問題尚存諸多科學疑點,但可喜的是,薩拉烏蘇河地區仍有豐厚的晚新生代地層,其中蘊含著巨大的化石潛在資源和大量的地質環境及考古資訊,只要我們持續在此開展科學考察和發掘工作,一定會有一系列重大發現和科研成果産出。

鄂爾多斯市政協一級巡視員 喬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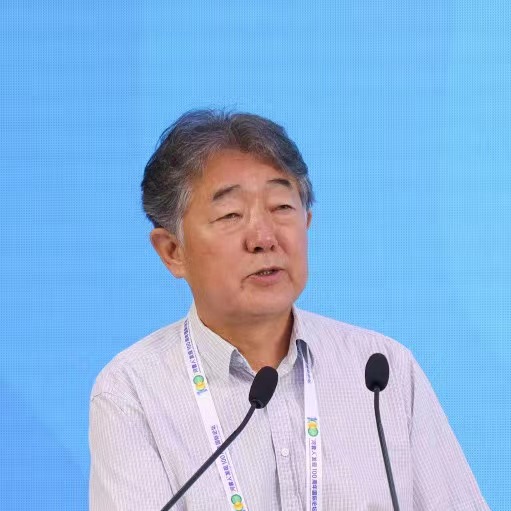
自治區文物局專家委研究員 王志浩
薩拉烏蘇遺址考古工作展望
100年來,中外科學家以巨大的勇氣和科學探索的精神,在薩拉烏蘇這個充滿神秘的地方開展了多學科的科學發掘、調查和科學考察活動,獲取了大量第一手的標本和資料,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將在探索古地質、古環境、古生物和古人類活動等方面發揮獨有的作用。
由於薩拉烏蘇遺址所蘊含的重要學術價值和其在社會發展領域所具有的重要社會價值,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業務部門高度重視對薩拉烏蘇遺址的保護研究工作,從2003年至今召開了4次不同規模的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和座談會,提高了其在國際國內的知名度,在學術領域的重要地位得到進一步認同;各級政府在經費等方面,不斷加大力度,使遺址的完整性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搭建起開展工作和科學研究、學術交流的平臺,建立了河套人文化研究中心和薩拉烏蘇遺址博物館,併為更好地保護利用進行了科學的發展規劃。
面向新時代,要依託河套人文化研究中心和薩拉烏蘇遺址博物館,進一步加強對薩拉烏蘇遺址第四紀地質、古環境、古動物群和舊石器時代考古等方面科學考察、考古發掘,綜合研究和展示等,使之形成持續性工作和研究狀態,不斷推出和展示新的研究成果,真正把薩拉烏蘇遺址打造成為具有世界人類共同價值的科學研究基地,考古研究教學實踐基地,公眾旅遊研學參觀的目的地和國際間學術交流的殿堂。

中山大學考古係副教授 劉揚
鄂爾多斯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精彩續章
鄂爾多斯地區是中國舊石器考古的重要發祥地,其中100年前發現和發掘的薩拉烏蘇遺址是中國最早發現既有大量舊石器又有大量哺乳動物化石,同時還出土了人類化石的遺址之一,在中國考古史上佔有突出地位,並揚名世界。
薩拉烏蘇之後,鄂爾多斯地區舊石器考古以2010年烏蘭木倫遺址發現發掘為標誌,開啟了精彩續章。近年來,該地區舊石器考古工作在考古調查、考古發掘與科學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進展。其中,烏蘭木倫遺址地理位置重要、地層剖面保存良好、人類遺物和遺跡豐富、時間節點關鍵,相關研究表明其重要性可以與薩拉烏蘇遺址相媲美。特別是從地層裏面發掘出土的完整披毛犀骨架和罕見肋軟骨化石,以及大型動物群腳印和植物遺跡化石面及其反映出不同動物的多種行為,具有很重要的學術和遺産價值。烏蘭木倫河流域調查和試掘發現的大量舊石器地點和石製品,極大豐富了對烏蘭木倫河流域古人類活動的認識。我認為,黃河(鄂爾多斯段)老階地舊石器考古新發現可能是目前鄂爾多斯舊石器文化的最早代表。
2022年,鄂爾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我們聯合,對鄂爾多斯東烏蘭木倫河流域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舊石器考古調查,發現舊石器地點99個,分佈具有一定的群聚成團現象;部分地點仍有原生地層;採集石製品近萬件,其分佈、構成保存較好,為進一步探討古人類行為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薩拉烏蘇遺址和近年來的舊石器考古新發現表明,鄂爾多斯地區的過去和現在都在中國舊石器考古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看向未來,鄂爾多斯地區舊石器考古潛力巨大,新的遺址和地點需要我們去發現,還有更多的考古材料和內涵需要我們去挖掘。我們相信,鄂爾多斯地區舊石器考古將會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績。

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舒培仙
晚第四紀夏季風邊緣的沙漠黃土過渡帶氣候環境初探
地球的氣候環境是具有多尺度週期性和突變性的複雜演化系統。氣候環境是多時間尺度上多圈層相互作用的結果。毛烏素沙漠和黃土高原交界過渡帶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乾燥,是受亞洲夏季風降水帶前緣區控制的環境變遷敏感地帶。這一過渡帶正地形上風成沙、黃土和古土壤在空間上犬牙交錯和時間上交互疊覆;而負地形的封閉湖盆上的湖相沉積呈帶狀或島狀分佈;過渡地帶的河流谷地、寬緩凹地則發育河流相沉積。
氣候地層記錄顯示,這一過渡地帶過去13萬年以來發生了44個沉積旋回的風成沙與河湖相和古土壤互為交替的演化過程,表現出巨大的千年尺度的氣候環境變遷歷史。古土壤同位素記錄發現,早全新世和中全新世該地區的降水——生態季節性發生過轉型。而來自動物牙齒的序列性同位素結果,初步揭示出薩拉烏蘇所在的沙漠——黃土過渡帶在不同背景狀態下季節尺度的氣候環境發生過顯著變化,影響該地區先民活動的生業方式。處在這一生態環境敏感地帶的薩拉烏蘇流域獨特的地貌起伏和斑塊多樣化的資源使其自古以來成為古生物、人類偏愛的活動生境。
未來在更多學科內外交叉,以及數據交叉和技術突破的支撐下,位於沙漠黃土過渡帶的薩拉烏蘇的氣候——生物——人類演化問題也許會在季節尺度視角上取得一些新進展。

中國岩畫學會會長 王建平
河套文化之石器時代藝術探究
“河套”一詞雖源自明代,但河套地區是世界古人類的棲息地和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確屬無疑。以石器時代考古材料而提出的“河套文化”首先出自裴文中先生上個世紀30年代所著的“中部舊石器時代(Middle Palaeolithic)——河套文化”一文,即“由桑志華和德日進發現、由步日耶教授加以報道”。由於當時的資訊傳遞滯後等諸多因素,埋藏在這裡的石器時代的藝術創作成果並未被引用到“河套文化”之中。事實上,在我提出的“泛河套文化圈”範圍裏,有著大量的、與歐洲的奧瑞納文化中發現的岩石藝術遺存。我依據相關資料統計,在“泛河套文化圈”的晉冀陜甘寧蒙一定區域,石器時代興起的岩石藝術總量達到全國總量的36%。
我們可以這樣思考:石器時代因為遷徙的條件所限,也因為薩拉烏蘇區域的動物繁多,可滋養人群,所以除了裴文中先生所講的“骨刻”藝術品,“河套人”在原發地利用的很多的木質骨質等材料刻畫了很多的“記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物件”無法抵禦風剝雨蝕,“偉大的藝術品”消失在曠野之中。過了萬年之久,隨著氣候的變化,人群追逐動物的遷徙而行,到達了有山有水的陰山和其他山脈,發現有大量的“畫布”——岩石可供記錄之用,所以,在陰山等山脈的岩石之上鑿刻下“偉大巨著”——岩畫。
今天談論、研究乃至傳播“河套文化”,應該在國內外專家學者等的考證基礎上,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黃河流域中華文明探源角度出發,以考古學、文化人類學、岩畫學和藝術史等發現中國的史前藝術遺存材料為依據,按照人類的共有文化遺産審視和研究其內涵與外延。在河套地區,在“泛河套文化圈”以充分的實證讓文物活起來。

北京週口店北京人遺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隗建華
數字技術開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未來
週口店遺址是著名的古人類遺址,位於北京西南房山區境內。在無數中外科學家們的共同努力下,才有了現在的這一世界文化遺産——週口店遺址。到目前為止,共發掘具有學術價值化石地點27處。其中發現了生活在距今70—20萬年前的直立人、距今20—10萬年前的早期智人以及距今3萬年左右的晚期智人化石,同時還發掘數百種動物化石、近10萬件石制工具和豐富的人類用火遺跡。迄今為止依然是世界範圍內更新世古人類遺址中內涵最豐富、材料最齊全和最有科研價值的遺址之一。
隨著高新科技在文博領域的廣泛應用,週口店遺址在數字化建設中進行了系統、全面、深入的思考和有效探索。
一是為遺址保護精準導航。建立週口店遺址動態資訊與監測預警系統,實現140個數據指標實時傳輸,累計3億多數據,並根據數據開展多項課題研究。二是實現公園管理運營智慧化。建立了完善的消防、安防系統,達到了遺址公園和博物館安全防控全覆蓋。三是開拓遺址價值闡釋新路徑。展陳更多地運用現代科技手段,並延長參觀路線,打造沉浸式體驗展廳,建設線上展示系統。靈活整合全景、三維、文字、圖像、音頻、視頻、連結等多種媒體形態,形成生動豐富的融媒體體驗,全面展現遺址博物館的研究成果與文化成就。組織實施夜景光文化展示,規劃打造週口店遺址文化IP,將凝聚人類情感和故事的虛擬IP形象打造成新型的文化傳播者。
我認為,數字智慧的公園管理運營模式是週口店遺址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發展途徑之一。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