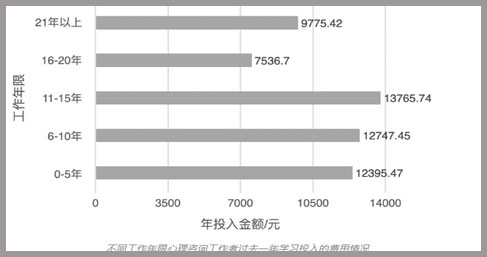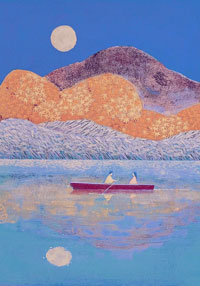漫畫家桑貝遺作探尋友誼的真諦:他的世界裏 一切情緒皆有落腳之地
發佈時間:2023-08-16 10:01:53 | 來源:北京青年報 | 作者:王勉


法國國寶級漫畫家讓-雅克·桑貝最新中文簡體版作品《所謂友誼:我需要陪伴,但我更渴望抽離》新近出版,書中有110組桑貝的原創插畫,還有他和好友馬克的3萬字訪談。在書中,桑貝清晰地揭露出當代人情感中擰巴又難以猜透的隱秘,浪漫中帶著犀利,清醒中不失溫柔氣度。他的新書畫風依然清新自然,給人以溫暖、純真、詩意、自由的感覺,他仍然是“美好”的代名詞,仍然是那個“最會畫春天的人”。
去年8月11日,桑貝去世,長眠于法國德拉吉尼昂市,享年89歲。桑貝在我國同樣擁有眾多讀者,在他去世一週年之際,本版特邀請畫家趙蘅、譯者黃葒和讀書博主袁泉談一談她們心中的讓-雅克·桑貝。
桑貝的故事
畫家必須看到所畫人的內心
19歲開始從事漫畫創作的雅克·桑貝,上世紀50年代中期與勒內·戈西尼合作了“小淘氣尼古拉的故事”系列,這部漫畫讓全世界小朋友為之瘋狂,全球銷量1500萬冊。而帶給無數人溫暖感覺的桑貝,本人的童年生活卻並不幸福,他的原生家庭生活拮據,繼父是個貧窮的酒鬼,時常醉酒回家引發家庭戰爭。小桑貝極度自尊,細膩敏感,他躲避家庭,喜歡學校生活,在學校裏,他堪稱孩子王。有一次,他看到一間教室天花板上的活板門開了,就慫恿全班同學爬到屋頂上,所有人都快活極了。
貧窮和並不和睦的家庭沒有令小桑貝沮喪,反而使他從小就擁有一種幽默反觀的能力。他曾回憶:“媽媽用力給我一巴掌,因為用勁太大,以至於我的頭也撞到了墻上,這樣我就像一共吃了兩記耳光。”
他還曾在自傳《童年》中描述快樂,並稱快樂是人之所以能活下去的奇跡,説那是“不可言喻、難以言表的東西”。
後來桑貝愛上了家裏的無線電臺,想從音樂中尋求安慰,甚至曾夢想成為一名爵士樂隊的成員,但是家裏沒有錢讓他去學習音樂。無奈的小桑貝無意中拿起了紙筆,他發現用簡單的紙和筆也能抒發自己的感受。他從12歲開始畫畫,賣出的第一幅畫作是無家可歸的小狗在大雨滂沱中拖著一口鍋。
14歲時,桑貝因不守紀律被學校開除,開始打工謀生,他參加過各種工作考試,但都沒有通過。19歲時,桑貝揣著他所有的“積蓄”來到巴黎,在這裡他第一次看到了美國的《紐約客》雜誌,由此産生了為《紐約客》畫畫的願望。
1978年,桑貝為《紐約客》畫畫的願望得以實現。此後他為這本雜誌畫了100多個封面插圖,這對《紐約客》來説也是史無前例的。《桑貝在紐約》中講述了桑貝與紐約的故事:只會兩三個英語單詞的桑貝住在紐約,即使有人大喊“著火了”他也聽不懂,但他喜歡這裡的每個人都幹著自己喜歡的事。同時他也談到,在紐約會特別感到人的渺小。
在大都市的生活經歷或許強化了桑貝的繪畫風格,他喜歡畫小小的人物置身於空曠寂寥的環境中,在平淡簡單的生活中偶現詩意的瞬間。桑貝認為“畫家必須看到你畫的人的內心,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藝術家——或一名優秀的幽默家”。
或許正是這份自我意識中深刻的幽默,使接觸桑貝的人都為之喜悅溫馨,上海譯文出版社桑貝作品系列責任編輯黃雅琴曾在一篇題為《一想到桑貝,我的嘴角就忍不住上揚》的文章中説:“桑貝系列是我迄今為止編輯生涯中做得最開心的一套書,是的,一定要用最高級,而且沒有之一。責編過的其他作家可能很偉大吧,但純粹的歡樂屬於桑貝。”
40後畫家趙蘅與桑貝
桑貝畫出了法國人的特質和法國式的風情
桑貝在畫家趙蘅這裡,也是如此一般快樂的感覺,雖然她説自己接觸桑貝很晚,而且至今還只算是個門外漢。
“第一次接觸是在一次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在一個童書大廳裏,花花綠綠的繪本堆得像小山一樣,孩子們和家長都在興高采烈地挑選著,桑貝的作品一下子跳入我的眼簾。”雖然書名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但那生動可愛的畫風卻令趙蘅過目不忘。後來,趙蘅把博覽會上購買的桑貝書送給了心愛的孫兒。
趙蘅認為只説桑貝是漫畫家不夠準確,“因為他對連環畫、插畫都在行拿手”。《所謂友誼》是桑貝留給世人的最後遺作,題材是不可或缺的友誼話題,趙蘅在一口氣讀完3萬字對談後,想向桑貝表示深深的敬意!
“書中的故事雖然發生在法國巴黎,但那些人際上的種種事端,人們的喜怒哀樂、小肚雞腸,以及獲得真誠友誼的幸福感,幾次看得我忍不住發笑。”趙蘅説太喜歡這樣的幽默感了,雖然是法國式的,但帶有普遍性,親切、輕鬆、滑稽極了。
作為畫家同行,趙蘅自然格外留意作者的畫技。她看到桑貝的鉛筆、鋼筆線條行雲流水,水彩畫面淡雅,絕少濃重色塊,看似漫不經心的塗色中卻有光感,畫出了城市的光線和空氣感。“他的人物造型也非常靈動,常常只是簡單幾筆就交代得清楚明瞭。”趙蘅最看重的是桑貝畫出了法國人的特質和法國式的風情。
“桑貝有一幅畫,畫的是他自己,在向書架上作家著作脫帽致敬。那是一幅鋼筆畫,只有致敬者的衣著涂了墨色。屋外熙熙攘攘,唯有他一個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趙蘅感慨,他是如何想到這樣畫的,他表達出的敬畏心情讓我深受感染。
桑貝談友誼,也是令趙蘅深有共鳴的話題。“這是一個恒常的話題,友誼對任何人都不可或缺,我今年78歲了,依然如此。”
趙蘅不記得“友誼”一詞自己是何時意識到的,好像與生俱來。小時候愛唱的那首兒歌“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個朋友/敬個禮,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邊唱邊帶舞蹈動作。她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媽媽到幼稚園接她,她正和小朋友特別認真地在唱這首歌,一見到媽媽,立馬紅漲了臉。趙蘅一直為此奇怪,在家人面前反而害羞?或許友誼要伴隨著成長吧。
獨不是孤,想明白了這點,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幸福感
談起自己經歷的友誼故事,趙蘅三天三夜也説不完。
“1956年我和父母到德國,認識了猶太女孩瑪麗,她大我兩歲,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57年趙蘅一家回國,瑪麗到萊比錫火車站送行,車開了,她還追著列車跑,誰也沒想到兩個小夥伴這一別就是39年。1996年趙蘅才又回到歐洲,多方打聽瑪麗一家的下落,最後通過父親的一位德國學生找到了,瑪麗已搬到柏林。趙蘅好不容易撥通了電話,喚了一聲“瑪麗”,電話那端馬上問是“Heng”嗎?趙蘅激動得很:“這種感應太絕了!它讓我深深相信真正的友誼不會因時空變換而隔斷。”後來兩個昔日的小姐妹見面,趙蘅發現瑪麗表情、神態都未變。
趙蘅和桑貝《所謂友誼》一書的譯者黃葒,也是見面不多但能心心相應的朋友。“黃葒的名字還是我媽媽先告訴我的,她們倆都搞翻譯,我媽媽常説她是才女。”今年春天在南京,趙蘅去拜訪過黃葒頗具法國風格的家,那長滿花草的露臺,讓她深為黃葒的生活態度所感染。
趙蘅相信真正的友誼可遇不可求,是冥冥之中的天賜。“上個月我去漠河采風,在開往哈爾濱的列車上遇見一位宋女士。我搭錯了車,她坐錯了位子,這樣我們就認識了。”在車上兩人畫畫加微信,車未到站已像久違的朋友。這一次的相遇讓趙蘅想到歌曲《傳奇》中的表達:“不僅有愛情的奇遇,更有友誼的魅力,因為追求美好是大家共同的動力。”
朋友之間,桑貝認為最主要的是忠誠、克制、尊重,他特別強調尊重,這一點趙蘅同樣贊同,她還想加上包容和默契。“在漢語裏有好多詞彙,比如暢所欲言、無話不説、話不投機半句多等,其實都是相對的,任何關係都需要有克制。我也經歷過背叛,受到過偏見和曲解的傷害,痛苦過,心碎過,但回顧大半生,更多獲得的是感動和溫暖。”趙蘅的話透出人生艱難,無人易過,人人都需要友誼,“我堅信人間自有真情在。我對中國舊傳統的一些習俗,如明哲保身、自掃門前雪等處世哲學,一向有保留看法,尤其反感冷漠”。
趙蘅對桑貝渴望陪伴又需抽離的主張特別有共鳴。“再好的陪伴,也需要保有自己的空間。”她的母親楊苡先生生前喜歡説“我享受孤獨”,她為了有一點兒獨自的空間和時間,寧可讓住家阿姨下午去鄰居家做兩小時工,她用這段時間看書、看譯製片,東摸西摸做自己的事。“她每天還都睡得很遲,因為捨不得這段沒有干擾的時間,她要在這段時間裏隨心所欲。”趙蘅認為媽媽是既需要陪伴也需要抽離的典型,她非常理解。“我也獨居30年了,同樣一直這麼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我説的獨,不是孤,想明白了這點,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幸福感。”
70後譯者黃葒與桑貝
他讓你世界分明,內心豐盈
黃葒是《所謂友誼:我需要陪伴,但我更渴望抽離》一書的譯者,她説自己的翻譯過程非常愉快,有一種偷著樂的感覺,雖然是出版社推薦的選題,但她也真的喜歡。翻譯桑貝,還勾起了她的某些回憶,讓她聽到了自己內心的某種回音。
桑貝畫過一個農場,女主人騎著自行車,她養的一隻母雞跟著她,一路跟到了集市,還陪著女主人賣了它生的蛋。黃葒因此憶起從幼兒園到高中生活過的松陽小縣城。“縣城特別小,群山圍繞,每戶人家都養雞養鴨,我們家也有一隻母雞,那只母雞不知道是不是基因突變,長得特別高大,像公雞那樣雄赳赳氣昂昂的,特別自信。它可能覺得自己特別美,所以特別喜歡見客,也特別喜歡出去玩兒。我當時還在上小學,這只母雞經常陪我去上學,送我到學校後它還會自己回家。”黃葒説,讀桑貝的文字時,自己很容易地想起了當年的母雞夥伴,感覺閱讀的是別人,其實説到底閱讀的是自己。
還有一幅插圖,黃葒也覺得特別有意思。“有兩個場景,這邊是一扇窗,窗裏邊是女主人和她的一隻貓,人和貓都是陰鬱的樣子。窗外則是男主人跟他的狗子,歡蹦亂跳地在院子裏玩,然後女主人跟貓講:‘沒什麼好羨慕的。’”這無疑是一幅幽默畫,它可能讓人想到夫妻間的關係,也可能讓人想到貓和狗之間的關係,還可能令人想到其他的文學作品。黃葒想到的是法國女作家科萊特的《動物對話》,因為科萊特也是用了動物視角去講述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故事。
“讀桑貝是快樂的,他讓你想到自己,想到其他的世界,你會覺得世界分明,內心豐盈,外面的世界也一下子變得豐盈了。”黃葒認為《所謂友誼》拓寬了友誼的邊界,也涉及了動物,“因為人和動物之間除了養育的關係,很多時候還有陪伴的責任”。
維繫友誼,桑貝説要靠言語,但話要少
黃葒理解桑貝,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都屬於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不願意受到打擾,需要一個相對安靜、可以安頓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但人又是脆弱的動物,不能永遠生活在孤島當中,所以在創作之餘,又會喜歡呼朋喚友,這也就是人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黃葒説:“通過桑貝這本書,我們可以更好地看待友誼,真摯的友誼也需要相互磨合,然後達到最舒服的距離和度。”採訪者馬克是桑貝的好朋友,他的有些問題提得挺尖銳,比如問桑貝在現實生活中有沒有絕交的朋友?什麼樣的朋友他會絕交?黃葒覺得通過閱讀他們的對話會給人以警醒,如何去維繫友情?
在黃葒的經驗中,時間和空間都不影響友誼,某種程度上友誼像石頭投到湖裏産生的漣漪,一圈圈泛過去,使人的交往更加廣闊。黃葒有一位10年奔現的插畫師網友,她們因為互相欣賞,所以微網志互關,説起10年相交的第一次見面,那份欣喜似久別重逢。
黃葒記得,馬克問桑貝友誼靠何維繫時,桑貝的回答很簡單:“桑貝説‘要靠言語’,後面一句話更重要,他説‘話要少’。”這無疑是桑貝的真知灼見,“因為言多必失是確實的啊,尤其是在爭吵的時候,你一句我一句步步緊逼,真真的就把友誼逼到了死角”。在桑貝看來,很多友誼某些時候你認為是一種背叛,但過後一想人生漫漫長路他也值得原諒。“走過的很多坎坷,對人生都是一種歷練。”黃葒説。
黃葒家裏有一個露臺,被她打造成了空中花園,那裏是她獲得抽離的地方。尤其在疫情期間,獨處的時間更多,她的露臺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她的一個孤島,她在那裏獨處,卻並不封閉,“因為我有非常多的天線,會跟各地的人連接”。
黃葒有一株檸檬樹,十幾年只開花不結果,疫情時候居然結了果,而且結了七八十個,“這成了我最大的抗疫物資”。去年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黃葒在菜場買了老菊花腦,把它們扦插在花盆裏,居然插了鬱鬱蔥蔥一大盆。物資實在匱乏的時候,她就去摘菊花腦,打上兩個蛋,做一碗清香的菊花腦蛋湯。吃到口中特別清香的湯水,更讓黃葒認可無論什麼樣的環境,生活都會給你開另外一扇窗,而友誼也同樣如此。
90後讀書博主袁泉與桑貝
他的體內住著一個沒有長大的男孩
袁泉是一位90後,畢業于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她通過桑貝的《童年》認識了立體的桑貝。她曾經臨摹《童年》中一幅小男孩騎車摔倒的畫,覺得非常迷人,臨摹時她仿佛感覺到桑貝體內住著一個沒有長大的男孩,之後她收了桑貝所有的書。
袁泉在小紅書上做讀書博主,開始時發現平臺上分享桑貝的人很少。桑貝去世當天,袁泉坐地鐵時看到了微網志推送,忍不住號啕大哭,涌上心頭的感慨是“能和大咖們同一個時代,呼吸同樣的空氣,是一件多麼有機緣的事情,而現在他去了”。那一個上午她都沒辦法辦公,哭著在辦公桌前寫了一篇推文,下午發現推文的閱讀數爆到了70多萬,“原來有那麼多人關注著桑貝”。
桑貝的每一本書都會讓袁泉喜悅得笑。她也特別認可黃葒的翻譯,覺得“她把法式的浪漫幽默、點到為止的那種感覺,翻得特別好”。其中有一句袁泉特別喜歡:“馬克問桑貝友誼總是很脆弱,你是否有點懷疑它會天長地久?桑貝説我毫不懷疑,它非常脆弱,就像我不懷疑水晶的純粹,但水晶也非常脆弱。”袁泉喜歡其中的畫面感。
友誼作為當代人情感需求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袁泉也感受到與之相伴的陪伴和抽離兩面。袁泉感慨,自己正在30多歲,處於人生爬坡的階段,生活中每個階段都會認識新朋友,但也總會平白無故地和一些朋友疏離再見。
“我是2008年來北京的,説實話,在北京真正好的朋友沒幾個。最早來北京認識的朋友都已經去了其他城市,之後有一段時間我的朋友來自於一起健身的,但當我腿受傷長達兩年無法健身時,和那些朋友也沒有交集了。之後追星,有一些共同愛好的朋友,現在沒時間做這事了,也就散了。”袁泉對此無奈又好奇:“如果我一直留在北京的話,身邊會留下來什麼樣的朋友呢?”
或許袁泉在桑貝的書中已經找到了某些答案,正像桑貝之前聊過童年,聊過巴黎,留給世界的遺言卻是聊友誼。他曾經説因為對友誼太過看重,所以一直不敢深入。而桑貝一旦談友誼,就能讓每個人從中看到自己,那種欣然的閱讀感受,會讓人感覺仿佛找到了知音。對於生活快節奏的當代人來説,桑貝的鬆弛感以及對生活的觀察和哲性的思考,或許更加珍貴。
(記者王勉)
藍皮書報告 | 2022年心理諮詢工作者職業狀況與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2023-08-16
嚴重拖延影響身心健康 孩子的三類拖延問題這樣解決2023-08-16
高校學生人生意義感略低 國民心理報告給出建議2023-08-16
運動成癮有害身心健康!修訂版量表適用於我國大學生2023-08-15
鄉村小學生問題行為突出 父親教育投入有助於保護學生心理健康2023-08-15
藍皮書報告|“雙減”政策實施後中小學學生心理健康影響因素的變化分析2023-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