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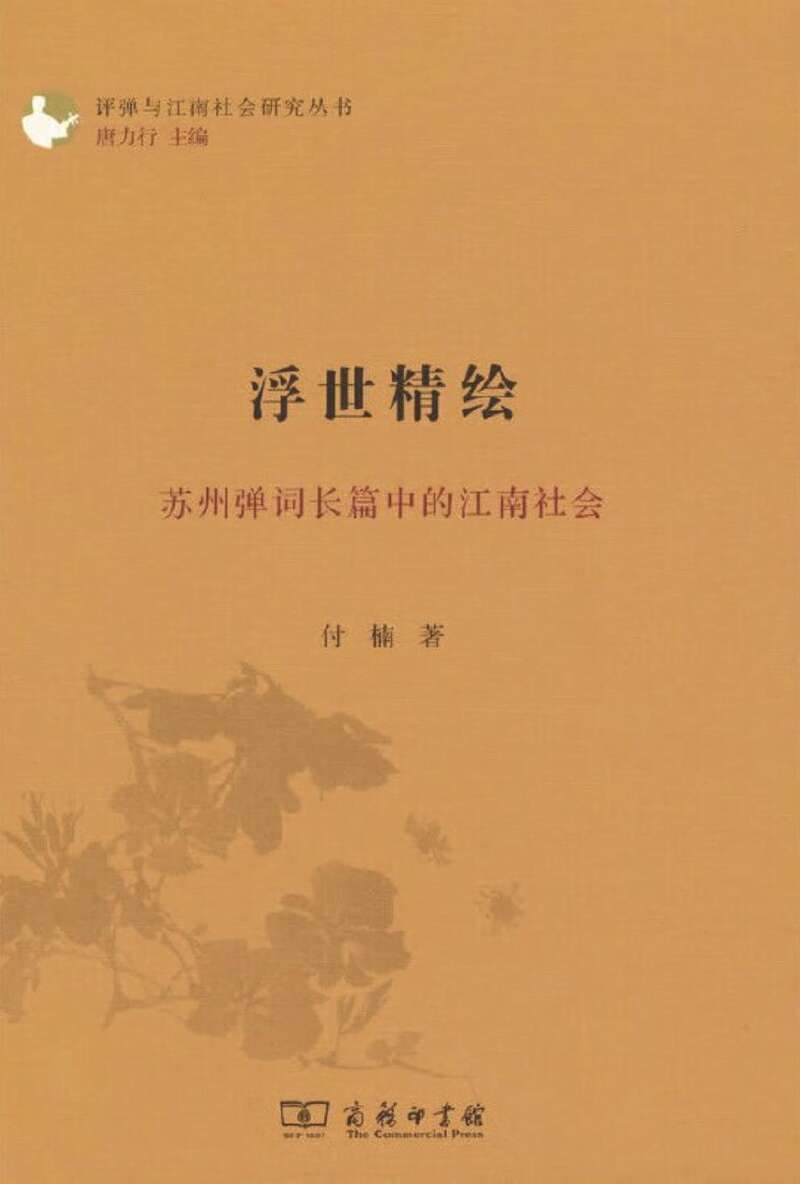
《浮世精繪:蘇州彈詞長篇中的江南社會》 付楠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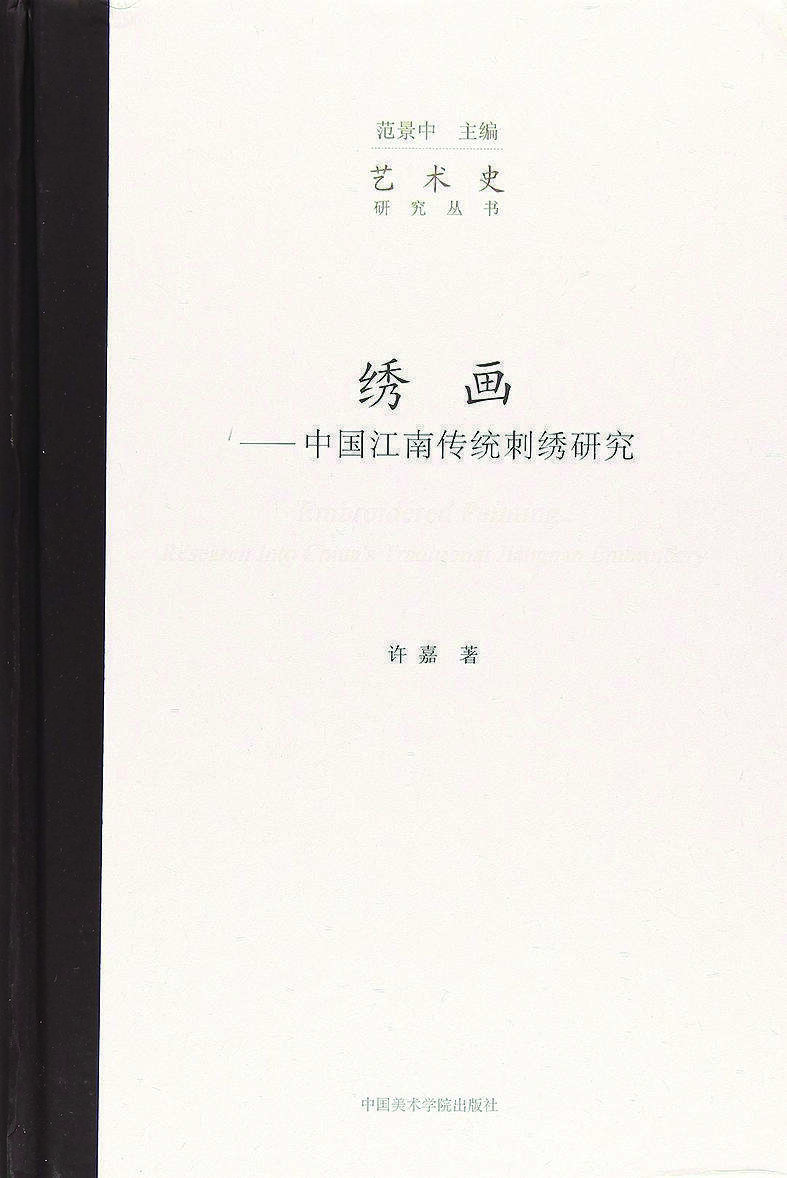
《繡畫——中國江南傳統刺繡研究》 許嘉著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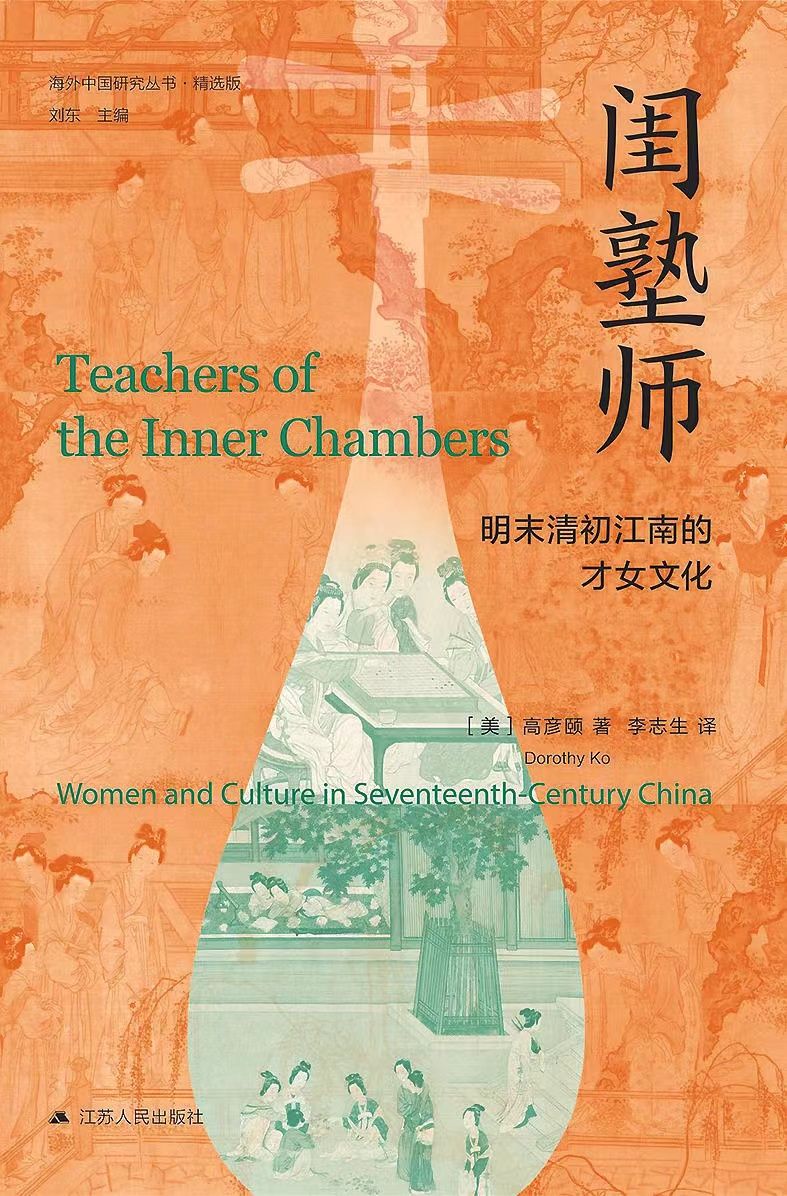
《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美]高彥頤 著 李志生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建構。明清時期的江南地區,商業繁榮,市民文化發達,與此相適應,江南的女子們逐漸超越了閨閣的限制,發展出一種新的婦女文化和社會空間。
《浮世精繪:蘇州彈詞長篇中的江南社會》《繡畫——中國江南傳統刺繡研究》和《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這三部著作主題接近,展示了明清時期江南女子介入社會生活的三種渠道,以及這三種渠道交織在一起所內含的、歷史學家對於中國女性的創造性與主體性的重新認識。
彈詞:醞釀著江南女性文化的各種要素
付楠的《浮世精繪:蘇州彈詞長篇中的江南社會》屬於“評彈與江南社會研究叢書”,叢書揭示了書目與藝人、聽眾乃至環境間的互動與流動性。《浮世精繪》中有不少筆墨涉及到明清江南的女性文化。
作者解釋:“彈詞屬於説唱曲藝,與評話是相互獨立的曲種,在取材上偏向男女情愛、家庭紛爭和市井生活的主題,大部分來源於廣泛流傳於民間的話本小説,故俗稱‘小書’。”所以蘇州彈詞在情節上會有明顯的程式化和雷同性。該書剖析了《玉蜻蜓》《珍珠塔》《十美圖》等評彈長篇。我們很容易發現,這些故事中的女性只是成就男性功業的陪襯。相比較而言,晚明大眾俗文學追求人性解放,馮夢龍、湯顯祖等在男女情感描寫上都強調“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清代的蘇州長篇彈詞更偏重禮教傾向,而且彈詞文本幾乎都經過了文人的修改整理再行出版,突出了“青天大老爺”的正派官員形象,以及以科舉為導向的擇偶觀念。然而,其中對於“嫌貧愛富”的抨擊,恰恰反映了這一時期士商聯姻觀念的潛變,説明當時士紳階層的家庭相當一部分是以財物、權勢為計而進行的“買賣”聯姻。同理,小姐們“私訂終身”的行徑,也可視為女性自我意識的一種呈現。
清朝的文化政策相當嚴苛,從各級政府到大部分士紳階層,對戲曲表演和市井文學的態度都較為抵觸。清代政府屢次頒布民間戲曲演藝的禁令,蘇州茶館被明令不得召集女性入內飲茶,蘇州彈詞書目遭遇多次禁書運動,彈詞藝人尤其女藝人生計難以維持,於是逐漸分散到蘇州周邊和江浙兩省交界的各處市鎮鄉村碼頭,遂有“吳宮花草移植滬上”之説。蘇州評彈成功抓住了在上海的新機遇,同光年間,寓居租界的蘇州彈詞因滿足了男性對“蘇揚之風”和滬上冶遊的想像而得到名人和報刊追捧。這種情形説明瞭評彈表演市場的興盛和商業社會環境的相關性,同時也醞釀著明清之際江南女性文化的各種要素。
繡畫:江南女性“閨閣”空間的擴大化
如果説《浮世精繪》只是對江南女性文化有所提及,那麼,許嘉的《繡畫——中國江南傳統刺繡研究》就是完全圍繞這個話題而展開的。
作者解釋:“繡畫,通俗來講,指刺繡觀賞品中帶有文人書畫趣味的刺繡,高超者能以繡的技法達到一種如畫、甚至勝畫的境界。”從事刺繡的群體,或大家閨秀,或普通農婦,或青樓藝妓,于中國江南傳統刺繡而言,江南水土的氤氳柔潤賦予了她們特有的詩性品格,她們對刺繡的敏感與執著是天生的、自發的、命運般的。“刺繡之藝,吳中為盛。其傳則自雲間之上海。”繡畫起源於上古江南吳地,成熟于宋,發展于近代松江,該書專論的晚明顧繡和清丁氏《繡譜》的發生地均在松江。
顧繡的誕生和興盛並非偶然,與時代地域背景、審美理念及明中後期整個文化藝術界的繁榮和文人雅士的密切參與有關。晚明盛産“大玩家”,追求優雅精緻的“時玩”,或是原有樣式基礎上的創新的藝術樣式,松江府服飾的艷美風靡一時。明中後期的商業意識和啟蒙思想改變了婦女的傳統觀念,女性逐漸敢於發揮自己的才學靈慧,大膽參與社會文化活動,閨秀女紅開始作為商品生産交易。除了深層的社會經濟原因,家族的文化積澱及個人的藝術修養等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顧繡女眷耳濡目染于家族的文人氛圍,優越的家庭生活條件和藝術文學修養使她們有閒暇寄情刺繡,怡情悅性,並且把自己的刺繡技藝與文人書畫相結合而成就“繡畫”之道。如畫之境、如天之工、如染之色,是公認的顧繡三大特點。
《繡譜》的作者丁佩,本人就是清朝中期擅繡畫之閨秀。該書不僅是丁佩幾十年刺繡的經驗總結,也是對江南地區包括顧繡在內的繡種的梳理總結,更是在傳統六藝基礎上對刺繡藝術的創造性點評。丁佩將刺繡與“才人筆墨、名手丹青同臻”,縱觀全書,以書畫詩文及其他藝術門類喻刺繡之處比比皆是,最後一章更是將張彥遠點評名畫的方法直接轉用於刺繡,“繡近於文”“通于畫”,説明在丁佩心目中繡畫實能登大雅之堂,丁佩已經有了以繡畫為工具,面向精英男性爭取女性話語權的主體自覺。
刺繡,自古以來被視作“女紅小技”,是“婦功”中的一項技藝,繡技高超是心靈手巧的象徵,還象徵著貞潔堅忍、悠閒恬靜。然而,明清時期繡畫的盛行,實際上遠遠突破了傳統刺繡的象徵意義。繡畫最重要的特點,是它與文人畫的結合。這説明瞭江南地區閨秀良好的詩文書畫的修養、女性知識水準普遍的提高,而這些繡畫引起社會上文人雅士的賞評與市場化的商品轉換,説明瞭“閨閣”空間的擴大化,知識女性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相對自由的賦權空間,通過刺繡將自己的主觀意識與文藝審美以及市場運作聯繫起來,把刺繡這種原本屬於私人的或同性之間共用的社交活動,延展到了更廣闊的社會空間,由此,士紳家庭女性的階級基礎和身份地位因近代性、商業化而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
閨塾師:對明清江南女性知識傳承的觀察
如果説《繡畫》所體現的江南女性意識仍然顯得較為模糊,那麼,《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書對明清時期江南女性研究的挖掘力度就更加明確深刻了。
明末清初江南富裕地區和都城周圍,職業女塾師群體的人數出現了明顯增長。這些巡遊的女性通常都是傳統文人家庭的女兒,她們通過為上流人家的女孩傳授儒家經典、詩歌藝術和繪畫而謀生,被同時代人賦予“閨塾師”的名稱,並作為儒家傳統中受人尊敬的女學者的精神後裔而獲得世人的尊重。
作者指出,閨塾師的生活暗示了一種浮現出的職業模式。女性的學問,特別是詩歌,是一個家庭的傳統。許多女塾師生於有學問但破敗的江南士紳家庭,並一直被母親或祖母教育著。實際上,塾師為這些女性提供了一條維持生計之路。作為出版過作品的詩人或得到承認的畫家,這些女性在因其聲名而獲得塾師的工作之前,就已經是職業藝術家了。與儒家視女性為安靜和無名的這些限制相反,一個女性的文學名望對其家庭來説,可能是一筆經濟財富。
《閨塾師》揭示了這些女性的公眾職業生涯和獲得的權力。一位女性獨立於其父、其夫之外的謀生,威脅了舊有的“三從”基礎。塾師的雇傭取決於作為有造詣的藝術家的聲望,而“聲望”這一概念違背了儒家所倡導的安靜和隱居的理想女性形象。閨塾師身體的流動性,顛覆了女性生存空間封閉性的理想。士紳家庭女兒教育的重心所在,證明了當時的教育模式與正統的道德教養出現了競爭。
但是,我們決不能就此將閨塾師認作中國近代女性的先驅者。對女子的教育,有著商業化的考量,是為了增加未婚女子的待嫁砝碼、已婚女子掌管家庭的能力,這與《浮世精繪》書中的敘述也是相呼應的。《玉蜻蜓》的張氏出身高門,全篇卻只強調她三從四德、打理門戶,《珍珠塔》的陳小姐詩書皆通,父親對女兒的要求卻是“略識幾個字就罷了”。《閨塾師》書中出現的所有女性,不管是閨塾師還是閨閣裏的少女、大家族裏的母親、妻子或寡婦,這些女性基本都遵循“三從四德”。江南士紳家庭重視女子教育,但是,女性知識水準提高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承擔為人妻、為人母的職責。歸根結底,最終強調的仍然是“重才更重德”。
《閨塾師》的寫作目的,是為了滌清“五四”啟蒙所建基的直線史觀,這種史觀將“傳統”與“現代”、“落後”與“進步”一分為二,造成了對中國婦女史的偏頗誤讀。作者認為,不能把“三從四德”簡單視為是對女性的壓迫,這種長期形成的儒家文化儘管以父權制為前提,但它在實踐過程裏有很大的彈性。我對作者的論點並不全然贊同,因為文化建構的權力掌握在男性手裏,女性的自由空間太有限了。在《浮世精繪》《繡畫》裏,我們都能發現女性文化背後男性的主導力量,而《閨塾師》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提供了對女性共同體內部文化教育的知識傳承的觀察。
“閨塾師”原指流動的女教師群體,《閨塾師》賦予它的涵義是擴大化的,除了所談及的那些江南才女的事跡之外,書中還有很多筆墨談論大環境。比如,廣受歡迎的戲曲如《牡丹亭》、市面上風行的各種出版物的影響,等等。在《浮世精繪》和《繡畫》裏,我們同樣能發現個人的、局部的知識與美學修養是被放置在大環境的影響範圍之內的,尤其三部作品都強調了江南地區出版行業的繁榮興盛和市民文化的廣為傳播。江南女性受教育、讀書、出版和旅行機會的不斷增加,是江南女性文化增長的必要條件,一個相當大的文化女性群體的存在,也給江南地區的城市文化留下了持久的印記。彈詞、繡畫、閨塾師,以及其他各種與女性相關的世俗工作渠道的出現,增加了女性自我滿足和擁有富有生存狀態的可能。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