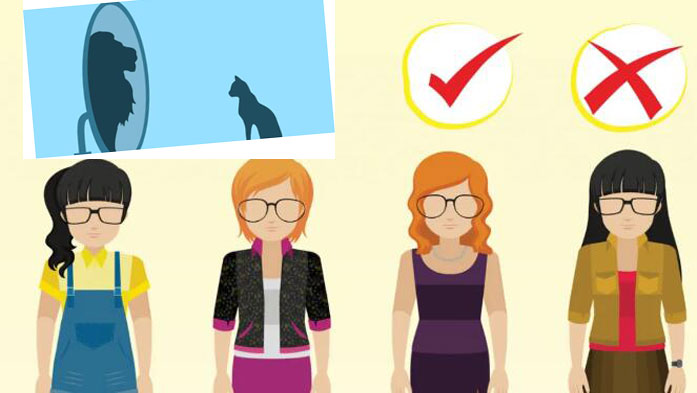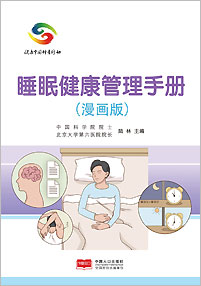心理援助熱線:3600秒,拉住“情緒漩渦”裏的青少年
發佈時間:2024-07-24 09:54:10 | 來源:中國網心理中國 | 作者:金蕓笑 王雪兒
北京回龍觀醫院內的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接線室。

7月19日,接線員李春玲挂斷電話後記錄來電者情況。
一條特殊的熱線,藏著高考的余溫。
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回龍觀醫院的一間平房裏,接連響起來自全國各地考生的電話鈴聲。有人説“考砸了”“人生是不是沒有必要繼續了”;也有人説考了高分不敢開心,怕選錯“賽道”。
這間平房有10個一平方米左右的格子間,配備了電腦和耳機,一天24小時,不能缺人——這是北京市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心理援助熱線(以下簡稱“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的接線室。在搜索引擎或社交平臺輸入“自殺”“安眠藥”等關鍵詞,最先彈出的就是它的號碼“010-82951332”,配文“這個世界雖然不完美,但總有人守護著你”。
進入6月,接線員劉婷明顯地感覺到,關於高考的電話多了起來,打來的人,主要問題是“注意力難集中”“一模二模考試成績不理想”或“擔心高考落榜”。劉婷同時發現,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學生、家長、家庭關係,呈現出與日常不同的狀態,一些青少年隱秘的心理傷痛容易爆發。
為這條熱線工作了16年的接線員韋曉艷發覺,近年來,青少年的求助電話比例升高,她已經習慣了和他們一起迎接每年都會準時到來的“招聘季”“考試季”“開學季”“畢業分手季”等。
她説:“心理熱線是很多社會現象的縮影。”
打心理熱線有時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
劉婷的工作以秒為單位計時,為了均等地分配資源,接線員通常會將打進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的電話控制在3600秒以內。這並不是固定時長,一旦通話開始,除非來電者自行挂斷,接線員不會主動挂電話,但會對通話時間作出提示。
哪怕來電者一直在哭泣,無法正常溝通,電話顯示屏的通話時長不斷累積,劉婷也會提醒對方“不用急著説”。
一般説來,她會用1200-1800秒時間去分辨和紓解來電人的情緒,“以對方為主,自由地講述遇到的困擾”,然後才是評估心理狀況、分析探討、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
6月初,劉婷接到一通電話,打來的女孩説被診斷患有抑鬱症,距離高考僅剩一週,媽媽卻讓她把漢堡包分給妹妹吃。女孩認為,自己正在經歷人生的特殊階段,卻還要照顧妹妹,産生了抱怨情緒,被母親批評“自私”。母女爭吵後,女孩情緒失控,産生了輕生的念頭,打心理援助熱線自救。
今年是劉婷在熱線工作的第三年,在此之前,她是一名有7年“面對面”經驗的心理諮詢師,也曾在特殊學校做過心理輔導老師。在傾聽來電女孩講述的過程中,劉婷聽到了更多資訊,她發現女孩父母離異,在校成績不錯,但沒有朋友。臨近高考的“高壓期”,家庭矛盾激發了她過往的痛苦。於是,劉婷引導女孩逐步弄清主要矛盾,讓她自發地意識到,排除升學壓力的話,她完全有能力應對這些困難。
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的前身是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心理危機干預熱線”,2002年開通,是國內第一條24小時開放的免費心理熱線。韋曉艷回憶,她從業以來,每年都接到高考考生的電話,電話裏有考前的焦慮緊張,也有考後的不甘與迷茫,一代代人很相似。
截至2024年,全國已經開通了400多條心理熱線。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查閱公開報道發現,高考前夕,不少省市都設置了針對考生的心理援助專線,以心理學專業見長的部分高校也為高考生開通了專屬的心理服務熱線。
一位在高校工作10多年的心理諮詢師告訴記者,中小學心理健康課程的普及,讓心理諮詢、心理熱線等“概念”更高頻地進入人們的視野。
不過,對青少年來説,心理熱線有時是一種“不得不”的選擇,一方面,面對面心理諮詢費用少則三四百元一小時,多則上千元甚至更高,他們負擔不起;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心理隱痛“無人訴説”幾乎是一種常態。
接到有高危風險的來電時,韋曉艷會向對方索要家人的聯繫方式,有的人會給。她在做“溝通橋梁”時經常發現,在父母的敘述中,孩子是“任性、無理取鬧的”。而那些不願意給聯繫方式的孩子則直截了當地告訴她,“説也沒用”。韋曉艷接過八九歲孩子的來電,問“爸媽為什麼都是對的”“作業寫不完怎麼辦”。
劉婷説,不少青少年説自己一個朋友也沒有,“他們社交能力有欠缺,但幸虧在問題發生時有很好的求助意識”。
一位商業機構的心理諮詢熱線志願者透露,她所在的平臺,每個手機號註冊用戶有30次免費熱線諮詢額度,曾有一位來電者,換了數不清的手機號打進熱線求助,在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求助者反覆撥打熱線的情況也很常見。
她牽掛著那通中斷後未再打來的電話
劉婷還記得,有個高中生,打來説經歷了一年的室友霸淩。每天,他要早早起來給室友買早餐,晚上要給每個人打上洗腳水。如果白天室友在寢室,他不被允許做自己的事,睡著了還會被室友用冷水潑醒。劉婷問他為什麼不告訴老師和家長,男孩説,早就告訴過老師,但老師不信。他是留守兒童,“週六日回家也是一個人”。
正説著,劉婷聽見,聽筒裏傳來慌亂的腳步聲和開關門的聲音,男生壓低嗓門説,室友回來了,他跑到廁所繼續對話。劉婷想進一步詢問時,聽到另一個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你在跟誰打電話”。男生沉默了,不再回答她的問題,辱罵聲和拳腳聲從電話線的另一端隱約傳來。
這通電話劉婷一直牽掛著,但她至今沒等到這個男生再次打來。在接受採訪時,她告訴記者,這不是孤例,近年來,因校園霸淩打來求助電話的人不在少數,全國各地都有,言語暴力與精神暴力並存,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更容易遇到此類問題。
有的孩子打來電話,不是為了問如何制止暴力,他們更因家庭和學校的漠視感到痛苦。“想想為什麼他們不欺負別人,就欺負你?”一些父母説過這樣的話。此外,一些在學校被霸淩的孩子,還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
劉婷説,孩子們的求助途徑不多,如果老師和家長不相信,他們通常會放棄保護自己。接到這樣的電話時,劉婷總有無力感,就像那天,男生的電話斷了,她只能記錄在案,接通下一個來電。這條熱線暫時沒有和警方建立應急聯動機制,韋曉艷談及此事,説自己期盼“和相關部門的合作”。
這並不容易,他們人手也不夠。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今年平均每個月接通2000多通電話,平均每個來電者等待10-20分鐘,近半年的接通率是4%。這個平均年齡30歲、30多人的接線員團隊流動性很大。
針對熱線與其他機構多方協同的問題,北京市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主任梁紅提到,多方協同涉及到的主體多,工作方式差異大,這讓很多機構的工作不易展開,“多方聯動是危機干預工作需要的,但多機構協調工作的機制還需要更多的嘗試和摸索。”
回龍觀醫院的“格子間”不是唯一的求助渠道。“12355”青少年服務台是共青團中央設立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和法律援助熱線電話,借助各級共青團組織的力量,一直在嘗試推進將心理熱線同救助統一起來。
比如,12355四川省內江市青少年服務台曾接到一名農村留守女童的求助電話。女孩自述父母在外務工,爺爺奶奶身患重病長期住院治療,鄰居鐘某以照料為由,多次進入女孩臥室實施猥褻。接到求助電話後,12355服務台立即安排法律專家與女孩取得聯繫,進一步了解情況、收集證據,協助提起訴訟。同時,督促女孩父母切實履行監護職責。多方協同下,法院以猥褻兒童罪判處鐘某有期徒刑五年。
“這不是你的問題”
韋曉艷説,“很多懂事的孩子,經歷都會讓我覺得心疼。”對遭遇霸淩的孩子,她會説“這不是你的問題”。
一位少年打來電話講述,他心疼母親承受過家暴,獨自撫養自己辛苦,又實在無法承受她傾瀉的負面情緒,他説母親對他期待過高,由此産生指責、批評和辱罵。韋曉艷也接過不少家長的電話,有的覺得孩子沉迷遊戲,有的抱怨孩子厭學,從這些來電中,她也發現一些家長不必要的擔憂、焦慮以及他們未察覺的自身問題。
梁紅經常在門診接診因學業壓力産生不健康心理狀態的青少年,她發現,這些孩子的父母有時“比孩子更焦慮”,梁紅認為,除了他們身處競爭激烈的環境因素,這些家長對孩子真實所需其實了解不足。她曾碰到來訪者傾訴:“我的家長只是讓我去‘卷’,但是沒有教給我怎麼去‘卷’。”
劉婷記得,有好幾個來電者,自述大學畢業三四年還沒有工作,整天待在家裏,要麼失眠,要麼早醒,還有人一度酗酒。
劉婷1990年出生,高考後自主選擇當年不算熱門的心理學專業。她能共情這些感到茫然、困頓的年輕人,幫他們紓解情緒,也嘗試帶著他們跳出對自身能力的一味指責。她説,影響求職結果的因素是多元的,但長期無業的年輕人蜷在房裏,將窗簾一拉,隔絕了晝夜變化,也排除了外界致因。她勸他們起身,“拉開窗簾”“找找別的因素,別全怪在自己身上”。
因就業産生的問題常常與其他問題相連,如父母期望、婚戀狀況等。韋曉艷曾接到一通來電,女子稱有個感情很好的男友,二人一起在外地生活。在父母的強烈要求下,女子報考了家鄉的事業編崗位。“上岸”後問題來了,她不知是愧對父母的期待,還是放棄深愛的男友。
韋曉艷説,熱線開通多年以來,她觀察到“失戀”一直是年輕人陷入自殺危機的重要因素。在她看來,一些年輕人往往把戀人當作“最後的稻草”,關係挽回無望時容易走極端,“這些來電者往往很難從家庭、社會和朋友那裏獲取足夠的精神支援”。
“你冷不冷,餓不餓,要不要從天台下來再聊聊”
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給接線員做培訓時,將電話分為“非高危來電”和“高危來電”。
非高危來電通話時間限制是3600秒,劉婷需要讓來電者通過問答的方式,做一個10分鐘左右的心理狀況量表,包括讓對方給痛苦程度打分、詢問是否有極端計劃等。劉婷能感覺到,多數來電者是如實回答的,儘管痛苦,但他們來電往往意味著正在嘗試自救。接著,諮詢師會分析量表結果。此時,留給3600秒諮詢的最後一步——探討應對情緒的方法——已沒有多少時間了。
高危來電的通話時限放寬至5400秒。諮詢師應對這樣的來電,大致分為兩步:確認對方人身安全,為對方建立安全網。
劉婷曾接到一通電話,對方一開口便説:“我知道你們這兒有錄音,我打電話想讓你們轉告我爸媽,我是自殺的。”
來電者稱已坐上天臺,輕生意向非常強烈,這是典型的高危來電。劉婷不能貿然試探,於是她問,你冷不冷,餓不餓,周圍有沒有商店買點吃的。她想轉移注意力,分散部分極端情緒。得到對方回應後,她又謹慎向前一步,“我很想聽你好好聊聊,但你現在這樣我很擔心,咱們從天台下來慢慢説好嗎?”
劉婷是無法等候在天台下的,她只能守在電話旁,一遍又一遍地盼著回音。幸好,對方説願意下來。
確定當下安全後,劉婷還需要幫助對方重新建立生存信心,也就是更長久的安全網。她會詢問來電者和親人朋友關係如何,有沒有什麼願望,是否養寵物,她要幫來電者找到留戀人間的支點。那個從天臺打來電話的人,最終接受了劉婷的幫助。按規定,熱線中心將對高危來訪者進行6次後續回訪,時間間隔分別是24小時、一週、一個月、三個月、半年和一年。囿於人手和工作量,回訪者無法保證一定是初次接到熱線者。
在採訪中,韋曉艷數次提到,導致年輕人心理危機的因素是多重的,這就考驗著接線員是否能從雜亂的矛盾中挑出最核心的問題。作為經驗老到的接線員,她同時也承擔著督導的工作。在短暫的接線時間裏,找到來電者産生情緒漩渦的癥結所在,需要專業功力。
培訓新人接線員時,韋曉艷發現一些接線員先入為主,對來電者真實情況的認知不夠,過多關注事實和過程等客觀層面的資訊,忽略了行為背後的動機。
針對這種情況,她舉了一個例子:孩子出現心理問題後,父母會更多關注孩子,夫妻間的矛盾減少,從結果上看,孩子生病反而讓家庭變和諧,“所以孩子是不可能主動去變好的,他知道自己好了以後,父母又會去鬧離婚了”。
“我的問題不嚴重,留給更需要的人”
在有限的時間裏,拉住崩潰的心靈——在梁紅看來,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的經驗是“規範化”,這也是她認為當前國內心理諮詢熱線普遍沒有做好的地方,即缺乏統一的接線標準。此外,她認為網路公開的心理援助號碼多而亂,這對來電者而言可能並非好事。
一名剛讀完大學一年級的女生,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回憶,自己去年撥打一條心理熱線,説不想高考,對方用質問的口氣講,“不高考能幹嗎”“學生不都是要高考的”“你上這麼多年學不是就白上了”。
“他全程沒有問我為什麼不想高考。”女生説,自己的情緒並沒有被尊重。
心理熱線水準參差不齊,造成的另一個問題是,資源利用情況不均衡。一項針對國內心理熱線服務現狀的調查顯示,20.1%的熱線在人員資質方面不符合“所有熱線諮詢員均有相關學歷教育背景或接受過相關的系統訓練”這一基本要求。59.5%的熱線日均接待量不足10個,5.6%的熱線日均接待量在60個以上,佔線是優質心理熱線的常態。
劉婷統計過,自己一個月要接30萬秒熱線電話,按一個人一小時算,也有80多人。有時來電者打來電話,匆匆説幾句就挂斷,“我的問題不嚴重,留給更需要的人”。
想解決佔線問題,其中一個方法是增加接線員、增設線路。
目前,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每年會進行兩次招聘,每次有二三十人報名,“獲得國家心理諮詢師三級或二級從業資格證書並有相應的臨床實踐者,具有醫學、護理學、精神病學、心理學或社會學知識者”會優先錄取,但由於對接線者的專業要求高,最後錄取人數並不確定,人手緊缺是常態。
中心沒有接線數量考核,採取輪班制。早班8小時,從早8點到下午4點;晚班16小時,從下午4點到第二天早8點,每個員工的排班是“早早夜,休三天,六天一輪”。坐上工位,就沒有休息時間,後半夜是“難題”最多的時候,有時接完一個電話天已經大亮了,劉婷靠坐在椅背上向後看,才發現晨光從半拉上的藍色窗簾透進來。
一些親友擔心劉婷被沮喪的情緒波及,劉婷的方法是“忘了”。包括她在內的很多諮詢員都明白,好好陪伴屬於每個來電者的那3600秒,然後接受“我們能做的就是有限的”這一現實。
一位從業者作了個比喻,“就像一個小孩子,並不是我們強硬的指揮造就了他的成長,而是他本身就有做好一件件事的潛質。鼓勵他,給他自我生長的土壤。心理諮詢或許的確有用,但不能神化它”。另一位從業者坦言,其實不管是心理熱線,還是心理面詢,諮詢員並不負責給出確定的建議,更不會直接著手解決來訪者的問題,只是幫著來訪者發現潛藏在後者身上的內在生機。
點開劉婷的微信朋友圈,裏面都是歡聲笑語的生活碎片:好友的聚會、兒子的笑臉、旅途的風景等,一張光束穿透烏雲的圖片被置頂,上頭還寫著一句話:“你會成為,別人心中的太陽。”(中國青年報 實習生 金蕓笑 見習記者王雪兒 文並攝)
山西婦女兒童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正式成立2024-07-24
親子公開課 | 3 個方法,幫助孩子成為千里馬2024-07-24
聚焦心理健康、踐行致力為民:記西南醫科大學心理學客座教授陳斌2024-07-23
兒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健康和公共衛生交叉前沿大會舉辦2024-07-23
工程院院士叢斌:心理健康貫穿人的整個生命週期2024-07-23
中國校園心理服務標準化示範工程湖北省試點工作正式啟動2024-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