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人小傳
劉敦願(1918—1997),湖北漢陽人。1944年畢業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西畫科。1947年應聘于山東大學,先後在中文系、歷史系執教。早年致力於山東地區田野考古調查,晚年專注于美術考古研究,針對史前陶器藝術、商周青銅藝術、東周與漢代繪畫藝術等問題撰寫了一系列論文。著有《劉敦願文集》。

劉敦願繪製的戰國青銅器紋樣。選自《文物中的鳥獸草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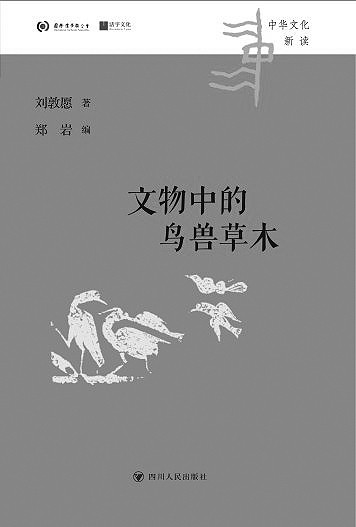


劉敦願(中排右二)婚禮照片,後排中為蒙文通。方輝提供
【大家】
追溯山東大學考古學科的發端,自然會追溯到1933年山東大學生物系教授劉鹹率學生參加董作賓主持的滕縣安上遺址的考古發掘,甚至提前到1928年時任齊魯大學助教的吳金鼎發現龍山鎮城子崖遺址。齊魯大學是山東大學的前身之一,這樣的學科溯源也自有其道理。不過,山東大學考古學科尤其是考古專業的全面發展還是始於劉敦願先生20世紀50年代在歷史系開設《考古學通論》課程,又于1972年創辦山東大學考古學本科專業。他重視田野考古的辦學思想也一直引導著山東大學考古專業的發展。因此,劉敦願先生是山東大學考古專業的締造者和奠基人。劉先生晚年致力於美術考古研究,在史前陶器藝術、商周青銅藝術與漢代繪畫藝術方面作出重要貢獻,是我國美術考古研究的開拓者之一。
一
劉敦願先生出身於書香之家,高祖父劉傳瑩為晚清舉人、國子監學正,是一位經學家。祖父劉少淮為鐵路高級職員,青年時期曾參加同盟會,精通法語、英語,兼通日語和俄語,晚年埋頭于法文大辭典的編纂工作。
劉先生年幼時就跟隨祖父走南闖北,20世紀30年代初在鄭州先後上了扶輪小學和扶輪中學,學校辦學條件較好,他因而受到良好的基礎教育。1934年到1937年,他遊歷了河南省內不少古跡名勝,並到山東登泰山、遊曲阜,去北京逛故宮、爬長城,尤其是1937年南京之行,參觀了南京的中山陵、明孝陵、靈谷寺、玄武湖和雨花臺,更有機會參觀了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和即將赴英參加倫敦國際藝術展覽會預展的全部作品,包括許多傳世的歷代名畫、書法、古籍版本、工藝品等國寶,還有安陽出土的甲骨、玉器、青銅器等考古新發現。這些經歷對於酷愛藝術的劉敦願先生的職業選擇産生一定影響,以至於在就讀大學這件事上與父親發生激烈衝突。
1939年,劉先生考上了夢寐以求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學習西方畫專業。抗戰期間,國立藝專和中央大學都內遷到重慶,劉先生經常乘坐輪渡過嘉陵江到對岸的中央大學去旁聽古代史課程,並深深為丁山先生講授的《商周史》和《史學名著選讀》兩門課程所打動。丁山先生很賞識他,還專門為他“開小灶”。我曾經見過劉先生手抄本《春秋左傳》,厚厚一摞,都是用毛筆謄抄的小楷,一絲不茍。劉先生笑著説,這都是當年丁山先生要求的“童子功”。數年的堅持,使得劉先生逐漸領悟到治學的甘苦與得失,也初步具備一些獨立思考的能力。1947年,經丁山先生的舉薦,在著名學者蒙文通先生資助之下,劉先生輾轉來到青島國立山東大學,作丁山先生的助教,從而開始步入學術殿堂。丁山先生長達60多萬字的《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1961年龍門書局出版)都是劉先生一筆一畫謄抄而成,此書“意在探尋中國文化的來源”(丁山語),運用了比較語文學、比較神話學與宗教學的方法,對史前神話加以初步分析,涉及題材之廣、考證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極具學術價值。這樣的學習經歷,使得劉先生在古文獻、古文字方面打下堅實基礎。1952年丁山先生因病去世,劉先生頓失名師,不勝悲痛。20世紀80年代,劉先生先後在《文史哲》發表《釋“齊”》和《博學的古文字學古史學家丁山教授》兩文,前者介紹了丁山先生曾在課堂上提到的對甲骨金文“齊”字的釋讀意見,後者則是對丁山先生生平和學術的介紹,以此感恩老師的栽培。
二
新中國成立後,劉敦願先生便一直籌劃創建山東大學考古專業。為了積累經驗,1953年經裴文中先生介紹,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洛陽燒溝漢墓發掘。1954年,開始為歷史系本科生開設《考古學通論》課程。據《夏鼐日記》記載,夏鼐先生與劉敦願先生在北京、青島和濟南有為數不多的幾次見面,所談話題均離不開山大考古專業創建事宜。為了滿足開辦考古專業的需要,劉先生同沈從文先生從北京琉璃廠購買了一批包括唐三彩在內的陶瓷文物標本,建立起歷史系文物陳列室。當時山東大學先後在青島、濟南兩地辦學,劉先生率領歷史系師生在省內多地進行考古調查,其中尤以青島、濟南、日照、臨沂、濟寧等地為主,發現了一系列考古遺址。如1952年5月與青島市文管會共同調查即墨縣李家宅頭村出土陶器,1955年春第一次調查日照兩城鎮遺址,1956年11月帶領部分學生調查青島市郊區東古鎮遺址,1957年5月帶4名學生調查兩城鎮、五蓮丹土遺址,1959年4月調查山東臨沂土城子、毛官莊、援駕墩、重溝、護臺、石埠等遺址。1961年11月,以歷史系韓連琪教授所收藏的清代畫家高鳳翰一幅畫作的摹本為線索,劉先生等按圖索驥,前往畫家故鄉膠縣調查,發現了三里河遺址,並專門以《根據一張古畫尋找到的龍山文化遺址》為題在1963年第2期《文史哲》撰文介紹這一發現,被學術界傳為佳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于1974年、1975年連續兩次對三里河遺址進行發掘,于1988年出版《膠縣三里河》一書,大大豐富了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內涵。2006年該遺址被國務院確定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劉先生和同事們的努力終於有了回報。1972年3月,山東大學獲得批准設立考古專業,成為較早設立考古學本科專業的高校之一。辦學之初,只有劉敦願、蔡鳳書、李肇年三位教師,劉敦願任教研室主任。當年4月,第一屆考古班10名學生入校。為了緩解師資不足的壓力,劉敦願先生先後聘請北京大學李伯謙、山東省博物館王恩田、徐州師範學院閻孝慈講授《商周考古》。接下來的兩三年,除了以上三人之外,他又先後聘請北京圖書館徐自強,山東省博物館張學海、朱活,故宮博物院李知宴等前來授課。1973年春,劉敦願、蔡鳳書等帶領考古專業學生對泗水尹家城遺址進行第一次發掘實習,李伯謙、閻孝慈等參與指導。此時的劉敦願先生已經55歲了,田野考古對他來説越來越力不從心,但他深知田野考古對於學科、專業發展的基礎作用,因此一直十分重視田野考古。他經常拿飛行員飛行時間與飛行技術成正比來教導、鼓勵新入職的年輕教師潛心田野考古,每個人都得過田野發掘這一關。重視田野發掘已經成為山東大學考古專業的傳統,即使在科技考古快速發展的今天,獨立自主開展田野發掘實習仍然作為山東大學考古專業的一項基本原則在執行。
三
改革開放帶來了學術的春天。劉先生在大力倡導田野考古的同時,他個人的學術興趣也開始轉向美術史、美術考古,這自然與劉先生早年的求學經歷密切相關。
對古代美術作品的關注實際上就是劉先生做學問的初心。據他回憶,早在重慶跟丁山先生學習期間,“我對中國古代青銅器裝飾藝術很感興趣,請問是否需要研究,是否已經有人從事研究。先生説這還是個空白,目前自然沒有條件,‘我正在全面整理金文資料,做重點器物的銘辭斷代,有了這個基礎,就可以做系統的藝術研究了’。”以年代學為基礎,在考古學框架內做美術史研究,這樣的研究旨趣決定了劉先生的考古研究走的是一條獨特的學術之路。
20世紀80年代之後,劉先生發表了一系列研究青銅器裝飾藝術的論文,就是在斷代基礎上進行的美術史、美術考古研究,是自己初心的回歸。而在此之前的六七十年代,劉先生對山東龍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陶器工藝與裝飾藝術的研究,既是以對常年考古調查發現陶器標本所做觀察為基礎,又何嘗不是初心的體現呢?劉先生1959年發表的《論(山東)龍山文化陶器的技術與藝術》一文(《山東大學學報(歷史版)》),就是一篇集考古、美術史和制陶手工業三方面知識于一體的大作。這篇文章的素材大多來自他親身考古調查獲得的陶片標本,其中有關制陶技術部分,大多基於他對山東農村制陶作坊所作考察的分析,而關於藝術部分,則有賴於他的美術功底。劉先生指出,龍山文化陶器的裝飾工作往往是同陶器本身的塑造與燒制結合;龍山陶器的器形比例勻稱和諧,質地輕巧,與輪制技術的精湛有著密切的關係;龍山陶器都是單色的,愛好單純的顏色是其特點;至於在陶器上運用劃紋、壓紋、印紋、鏤孔、附加堆紋與塑造動物形象等具體的裝飾方法也都是在不破壞上述特點的原則下進行的。因此,龍山陶器的裝飾方法是非常經濟而紋樣母題又是非常簡單的。此前有關龍山文化陶器紋飾的研究雖然不少,但如此細緻的觀察、認識則不多見。該文最大的貢獻,是指出了龍山陶器紋樣也有相當複雜的,這就是日照兩城鎮遺址“一再發現有類似銅器的花紋”,這種紋樣是曲線與直線的結合,刻畫比較細弱、潦草、稚拙,很像從什麼東西上臨摹下來的,並推測“是不是這時已經有了銅器,陶器倣自銅器,還是兩者都是從某種工藝品上仿傚而來(例如織物或刻骨之類的圖案)”。待到20世紀70年代劉先生從兩城鎮徵集到那件著名的帶有獸面紋的玉器之後,才得識此類紋樣母題的真面目,也證明劉先生當年的推測確有道理。20世紀80年代撰寫的《大汶口文化陶器與竹編藝術》一文,則顯示出劉先生對史前陶器裝飾持續的關注。從文章題目中不難猜測該文的研究內容,大汶口文化流行的鏤空陶器直接模倣自竹編藝術,現在已經成為共識,但在陶器上採用這種違反陶土性能的“超前”做法,一定是有著技術前提和藝術設計基礎,劉先生認為:“裝飾藝術與器形結合起來考察,與其稱之為圖案移植,還不如説是陶器對編織物的直接模倣。”若這樣的討論僅限于史前資料,該觀點的立論基礎顯然具有很大的推測性質,而該文的精妙之處還在於結合商周青銅器和古文字資料,尋找到不同材質器物之間的關聯性,又從先秦文獻中尋得上古北方盛産竹子的若干記載,從而論證陶器模倣編織物觀點的可信性,正可謂左右逢源,相得益彰。劉先生這種貫通史前與歷史時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在分科日益專業化的當下愈益顯得難能可貴。
劉敦願先生學術研究最為集中的領域還是對商周青銅器紋樣的解讀。這些論文大多發表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正值他的學術活躍期。其學術觀點之所以至今深受學界重視,與劉先生一生的求學和治學經歷密切相關。從這些成果可以看出,劉先生比較早地揚棄了流行已久的“圖騰説”,將商周青銅器或三代藝術品納入“歷史”與“考古”場景加以考察,他對多種青銅器紋樣意義的解讀,即使對於信從近三十年來影響甚廣的三代禮器動物紋樣“通天説”“媒介説”的學者而言,讀起來也絲毫不會有不合時宜的感覺。如對饕餮(獸面)紋的起源與含義問題的探討,從良渚、龍山玉器紋樣,到二里頭銅牌飾、商周青銅器紋飾,再到漢畫像石、後世民間藝術乃至希臘瓶繪,從《春秋左傳》到《呂氏春秋》再到《隋書·東夷傳》,論證青銅器上的獸面紋樣不過是安置在門戶上的“獸頭骨角”的複雜化與藝術化,“應是象徵威猛、勇敢、公正等等,用意明確簡單,未必含有《呂氏春秋·先識覽》‘周鼎著饕餮’云云的那麼一套神秘複雜的故事”。又如《夜與夢之神的鴟鸮》是一篇對商周青銅器常見的貓頭鷹題材進行解讀的論文,劉先生在廣泛收集史前、商周以至漢代有關貓頭鷹題材文物和紋樣的基礎上,結合古文字和歷史文獻中關於猛禽、夜禽的描述,勾勒出商周時期有關鴟鸮崇拜的史實,有助於了解國人對於貓頭鷹好惡觀的變化過程,補充了文獻記載的不足,其中對於晚商時期鸮類題材的美術史觀察,從立體雕塑品重心的處理方式,到平面鏤刻中頭部與身體正面透視法的運用,分析十分精確,配以劉先生親手繪製的插圖,讀來讓人興趣盎然,尤其是對於習慣於閱讀考古報告中單調的器物形制紋飾描述的人來説,常常會産生恍然大悟的感覺。在一篇討論中外猛禽崇拜的文章中,劉先生從古埃及和古希臘藝術品中的猛禽入手,反觀中國古代猛禽不那麼突出的史實,因此文章取名為《未曾得到充分發展的鷹崇拜》。雖然當時考古發現的這類例子有限,但劉先生仍然尋找或辨識出數十件相關題材的文物,其中有見於史前時期仰韶文化、紅山文化者,而尤以山東龍山文化數量最多,個中原因自然與東夷族群鳥崇拜有關,尤其與少昊氏“高祖鷙”有關。商和西周鷹類題材很少,與鴟鸮形成鮮明反差。劉先生還敏銳地觀察到,春秋戰國見到的鷹攫蛇或鷹蛇相鬥的題材,蛇為一首雙身,顯然具有吉與兇、禍與福相剋之類的含義,這類的鷹應具有神性。筆者注意到,劉先生所舉這類題材青銅器的例子,有一件出土於安徽壽縣楚墓的青銅蓋飾,老鷹作展翅飛翔狀,雙爪攫獲一首雙身的蛇,巍然屹立在器蓋上,這樣的造型幾乎與近年來陜西石峁出土的陶鷹如出一轍。石峁所見這類陶鷹身體壯碩,發掘者推測是一種在祭祀或禮儀場合使用的具有神性的陳設品,只是因為足端殘損,不知道當初是否也在鷹爪之下塑造有這種一首雙身的蛇?
劉先生討論過的動物題材十分廣泛,僅從下面所列題目就可窺見一斑,如《含義複雜的中國古代虎崇拜》《作為財富象徵的牛紋與牛尊》《湘潭豕尊與古代祭祀用豭》《中國古代藝術中的鹿類描寫》《神聖的昆蟲——蟬紋研究》《貘尊與雞卣》,幾乎涵蓋了商周青銅器紋樣中所見的所有動物題材。動物紋樣之外,劉先生的關注範圍還包括其他常見紋樣,如《青銅器勾連紋探源》《圓渦紋與〈考工記〉的“火以圜”》等,這類紋飾常以所謂“底紋”或輔助形式存在,但也各有源流,如認為勾連紋原是竹蓆所用,然後移植到青銅禮器之上,並引用《禮記·檀弓》所載曾子臨終“易簀”的故事,指出看似普通的竹蓆也有等級之別,而竹蓆上的圖案則是區分貴賤的主要標準之一。這些觀點逐漸被近年來湖湘地區楚國的竹蓆實物所證實。劉先生的大作往往就是這樣,從小處著眼,解決的都是一些基礎性的問題。除了這些長篇大論,劉先生還經常寫一些類似隨筆的短文,一般是一兩千字,如《給動物係環帶牌的故事》《甘肅黑山岩畫狩獵圖像中的飛鳥》等。無論篇幅長短,文章均言之有物,一般都是從某一題材的造型和紋樣出發,結合先秦文獻以及後世筆記野史,尋繹解讀其原本含義,其結論往往是發人所未發,給人以深刻啟示。這就是劉敦願先生留給後世的文化遺産。最近,鄭岩教授將劉先生的部分論文以《文物中的鳥獸草木》為題結集出版,讓對劉先生美術史、美術考古感興趣的讀者免於搜尋之苦,實在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四
劉先生經常慨嘆晚年有幸趕上了學術昌明的好時代,因此愈發珍惜點滴時光,勤於筆耕,與時間賽跑。在病重期間,他躺在病床上數次説起自己能在有生之年把想寫的東西寫出來,感到比較滿意,但同時又能明顯感覺到他對人生的留戀。2018年是劉敦願先生百年誕辰,有媒體在採訪了鄭岩教授和我之後,用“一位錯時的考古學家”來概括採訪者和被採訪者心目中的劉敦願先生,我想劉先生本人對這一概括也會表示認同的。
劉先生非常熱愛田野考古。1958年,從野外調查歸來、口袋中裝滿陶片的劉先生給剛剛出生的三兒子取名為劉陶,以此紀念野外考古調查的新收穫。他對考古的熱愛由此可見一斑。改革開放後,年屆六旬的劉先生把相當大的精力用在人才培養上,對研究生和年輕教師的培養尤其強調田野考古。他總共培養了4位研究生,除了親自講授商周考古之外,特別強調考古實習,為研究生的調查、發掘實習盡可能提供方便條件。而在畢業論文的選題方面,他也堅持從第一手資料入手,做最基礎性的研究,當時的基礎研究就是以地層學、類型學為基礎的陶器編年。第一屆研究生倪志雲師兄寫的論文是濟南大辛莊遺址陶器編年,以此為基礎討論商史問題。第二屆的欒豐實和我,分別選擇了泗水尹家城遺址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陶器分期,兼涉與周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關係問題。第三屆許宏也是以大辛莊陶器編年為基礎討論魯北地區商文化的性質等問題。實際上,倪志雲師兄的美術功底相當好,讀書期間就發表過有關史前彩陶研究的文章,但在20世紀80年代考古研究都是以年代學為主的大背景之下,陶器編年無疑是最具前沿性的問題,這樣的選題顯然也最容易獲得專家認可。
記得1984年秋,剛剛步入研究生一年級的我陪同劉先生前往河南安陽參加首屆商史討論會,夏鼐、胡厚宣、張政烺、田昌五、李學勤、鄒衡、安金槐等著名學者都參加了,可謂大家雲集。劉先生提交大會的論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關於鴟鸮的大作。因為此前不久殷墟婦好墓出土了體積最大、形制最為精緻的一件商代青銅鸮尊,這篇論文是非常適合在安陽商史會議發表的。不過在會議分組時,這篇論文究竟應該放到商史組、商代考古組還是古文字組?似乎都不合適,而且會議上就沒有類似的美術考古論文,最後好像是放在考古組發言討論。後來出版的會議論文集並沒有將該文收錄其中,大概小開本的論文集不大適合刊登滿是線圖的文章吧。不過,這篇大作在會下還是受到不少學者的好評。陜西師範大學的斯維至先生、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徐錫臺先生都跟我説這篇文章寫得好,徐先生還特別囑咐我要好好跟劉先生學習美術考古,還説到這個領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來的,目前國內研究者很少,但在國外美術考古一直是考古的大熱門,將來我國也會重視云云。我雖然不能全都理解,但感覺他們説的是對的。因為在此之前,劉先生關於美術考古的大作已經在學界産生一定影響,英國學者傑西卡·羅森教授、艾蘭教授,美國學者張光直教授都曾來山大拜會過劉先生,並以他們的大作相贈,一些影響很大的美術史乃至美學類圖書也徵引過劉先生有關青銅器紋樣解讀的觀點。此後的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美歐學界關於三代青銅器美術考古研究的論著被大量譯介到國內,其中尤其以張光直先生的祭祀美術、薩滿説、動物通天媒介説等影響最大。這些觀點一般是把青銅器動物紋樣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的,與之相比較,劉先生對不同器物造型、不同紋樣母題的系列解讀真正做到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且研究的範圍也不僅僅限于動物主題。因此,這些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反而愈加顯示出獨特的學術魅力和價值,日益得到學界的重視。從這一點來説,昔日的“錯時”不正可作為今日的應時、適時嗎?
(作者:方輝,係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