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標題:徐城北走了,他曾從老北京寫到新北京|逝者
10月11日上午7時30分,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徐城北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徐城北的女兒徐佳于當日發佈了訃告。訃告中還表示,因疫情防控要求,一切後事從簡。

訃告截圖。
徐城北生前專注于對京劇藝術和京城文化的研究,著有《老北京:帝都遺韻》《老北京:巷陌民風》《老北京:變奏前門》《梅蘭芳與二十世紀》《京劇與中國文化》等各類著作。

徐城北,筆名塞外、品戲齋,1942年生於重慶,在北京長大,1965年畢業于中國戲曲學院。歷任中國京劇院編劇、研究部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京劇一百題》《梅蘭芳與二十世紀》《京劇架子與中國文化》《老北京:帝都遺韻》《老北京:巷陌民風》《老北京:變奏前門》等。(照片由郭延冰于2006年攝)
在2006年,新京報曾專訪徐城北先生,請他口述個人的生活、思考和寫作經歷。當時他六十多歲,不斷回憶過去,在口述中感嘆,“現在這些前賢很多人都走了,我自己也步入了老年。那些回憶都成了我後半生的寶貴財富”。
以下為徐城北先生口述舊文《徐城北:做新時期的舊文人》。重發以紀念。
口述丨徐城北
早年經歷:離開北京,回到北京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媽媽在《大公報》做過記者,筆名子岡。家裏的文化背景,給我帶來非常深厚的影響,像沈從文先生、聶紺弩先生、常任俠先生等一大批老先生,都是媽媽的朋友,這些老人對我都非常鍾愛,都願意把自己那一肚子學問教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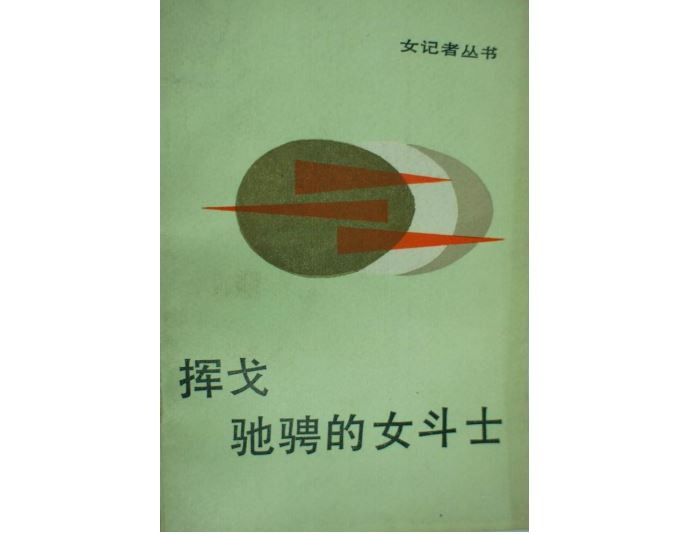
《揮戈馳騁的女鬥士:女記者子岡和她的作品》,徐城北著,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7年3月。
當時有個青年作家浩然,他忠告我説:“城北,你缺少的不是筆墨,你應有自己的第一手生活,這樣你寫東西就會源源不斷了,誰也搶不去了。當然,我也不主張你去普通的農村,那樣跟你的氣質和專業也不契合。你需要特殊的生活基地,只要你能一竿子插下去,三五年必有所成,生活不會埋沒人的。”我覺得很對,沒過多久,媽媽在我們家那臺十二英寸的小電視上看到了反映新疆建設兵團的報道,看了之後媽媽問我:“你願不願意去新疆?”
我想了想説,去!
1965年,我就到了新疆,在新疆一待就是八年。到新疆若干年之後我才猛然發現,我家庭周圍的那批老人身上的和身後的文化,是非常深厚的。這種文化我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又不是説割斷就能割斷的。我開始思念沈從文、聶紺弩、吳祖光那一批老先生,甚至比思念我的父母還要強烈。我開始希望離北京近一點,離他們近一點。
一度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劇團要我當編劇,但戶口解決不了。河北梆子劇團把解決我戶口的問題報到了市委,市領導答覆説:北京有很多文藝幹部下放在農村,有什麼理由從新疆調一個青年的文藝幹部呢?後來我又想去唐山,也沒去成。

《中國京劇》,徐城北著,五洲傳播出版社,2003年10月。
最後我選擇了河北省固安縣,我直接找到縣委書記,自報家門,説明我的家庭跟自己都是什麼情況。我説得很坦率:“我想到這裡來,但是不準備在這裡幹一輩子的,將來你一定要放我回北京。”那個縣委書記説:“完全理解,不過你來了要先賣把子力氣,好好幹幾年,將來我一定把你送回去。”沒想到一幹又是七年。
後來回北京,我還真不是靠“後門兒”,憑的完全是自己。我曾把一個寫回憶新疆生活的劇本寄給了中國京劇院,最初無非是想徵求一些意見,沒想到他們看了之後,直接就給我發了調令。
進京劇院十年三寫梅蘭芳
很快我就被調回了北京。
回了北京之後我開始就是一門心思想搞編劇。我有生活和文字上的積累;我有幾位難得的好師傅———京劇圈裏有范鈞宏﹑翁偶虹,文化界有吳祖光和汪曾祺。幹了不到三年,文化部長在春節講話中説到京劇團要搞承包,劇團要打破原先的建制,重新組成小分隊為不同的觀眾群服務。這樣一來,演員們也不排新戲了,把創作人員甩在一邊,忙著賺錢去了。當時劇院領導安慰我們説:“等暫時的混亂過去之後,工作還會有的。”我在台下補了一句:“麵包也會有的。”我心想,我的師傅們可以等,唯獨我不能等,為什麼?因為他們的成就已經奠定了,唯獨我還是一張白紙,如果若干年後我還是一張白紙,這個地方我就不能待了。
我進入京劇院時,筆頭比較活,新詩、舊詩、散文、雜文寫過不少,當時我父母的那幫老朋友紛紛復出,擔任了諸多報刊的主編,我投稿不愁發表。正好京劇院也不用坐班,我就撒筆寫開了。寫了半年一年之後,吳祖光和汪曾祺都託人帶話給我:“城北啊,你寫得太雜了。這些東西是你在新疆的、在河北的生活,而不是你在京劇院的生活,不是你作為一個編劇應該寫的生活。京劇院現在雖然亂,但終究是塊寶地,袁世海、李和曾都是國寶級的演員。不要看京劇演員説話不利落,認字有限,但京劇文化是直接秉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線,只不過是沒有人把這些內容勾連在一起,你正應該擔當起這種勾連的工作。”我聽了這種規勸,就開始把自己的研究創作集中在梅蘭芳身上了。

《這裡是老北京》,徐城北著,陜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當時梅蘭芳已經去世多年,我為什麼選擇梅蘭芳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呢?因為我在京劇院接觸到那些健在的老先生,許多大牌演員在回憶自己時總難免帶著吹噓成分,我就是想找一個比他們還大氣的人壓住他們。從這個角度上來説,梅蘭芳最合適,梅先生雖然走了,但去世的時候歲數不是很大,而且他是中國京劇院的第一任院長。我母親採訪過梅蘭芳,她周圍的一些朋友跟梅先生也熟識,在這樣的基礎上,我調集了大量的資料,又採訪了梅蘭芳的家人、弟子包括尚、程、荀這三個家庭裏的人。
這樣的工作讓我對於梅蘭芳及其同輩成長的年代文化背景有了細緻了解。
這樣,我就開始寫書了,1990年我就出版了《梅蘭芳與二十世紀》,後來一不做二不休,咬定青山不放鬆;1995年,我又出版了《梅蘭芳百年祭》;到了2000年,我又寫了一本《梅蘭芳與21世紀》。這就是朋友們所説的“十年三寫梅蘭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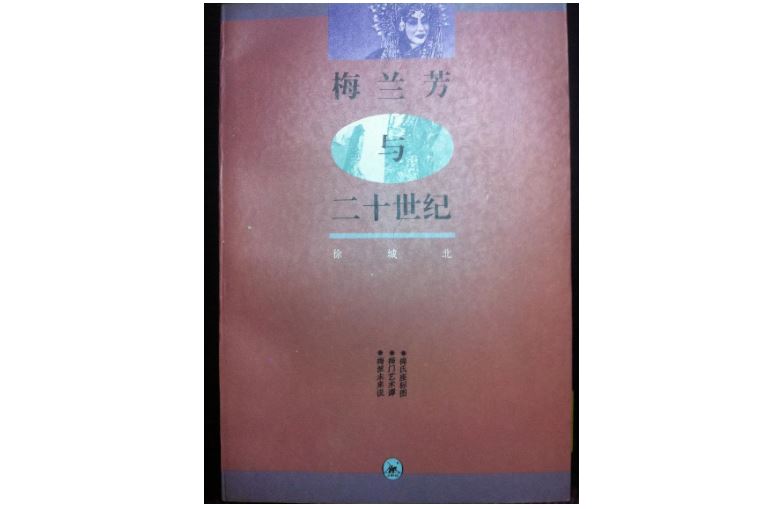
《梅蘭芳與二十世紀》,徐城北著,三聯書店1990年12月版。
從老北京寫到新北京
實際上,到了1995年前後,京劇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京劇大勢已去,要説進步是在文化層面,在理論上,唱腔上進步不大。就是在那一年,我開始尋找我自己新的研究方向。正好當時江蘇出版社來北京組稿,找人寫老北京的稿子。我説:“我正在寫《京劇和中國文化》,還差個尾巴。”但是他們咬住了我,非讓我寫。
我想自己有研究老京劇的底子,對於老北京的事兒也比較熟,就應承下來。寫完《京劇和中國文化》,我就開始寫《老北京》,在那本書中,我憑著對老北京感性的直觀認識,寫了一些老北京的舊事,出版之後賣得非常好。於是我跟出版社説:“一本我還沒有寫過癮,我想變換角度逐漸深入,寫一個三部曲。”出版社讓我拉了一個提綱,他們看了之後就同意了,我次年就出了《老北京2》,隨後又寫了《老北京3》。
寫完了《老北京》三部曲,我58歲了,離退休還有兩年,出版社的朋友跟我説:“城北兄,你60歲就得退休了。我們有個建議,既然你寫了《老北京》三部曲,如果你的身體和腦子還行,在2008年之前再寫出《新北京》三部曲如何?”我覺得這建議可行,對我來説也是一種激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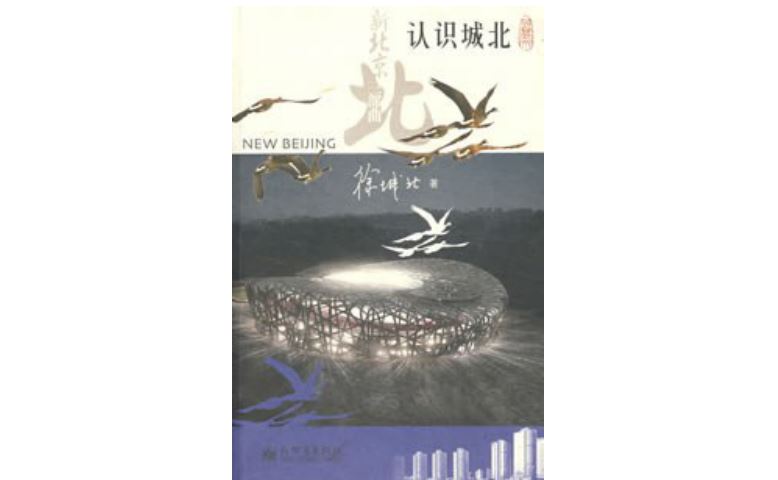
《認識城北》,徐城北著,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6月。
就這樣,我從北京城南搬家到現在這個地方———新北京的城北,徐城北這下子真的住到了城北!
搬到這裡我有一個考慮,那就是在我《新北京》的三部曲中,第一本就定名為《認識城北》,這個城北不是我本人,而是新北京的城北。
現在這本書已經寫完了,第二本也已經寫了一半,在這本書中我回到城南,描寫新北京的城南,第三本我計劃寫新北京的左東右西,東到通州,西到門頭溝,而且在東西之中,還牽扯到“中”———既包含北京城的中心區,也把中國哲學上的“中”的內容也融會進來。
沈從文送古董
這些內容都寫完之後,我打算掉頭往回轉,極力做一名“新時期的舊文人”,回到沈從文、汪曾祺、聶紺弩那一輩老人的傳統中去。説到我和那些老人的精神聯繫,可寫與可琢磨的東西太多。
比如説我對沈從文的認識,是從我自小在沈從文的膝蓋下玩的時候得來的。我33歲結婚的時候,我們家在平安裏,沈從文那時住東單,他坐著111路無軌電車到了我們家,送了一點小禮物,一個是五蝠捧壽的清朝盤子,上面貼的紅字是他自己剪的。還有一個,在一張小小的紅色灑金紙上寫了他對我與妻子的祝福:“祝兩位多福長壽———為國家多做好事為多福,長壽則可以為國家多做幾十年好事。從文敬賀。”別小看這紙小,那是故宮裏的古紙,非常名貴。

《京腔話京劇》,徐城北著,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1月。
至於汪曾祺,他算是叔叔輩了,但是我始終叫他“先生”。後來我跟汪先生比較熟悉的時候,我也成人了。中國作協組織作家采風團,我們倆都是成員,他是年紀最大的,我是年紀最小的。同時我倆還都是大連日報文藝部的顧問,有一年夏天,大連日報組織筆會,我和他都去了,住在棒棰島。晚上吃完飯之後,很多當地人就拉著汪先生寫字畫畫,汪先生覺得自己一個人去未免孤單,就拉著我和蘇叔陽一塊去。我去了,寫了幾幅字就不寫了,站在汪先生旁邊看他畫,一遇到出色的就“截留”了下來。
現在這些前賢很多人都走了,我自己也步入了老年。
與健在的老人見面的機會雖然還有,但像以前那麼在一起玩的機會,卻很少很少了。
那些回憶都成了我後半生的寶貴財富,不要説寫進文章了,就是想上一想,心頭也充滿了幸福感。
逝者新聞作者|何安安
舊文口述丨徐城北
舊文采寫丨陳遠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