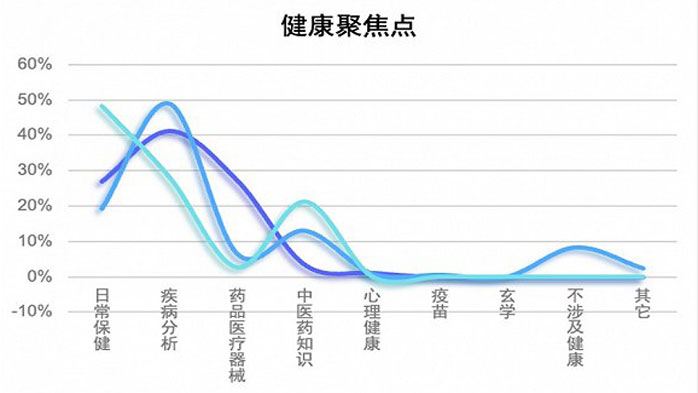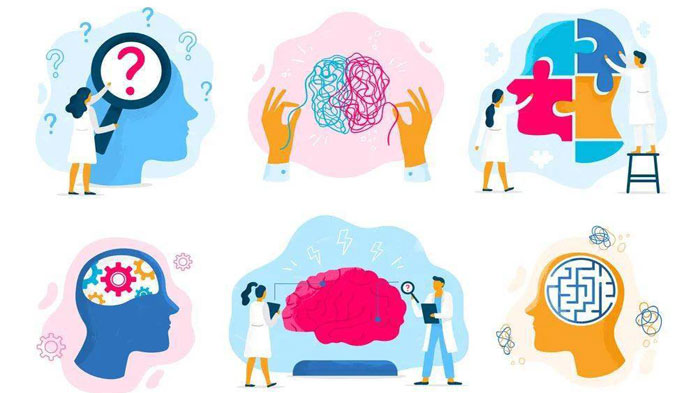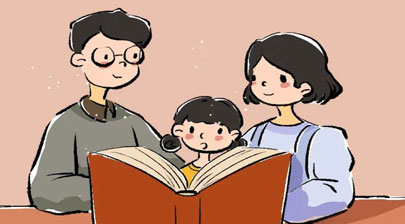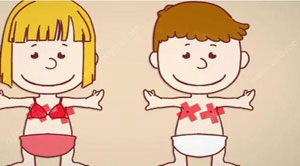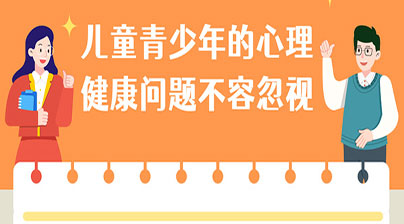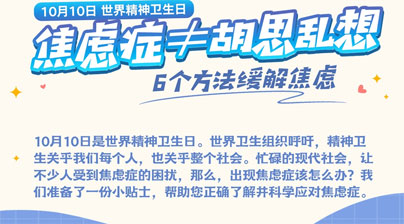李勇生:在看不見的世界裏,用心理諮詢救人救己
發佈時間:2023-12-04 09:39:05 | 來源:中國網心理中國 | 作者:慕宏舉鈴聲響起,李勇生迅速戴好耳麥,接通電話。他可能會聽到“我不想活了”的大吼,也或許是壓抑不住的痛哭,還可能是自言自語的低喃,抑或是令人不安的大段沉默。
捕捉聲音和其中的情緒,本就是李勇生最擅長的事,作為自殺干預熱線的接線員,他要做的就是快速分析來電者的心理狀態,然後有針對性地溝通、勸導,有時充當傾聽者,有時化身勸慰者,一直守在“死門”前。
一個電話可能要打很久,時間的流逝李勇生只能通過感官來判斷——打在身上的風變涼了,那就是太陽落山了,街上人聲車聲漸多,上下班高峰到了。李勇生今年41歲,失明31年。
年幼失明,他跌跌撞撞闖世界,急切地證明自己即便看不見,也能像普通人一樣生活,自卑又驕傲。做盲人心理諮詢師,他試圖走進別人的內心,治愈他人的同時,與自己和解,在助人與救己中,尋找人生的意義。

李勇生。受訪者供圖
眼睛以上,全是“雷達”
十月的一個下午,天津郊區的一個小院裏,李勇生坐在院裏等著來訪者。人走到他面前兩米時,李勇生抬起頭,向著腳步傳來的方向站起身,伸出右手,過程乾脆利落。
“你好,歡迎,走,我們進屋裏聊。”
手被抓住握兩下,李勇生“看”向來訪者,他墨鏡後的雙眼,右眼緊閉,左眼微張露出灰藍色的瞳孔,無神。
盲人的姿態更多顯現出來。他右手向前試探地摸索,走到門邊,頭微微低下——儘管站直後他的頭頂距離門框還有很大距離;在熟悉的走廊裏,他的步子邁得很大,但身體忽左忽右,直到摸到右側墻壁上的扶手,該右轉了;進屋後,幾步之外就是桌椅,當腳尖踢到桌腿時,他停了下來,沿著桌子邊緣摸到了緊挨著的木椅,轉身,雙手向後握住椅把,緩緩坐下。
心理諮詢正式開始。
傾聽時的李勇生頭略低著,眼睛“看”著對方,時不時挑下眉毛,耳朵不經意地抖動,像是打開了全部的感知“雷達”。他很快捕捉到了對方細小的動作——對面那個聲調高亢的年輕人,一會兒蹺著二郎腿,一會兒又雙手摸著膝蓋,時而坐直了身體,時而靠在椅背上。
李勇生心裏有了判斷,這是個內向、心思細膩、不太成熟的大男孩。“可能也就1秒”,李勇生這樣描述他的感知速度,他用自己的經驗解釋,“音調高的人往往心思細膩,那些聲音低沉、坐著不亂動的人一般城府較深,他絕對不是,甚至不夠成熟。”
談話不知不覺間進行了三個小時,李勇生問來訪者:“天黑了,要不倒點水再繼續?”
他面向窗口接著説,“窗外的鳥已經從嘰嘰喳喳的啼叫變成一聲一聲的低鳴,涼氣也灌進我衣服裏了,最近天津溫差大,有點兒涼,我也是想穿件外套。”
似乎感知到了對方的詫異,李勇生指了指自己的眉心,又以眉心為起點,沿著眉毛、耳廓上方、後腦勺畫了一個圈,“這個圈以上都是我的感知區域,像雷達一樣。”

李勇生做心理諮詢時喜歡與來訪者一起坐在沙發上。受訪者供圖
失明是件心酸且自卑的事
李勇生並非天生失明,墜入黑暗前,他眼前的最後一個畫面是,被鮮血染紅的雪。
那是一個初冬的中午,在山東德州老家的村子裏,10歲的李勇生和小夥伴打鬧時,一跤摔在了路中間的鐵磅秤上。
爬起來後,他摸了摸自己的眼睛,原本應鼓起的右眼癟了。依靠左眼依稀的光亮,他看到滴落的血染紅了周圍的雪。
當晚,李勇生做了眼球縫合手術,醒來時不知道過了多久,只覺得頭頂很重,“像箍了頂鐵帽子”。他摸著臉,雙眼被一層層紗布裹住,世界一片黑暗。也是從那時起,他總會下意識摸頭頂,“像有什麼東西在上面,想把它摘下去,總覺得頭頂戴了鐵帽子,持續了很多年。”
突遭劇變的李勇生還沒來得及理解失去雙眼意味著什麼,只知道一切都變了。“早晨”由射進家裏的第一束光變成了麻雀的第一聲啼叫。身體對溫度變化的感知更精細了。當“溫暖“與嘰嘰喳喳的麻雀聲同時出現時,屋外便是晴朗的好天;而潮氣和扇動翅膀的聲音同時出現,他斷定,一場大雨即將來襲。
直到那些背後議論的聲音四起,他才意識到,失明竟是件心酸且自卑的事情。
不舒服的感覺並非猛烈的,難過的瞬間總是悄無聲息地出現。“多好的孩子啊,這輩子算是廢了。”親戚無心的一句話,直直扎進李勇生的心裏。
酸楚漸漸堆積,自卑從中發酵。原本活潑開朗的孩子成了走路都踉蹌的盲童,他參與不進小夥伴們的遊戲和話題,不能再上樹掏鳥、下河摸魚,春天的綠草、夏天的藍河、秋天的黃葉和冬天的白雪,在他的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和意義。
失明後,李勇生的腦海裏總會涌現出“曇花一現”的理想。聽著電視劇裏軍人鏗鏘有力的口號聲,想著自己要是能看見,或許能去當兵;聽著新聞裏播報航太員搭乘飛船上了太空,他也想知道太空是什麼樣子。
理想穿插進殘酷的現實,總會帶來短暫的失落,而這一切都和失明有關。“雖然沒有直接的傷害,但總有不舒服的地方,就像胸口壓了塊石頭。”
跌跌撞撞闖世界
或許是骨子裏天生要強,也或許是想擺脫自卑,李勇生總想證明自己與常人無異,“別人越説我做不了,我越想做出來給他們看。”
當具象化的物品變得模糊,勇氣就佔據了上風。以往怕蛇又怕鬼的李勇生,不僅敢徒手抓蛇,也敢一個人闖進漆黑的小路,還敢爬上三層樓高的樹杈。
他一點點摸熟了村裏的路,一塊不起眼的石頭,墻壁凹進去或凸出來的石磚,地面的斜坡都是指路標識,“地圖”在腦子裏漸漸成形,他扶著墻壁就敢大步快速向前。
村西頭幾米深的河,常有村民掉東西進去,村民嫌臟、怕深,只有李勇生願意脫下衣服憋足一口氣扎進去,在淤泥中摸索失物,每找到一件,可以得到幾毛錢的“辛苦費”。上岸後,他來不及沖洗,帶著一身河腥味將錢換成冰棍,一路嗦著回家。一來二去,李勇生的水性越來越好,找他幫忙的人也越來越多,他第一次覺得“挺自豪”。
後來,為了改善家裏生活,李勇生父母帶著他和弟弟去天津打工,一家四口住在了郊區的村子裏。很長一段時間,他最遠只走到家門前的衚同口,再往外走,母親便以看不見為由命令他不許胡來。
離開了熟悉的環境,一切都要從頭再來。憑藉一根竹竿,一雙沿著墻壁摸索的手,李勇生將自己的活動範圍從衚同擴大到村裏,又從村裏走向村外。
有限的地圖慢慢展開後,他的野心越來越大。找來朋友提前寫好“我沒事兒,一切平安”的紙條留在家裏,李勇生偷偷帶著自己攢下來的零花錢和一根竹竿,獨自從天津坐火車到了哈爾濱,一路邊走邊問。
帶的盤纏即將花完,他低價從小販手裏買來一大包笛子,再高價倒手賣出。聞到飯香時,他聽聽排風扇的聲音,“聲音大的是大飯店,不去,聲音小的可以進去飽餐一頓。”
流浪一段日子,再安然無恙地回家,李勇生證明了自己“能行”,從那之後,家人再也沒有限制過他的自由。
與自己和解
聲音,在李勇生看不見的世界裏佔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在老家的那些年,每當暖風吹到身上時,他便一個人走出家門,憑藉腦海中的地圖去“有聲音的地方”。
當聽到“嘩嘩”的聲音,感受到周圍的溫度也降了幾分時,他便知道此行的終點到了——河邊一棵茂密的大樹。他拍拍腳下的泥土,找到最柔軟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去就是幾個小時,頭頂不時傳來“沙沙”的聲音,他知道,綠葉正在風中舞動。
不出門的日子,最好的夥伴就是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打開開關,相聲、評書、二人轉一股腦地闖進他的世界。
深夜收音機裏心理諮詢節目最多。一次撥打電臺熱線時,李勇生連線上了心理諮詢專家,談及未來,專家説,不如做一名心理諮詢師。
從那之後,“心理諮詢”這幾個字在李勇生心裏扎了根。但真正成為一名心理諮詢師卻沒那麼容易,這條路他一走就是很多年。

李勇生的心理諮詢室開在按摩店旁邊,他説現在偶爾也接一些按摩的工作,但比以前少多了。受訪者供圖
李勇生一直記得剛開心理諮詢室的時候,自己的忐忑和無措,“既希望有人來,又害怕有人來。”
在前期通過QQ或電話與諮詢者溝通時,他不敢袒露盲人的身份。線下見面時,總會有人因為諮詢師是個無法看到自己表情、連個眼神都不能回應的盲人,而選擇離開。
進入心理諮詢階段也不順利,遇到難以理解的人,李勇生經常表現得不耐煩。他記得,一個已婚男人向他傾訴“從小到大被父母寵慣了沒受過半點兒委屈,愛花錢卻被媳婦限制”,李勇生想到自己的經歷,越聽越覺得“不可思議”,坐也坐不住,一會兒蹺二郎腿,一會兒摸摸頭,反覆拿起手機聽時間,簡直度秒如年,連對方都能感覺到他“聽不下去了”。
聽不下去,也是專業性不夠的表現,李勇生知道自己的問題。一個半路出家的盲人心理諮詢師,很多時候都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和絕大多數盲人一樣,李勇生的學業、工作沒有太多選擇。上盲校,學按摩,畢業開個按摩店維持生計,日子一眼看得到頭。“心理諮詢”的種子只能在角落裏野蠻生長。
學校沒有心理學課程,他就去圖書館找幾本盲文版心理學理論書籍,自學得一知半解。用開按摩店賺的錢買了電腦,下載大量心理學課程視頻,蒐羅全國各地關於心理諮詢講座的資訊。遇到講座費用不貴的,便背著包,拿著盲杖,千里迢迢地趕過去。
2008年,李勇生報名了中殘聯面向殘疾人的心理諮詢師培訓班。現在回憶,李勇生覺得那是段充實且瘋狂的日子。每天除了做按摩就是學習,天濛濛亮就起床,一遍遍聽視頻,直聽到能背誦下來,晚上再復習鞏固。
兩年後,李勇生順利通過三級心理諮詢師考試,2013年又考下了二級。
一次次心理諮詢,對李勇生來説,也是與自己和解的過程。他不再忌諱告訴諮詢者,自己是個盲人,聽到別人的非議與嘲諷時,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氣不過懟回去,甚至他可以笑著調侃自己失明後遇到的糗事。
女兒問他為什麼眼睛看不見,他逗女兒,“看手機看的。”年過四十,李勇生早就接受了自己是個盲人的事實,只是偶爾,他還是遺憾。
李勇生記得,一次他和妻子夜爬泰山,日出時,身邊的人都在為躍出地平線的朝陽歡呼,只有他看不見,喜悅轉化為心酸,寒冷又多了幾分。
“我不恨命運的不公,但如果可以,我依然希望能再次看到這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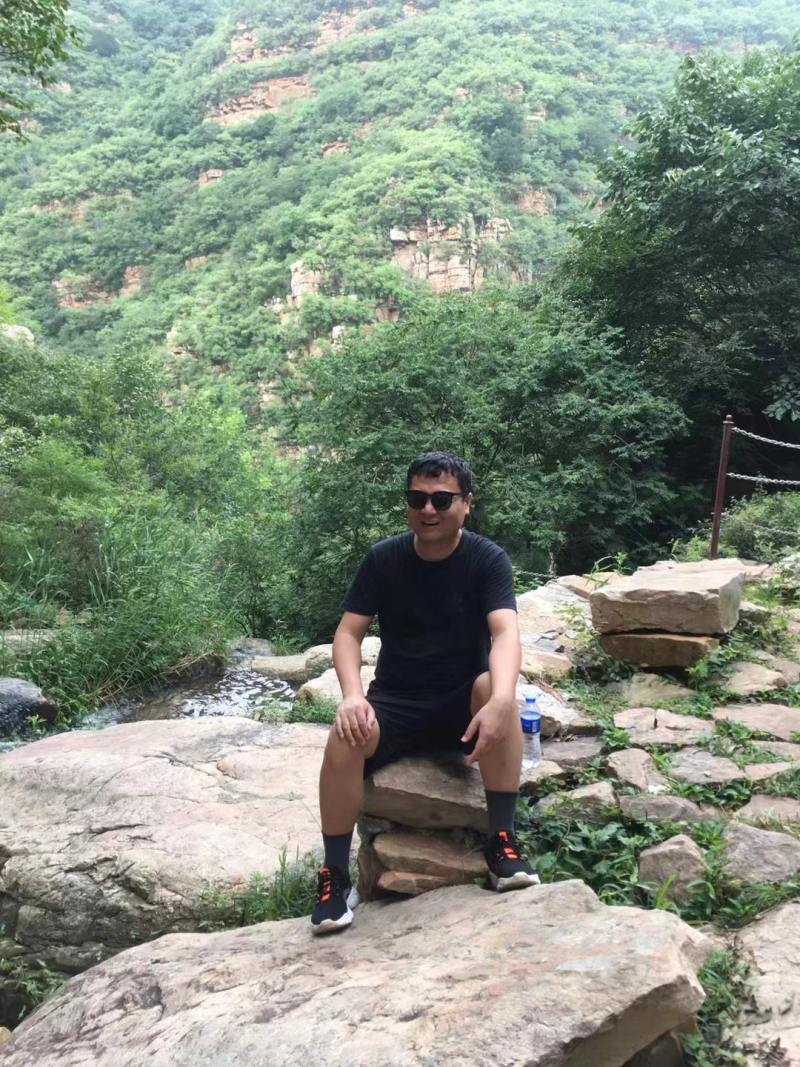
李勇生與家人外出旅遊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助人救己,就是意義”
從心理諮詢,到自殺干預,李勇生的陣地多了一條電話線。
“希望24熱線”是一條專門面向企圖自殺、有抑鬱傾向的人的生命援助熱線,全年24小時無休。電話是“400-1619995”,諧音為“要留、要救、救救我”。2015年,“希望24熱線”在天津開通專線後,李勇生立刻報名成為了首批志願者。
他還記得自己加入“希望24熱線”的第一通電話,來自一位老人,電話接起的瞬間李勇生就聽到了聲嘶力竭的五個字:“我不想活了。”
第一次面對“生死”,李勇生隨著對方的嘶吼而心跳加速,腦海裏快速閃過幾句安慰的話,隨後又被“萬一説錯怎麼辦”擠佔。他引導著老人慢慢講述,自己的語速因為緊張變得比往常快了些。
這是一位被電視購物上的假藥販子騙了半生積蓄的獨居老人。“他既然會買藥,就説明還想活下去”,李勇生冷靜了下來,抓住這個突破點問老人,“世上一個關心你的人都沒有了嗎?”
“也不是,有一個比我大的表哥,每天給我送菜送肉。”
“你看,這就是一個對你好的人,還有誰這麼做過?”
“還有……”隨著老人一一列舉,李勇生順著對方的話安慰,不到20分鐘,老人的氣消了,和李勇生平和地聊天,一場生死危機就此化解。
每一通電話背後,可能都是一條搖搖欲墜的生命。李勇生總是很謹慎,生怕哪句話説錯了,給對方帶來傷害,甚至産生不可挽回的後果。剛開始接線的時候,他緊張得手心冒汗,現在,不到1分鐘他就能判斷來電者的危險等級,並在腦海裏建立一套有針對性的溝通方案。
一個晚上,電話響起,來電者是一名貨車司機。出車禍導致高位截癱,妻子拋棄了他,留下一個8歲的孩子,天天夜不歸宿,泡網吧、抽煙、喝酒,眼看著就要走入歧途,男子喊著“我到底該怎麼辦”,隨後再也抑制不住情緒,放聲大哭。
“這是一道過不去的坎,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李勇生任憑對方發泄情緒,接線室裏安靜得可怕,只有李勇生的呼吸聲和聽筒裏傳出的哭聲。
接線結束,李勇生深吸一口氣,打開窗,風吹了進來,街上車流的聲音和人們的嬉笑打鬧聲闖進來,把他重新拉回現實世界。
不是所有人都能扛住不斷傳來的負能量,天津“希望24熱線”開通8年,接線員走了一批又一批,從最初的幾百人到如今只剩不到50人。

“希望24熱線”接線室,屋子裏的每個設施都是志願者們捐贈的。新京報記者慕宏舉攝
李勇生也難免有因為過度共情陷入負面情緒的時候,他的發泄方式是,獨自到KTV裏吼兩首歌,或者帶一瓶純糧燒酒,和朋友在地攤擼串吹牛,第二天起來,又是那個冷靜又能共情他人的心理諮詢師。
有一種情況他最害怕,就是接通電話後對面平靜而空洞的聲音,或者是長時間的沉默。
一個冬夜,李勇生接到了一個女孩的電話,女孩平靜地告訴他,自己正坐在橋上,準備跳下去,然後電話裏只剩下“呼呼”的風聲。“給我一個了解你的機會”,李勇生不停地説話,試圖引導女孩説出自己的經歷,慢慢地,女孩有所鬆動,李勇生趁熱打鐵,“你找個沒風安靜的地方,咱們好好聊。”
半小時後,聽到女孩走下大橋來到公交站,李勇生狠狠松了一口氣,又一個小時,女孩終於放聲大哭,李勇生知道,他又拉回了一個人。
8年間,李勇生累計救助上千人,聽到過號啕大哭,也聽到過嘶聲大吼,甚至要承受憤怒謾罵,但他聽到最多的還是“感謝”,感謝他的傾聽,感謝他的挽救。
這是李勇生最驕傲的時刻,“每個人來到世界上,並不是簡單地吃飯睡覺,最起碼要活得有意義和價值,做一名心理諮詢師,既能助人,又能救己,就是意義。”(新京報 記者慕宏舉)
守護好家庭“微生態” 孩子出現這些情況 家長需警惕2023-12-04
關注中小學心理教師成長:工作被邊緣 待遇難保障2023-12-04
心理百科 | 當一個人反駁時,是在反駁什麼?2023-12-04
壞情緒讓心臟“變形”!被情緒影響的器官,都變成了這樣……2023-12-01
心理療愈小錦囊|這個感恩節,你感謝了誰?2023-12-01
專訪彭凱平:如何讓孩子活出更美好的生活?心理能力的培養非常重要2023-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