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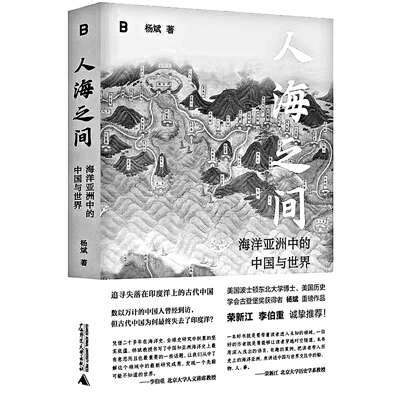

《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 中的馬爾地襪與溜山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藏龍涎香

泉州一號發掘現場

清繪本《福建省海岸全圖》中的泉州

黑石號中發現的 揚子江江心鏡
主題:海洋中國:歷史與展望
時間:2023年11月11日下午
地點:深圳市寶安區覔書店(壹城中心店)
嘉賓:錢江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
楊斌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人海之間》一書作者
海洋史,對幾千年農耕文明古國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説,是較新鮮的視域。
學術上,海洋史跟科技史、歷史地理關係較密,學者寫出來的東西相對而言又比較專門,故一般讀者對海洋史所知較少。
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楊斌的新著《人海之間——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是本有助增進普通人對海洋史興趣和了解的難得之作。
聚焦邊疆:從“彩雲之南”到雲南以南
錢江:今天我們請到香港城市大學的楊斌教授,來分享他的新書《人海之間——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聊聊與之相關的海洋史研究的一些事情。
楊斌:錢老師是海洋史研究的老前輩,這本書直接受惠于他。
2020年春夏之交,我當時正在研究中國和印度洋的關係,仔細閱讀了發現于1974年的那艘南宋沉船的考古報告。讀後好像有點新發現,我就微信錢江老師,説:“這艘船他們都説是從東南亞返航的,我倒覺得很有可能是從印度洋返航的。”錢江老師説:“你寫,寫出來我推薦到《海交史研究》去發表。”我幾週之後就寫了,也順利發表了。
一年過後,2021年7月福建泉州申報“世界遺産名錄”成功,我把這篇文章在公眾號上發了一下。被澎湃新聞編輯彭姍姍看到了,她鼓勵我把它寫成通俗易懂的文章。於是就開啟了我在“澎湃”的海洋史隨筆系列。寫到十幾篇,出版社的楊曉燕老師就聯繫我,要把它出成一本書。
錢江:中國寫歷史研究論文、論著的教授或學者,我估計幾萬到十多萬都有,但是能像楊斌教授這樣坐下來、願意真的花時間把學術界很枯燥嚴肅的考證變成大家通俗易懂的著作的,真的很少。這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很辛苦。我非常佩服。
楊老師做博士論文是在美國東北大學,寫的是從歷史維度上、從全球史眼光切入看雲南,後來卻轉寫海洋史,這轉變是怎麼發生的?
楊斌:與人生道路一樣,純屬偶然。
我當年去美國讀博讀的是世界史。美國的世界史就是現在所謂的全球史,強調文明之間的交流,而交流的主要場所就是邊疆——多個族群交流的地方,最容易有文化的碰撞。
北疆,比如長城,族群眾多,浩瀚如海,猶如繁星,倏忽漫天,倏忽不見,很難把握。加之語言難度——有些甚至是死的語言、沒有文字記錄。所以北部邊疆無法做。
我往南邊看,主要是西南邊疆——雲南、貴州這邊。我突然發現它是相對固定的,政權關係也相對簡單,相對穩定,語言主要以漢文材料為主,所以我就做雲南。
我把雲南放在東南亞和中國之間——不僅僅從中國的角度看雲南,還要從印度洋的角度看雲南,甚至還要從中亞、從青藏高原的角度看雲南。我當時就寫了全球視野下的“雲南”是怎麼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怎麼成為中國民族融合、“56個民族56朵花”這樣一個共同體的象徵和隱喻的。
做完以後,我到了新加坡工作。新加坡給我很大的觸動。因為新加坡是東南亞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是華僑社會、華人國家,我開始觸及到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東南亞又是位於中國和印度洋世界之間,所以我把眼光放到中國-東南亞-印度的三角關係上,這時候我開始涉及到海洋史。
這個過程差不多二十年。因為我初到新加坡時對海洋史一片空白,什麼都不知道,慢慢開始摸索。回顧一下,就是從“彩雲之南”到雲南以南——東南亞、南海、印度洋的這樣一個過程。
為什麼只有印度洋才“出産”龍涎香
錢江:《人海之間》特別詳細闡述了海洋亞洲在中國—印度洋之間扮演的特殊角色。而馬爾地夫群島始終在其中佔據中心角色,他即將出來的英文著作就是以此為焦點。
楊老師不僅看正史,也很注意看航海遊記。無論阿拉伯人還是歐洲東來者的航海遊記,都包含非常多豐富有用的記載。此外還有一些小説,比如《三和太監下西洋記》等,楊老師都把它用上了。
所以他有時是很嚴肅地考據、考證和分析,有時是一段段故事穿插其間,包括馬可·波羅等。一下子就顯得相當豐富有趣。這讓我覺得楊老師眼光獨到。
請楊老師簡單講一下龍涎香的故事。
楊斌:抹香鯨吞食一些大的食物比如章魚、墨魚(可以長達幾米)後,一些硬的骨骼消化不了、刺激消化道分泌,就形成了龍涎香。抹香鯨必須把它吐出來或排泄出來,否則就要生病甚至死亡。龍涎香是漂浮在海上的,漂浮在海岸、島嶼、沙灘上,被人發現和拾取,被稱為“海上的黃金”。
唐宋時期龍涎香就傳到了中國。宋徽宗發現內庫裏有一種一小顆一小顆的香,不知道是什麼,一問説是龍涎香。他不知道龍涎香是好是壞,就分給大臣們。大臣們一用,發現這麼香,宋徽宗就後悔了,又把龍涎香要了回來。宋徽宗的時代,龍涎香非常昂貴,一兩黃金、一兩龍涎香,而且是有價無市、你買不到。後來鄭和下西洋,從印度洋上的島嶼比如馬爾地夫,得到龍涎香帶回明朝,永樂宣和年間,15世紀初。然後1433年鄭和下西洋被叫停,再度海禁,龍涎香也就基本上不再在中國出現,至少從文獻上看是這樣的。
我開始研究時想,龍涎香這麼有名,肯定有人研究。再去找資料,發現並不多,主要是研究澳門史的金國平、吳志良老師,他們論述了龍涎香如何在葡萄牙人獲准入居澳門這件事上起到關鍵的作用。
至於龍涎香是從哪來的,這個問題大家講得很少。而我如果説有一點貢獻,主要是厘清一件事——為什麼“只有印度洋産龍涎香”?
東南亞海域,肯定也産龍涎香;在南太平洋、東太平洋、西太平洋的那些小島上,肯定也有龍涎香。但是沒有記錄。因為“龍涎香被人類所認識”,是不僅要被人類發現,還要被消費,這個發現過程、消費過程記錄下來,現代的人才知道。
而從印度洋到太平洋沿岸,能夠用語言記錄的民族非常少,是阿拉伯人首先用自己的語言記錄龍涎香。因此,龍涎香雖然在全世界幾大洋都有産生和發現,但它的消費、命名,是由印度洋世界的阿拉伯人完成並傳開的——幾乎全世界的“龍涎香”一詞,都是源於阿拉伯人的命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印度洋才“出産”龍涎香。
為什麼中國沿海的大量沉船都是福船沒有廣船?
錢江:楊老師在書中提到了三艘船:
第一艘上世紀70年代在福建泉州後渚港被打撈出水,後被命名為“泉州一號”。正是因為這艘沉船,在泉州成立了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中國學者對海洋史的研究慢慢走向正軌;第二艘是中國學者命名的“黑石號”,西元9世紀阿拉伯式海船;第三艘是20年前發現、現已成功整體打撈、現在廣東海寧島的“南海1號”。
楊老師在書中提到福建的福船還有廣東的廣船。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無論在中國沿海還是東南亞,現在找到的大量沉船中,廣船一艘都沒有,都是福船。
福船在製造工藝上有很鮮明的特點:
一是水密隔艙,即遇到颶風或船隻觸礁,導致船上的某個艙位破裂進水,海水不會灌進其他的船艙,水手們可以把海水排出去,然後再把洞口堵起來;再有一個就是船型。福船和廣船都是V字型,下面是尖的。只有這樣的海船才能夠遠洋航行,因為在海上碰到狂風巨浪的時候,帆船能很好地保持其穩定性。雖然船隻上半部在劇烈地搖擺,但它不會沉沒。若換成江蘇至天津沿海的平底沙船就不行了,平底沙船穩定性不好,頭重腳輕,遇到狂風巨浪,若船隻搖晃的角度較大,三兩下就翻船沉沒了。
福建沿海建造的海船若遠到印度洋或東南亞去貿易,因為必須等季候風轉換,船隻一來一回需要一年的時間。福船回港之後要進行維修,在已經受損的舊板上加釘一層新板鞏固。就這樣,每遠航一次,福船回來後就得加釘一層船板,一層一層地往上釘,加釘至第六層,這艘福船就不能再遠航,否則不安全。但是,仍然可以用於在中國沿海航行。
多層板結構的維修方法只見於福船。所以,老水手和造船工匠就以這一點來區別福船和廣船。從史料記載來看,廣船用的材料比福船好。福船就是用松樹、杉樹,在山上到處砍得到,而廣船用鐵力木。如果廣船和福船相撞,肯定是福船碎掉,廣船一點事都沒有。但是鐵力木不好找,廣船的造價高。
我和一些造船的老師傅,以及研究中國造船史的學者、教授們,有一個微信群。經常發現老師傅們為了造船,在微信裏吵架吵得面紅耳赤。後來才發現,造福船的工匠不説褔船是怎麼造的,造廣船的也保密,到今天還在互相封鎖。
楊斌:“黑石號”是阿拉伯式的縫合船。我記得錢老師寫過一篇文章,在泰國灣發現另外一艘阿拉伯式的縫合船。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嗎?
錢江:那艘船不能説叫出水了,因為是從淤泥裏挖出來的。因為過去幾百年整個泰國灣的海水一直往下退。原來是大海的地方,今天變成陸地。
當時是一對泰國夫婦在靠近海邊的地方辦一個很大的養蝦廠,隔一兩年就要在冬天深挖一次,把塘裏的泥挖起來,疏通完,洗乾淨,蝦苗要放進去。結果挖淤泥的時候發現很大塊很長的木料。他們就報告泰國文化部,派專家來勘察,發現有古船的桅桿。後來慢慢其他的船板都找到了。挖出來後發現留下來的東西不多,估計是被拋棄的船,水手們把好的東西都帶走了,剩下的都是破碎的。
一開始,包括我的老朋友、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Jim Guy,原來澳大利亞人,他是研究中國和東南亞陶瓷的專家,都發論文説這應該是阿拉伯船。我當時就打個問號,我説姑且叫阿拉伯船。因為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印度人造船是一模一樣的。這個師傅不一定是阿拉伯人。只是因為阿拉伯地方多,影響大,大家就誤認為用縫合技術的帆船就是阿拉伯船,其實未必。在印度洋西部,大量航海民族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建造木帆船。
最後物理學家、考古學家聯手,他們對選取的纜繩、檳榔等用科學手段探測分析,最後測下來是西元8世紀的船,比“黑石號”阿拉伯船的時間還要早,是目前為止東南亞海域出土的最老的一艘古船。化驗出來結果,包括船上的用品,我們詳細討論,覺得應該是波斯的古船,而不是阿拉伯船。
“黑石號”為什麼是“無釘之船”?
錢江:“黑石號”當時剛剛出來,因為是盜挖,沒有按照考古的規矩,受到國際考古學界的抵制,不讓他們展覽。他們為了賣錢,就把沉船上的瓷器拆下來,各處奔走找買家。這當然是不對的,應該原樣保存,這樣才有利於水下考古的研究。當時我是香港海事博物館董事會的成員,負責學術研究這一塊。他們就做了目錄給我們看有多少陶瓷要賣,當時出價很高,香港也沒有鬆口。
最後新加坡政府買下來了。起初沒有對外,只是內部參觀。我去看過一次,當時記得很清楚,解説註明是印度船,不是阿拉伯。到正式展示的時候我又去看,問他們“怎麼又把解説詞改成阿拉伯了?”他們説我們想來想去,這應該是阿拉伯船。
我説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麼就能一口咬定這是阿拉伯船?根據史料記載,阿拉伯很多人付錢,讓印度西南海岸的造船工匠造船。因為阿拉伯半島沒有大樹,沒有木料。印度人造完船後,把它送到波斯灣、阿拉伯半島,交給阿拉伯人。買主是阿拉伯人,造船工匠是印度人。因為造船樣式、工藝都是一模一樣的,所以船的樣式要比較小心地進行分析,不然容易擅斷。
縫合船就是“無釘之船”——一根鐵釘都沒有,完全靠繩索縫合起來,就像縫衣服一樣。
印度洋海底很多礁石是有磁性的。如果用鐵釘或其他金屬的東西包船,會被礁石吸過去,然後撞礁,在海洋中沉沒。所以波斯人留下來著作,很早就告訴他們的子孫後代,不能用金屬的東西造船,所以他們才想出來縫合船。
用來縫合的當然不是普通的繩索。而是椰子喝完汁之後,把椰殼拍散,泡在海水中,讓纖維自己散開來。再用木棍敲,把它打散。用散開的纖維搓成粗的纜繩和細的縫合船用的繩子。
這種技藝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就是楊老師一直研究的馬爾地夫群島,這是他們當地很著名的特産。這是印度洋、西印度洋在使用的縫合技術。
縫合技術並非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才有。在中國沿海也有。
所以我認為全世界、全球不同地區的航海民族,都共同發明,都享有這種很特殊的造船文化。中國的《史記》早就記載了,在今天的越南北部(當時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到海南島、廣西臨州,都是採用縫合技術來造船。
楊斌:是的,縫合船最遠到北歐,印度洋、太平洋都有,只不過因為阿拉伯最有名,是“海開工車夫”。我們生活中有很多阿拉伯人給留下的遺産,就像龍涎香一樣,由它使用、由它傳播,大家也就將錯就錯了,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當然,我們認為縫合船是阿拉伯式的,其實未必是阿拉伯人發明的,就像阿拉伯數字並不是阿拉伯人發明的(其實是印度人發明的)一樣。
海洋研究:由文獻時代進入考古時代
楊斌:剛才錢老師講了這麼多沉船的故事,正是沉船的發現使得海洋史研究從文獻時代進入到考古時代。
過去幾十年我們研究海洋史,主要是靠文獻記載,從傳統的文字材料比如説“二十四史”、筆記小説甚至各種傳奇中找材料。舉個例子,錢老師的導師王賡武先生,他的碩士論文《南海貿易》,就完全是用“二十四史”——從《史記》到《舊唐書》《新唐書》的文獻資料,寫到唐代為止。這部王先生二十多歲時的著作,距今70年了,到現在我們還在讀。
最近幾十年,南海特別是東南亞海域發現沉船越來越多,從唐代一直到近代、二十世紀初的有幾十艘,主要依賴的是海洋考古技術的絕大提高。
過去海洋考古發現沉船靠運氣,碰到了漁民撒網打漁撈上瓷器了,就知道這裡有一個沉船,然後潛水員才下去。如果水太深了,到了幾十米、上百米,潛水員也不敢下去,太危險。
前兩天,國家文物局剛剛發佈消息,我們在南海一千多米的海底發現兩艘明代古船。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正是由於海洋考古技術的巨大提高,我們可以預測會有更多沉船的發現。而沉船的發現,不僅是對過去文獻記載的補充和參照,而且它其實比文獻記錄更週詳、更直接,是最原始的資料。
錢江:中國海洋史研究其實晚清就有了。民國時期叫中西交通史,只是分為陸上和海上。姚楠先生、朱傑勤先生,以及我原來在廈門大學的老師韓振華先生,都是早期做海洋有關的。還有張馨曼,《中西交通史》六卷都是他編寫起來。
1978年“泉州一號”古船挖掘出來以後,成立了中國海交史研究會,團結一大批老中青三代的學者,開始逐步放開。
到過去二三十年,開始不再講“交通”,改叫海洋史——任何跟海洋有關聯的,包括交通、航海技術、地圖、港口、船、商品,還有移民等,都屬於海洋史的範圍。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