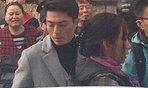啟迪之星 一個老牌孵化器的別樣玩法
- 發佈時間:2015-08-27 08:41:46 來源:新京報 責任編輯:王磊

啟迪之星董事長張金生説,當大潮退去,那些有能力的能活著的,能活得更好,但死掉一些不可避免。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近年來,一大波孵化器在不斷涌現,但前景堪憂。
8月24日,原SOHO中國副總裁王勝江辭別老東家,與創業教父俞敏洪、投資銀行專家盛希泰一起,組成豪華三人組,打造洪泰創業空間。成立當天,王勝江就“放炮”稱,現在不少同行打著“眾創空間”的名義,挂羊頭賣狗肉,“未來七八成孵化器會死掉”。
當下資本氾濫,“地主”也要競爭上崗。為博創業者歡心,孵化機構各顯神通,爭先推出“特色服務”。
但作為國內第一批孵化器,啟迪仍延續著上世紀90年代的模式,並且更看重“公益性”。令人意外的是,這家不看重賺錢能力的孵化器,賺錢能力卻驚人的好。其背後暗藏著哪些秘密?
清華老師的“情懷”
早年間,“情懷”是孵化器行業的主要標誌。彼時,年底開會都是講又服務了多少家公司、又為國家貢獻了多少人才,很少有人願意談掙不掙錢。
今年1月21日,中文線上和崑崙萬維在A股上市,湊巧的是,這兩家公司都經過了啟迪之星的孵化。
啟迪孵化器成立於上世紀90年代末的網際網路創業潮。那一年,啟迪之星總經理沈全洪剛剛考入清華大學精密儀器係,在他印象裏,周圍學生和老師的創業熱情都相當高。用一句話可以概括當時的清華,“每推開一扇實驗室的門,就有好幾個公司”。
于清華而言,創業項目放到學校裏顯然不合適,要把它們引導到圍墻外,以保持學校相對平靜的教學、科研、育人環境。
此時,清華校企平台啟迪(清華科技園)承擔了這個責任,羅建北、梅萌、李志強等一批清華老師組成啟迪孵化器的初創團隊。雙清路上學研大廈就作為啟迪孵化器最初的大本營,並孵化了幾個收益上百倍的項目。
比如,中文線上董事長童之磊,1999年清華大學第一屆大學生創業大賽的獲獎選手,當年,他得知學校要辦孵化器,便在9月,帶著自己的創業項目進駐啟迪孵化器。
幾十家企業初進到啟迪孵化器時,都是零起步,窮得叮噹響。“老師們”想到了用房租換股權、用自有資金幫助孵企業的辦法。“服務、房租、投資等,凡是能折算成股份的東西就不收錢”。
沈全洪説,“啟迪一些前輩老師如今回憶起來還常説,當時的創業者確實很讓人敬佩,不支援他一把會覺得於心不忍”。這與今天投你明天想掙多少錢的邏輯完全不同。
篤信“適度投資”
孵化器這個業態,從一開始出現就很寂寞,冷板凳坐了很多年。一開始沒人知道孵化器是什麼,當初啟迪去註冊孵化器營業執照時,一度被認為是孵小雞的,應該屬於農林牧類。
從最初政府辦孵化器到後來學校辦孵化器,孵化器的主要使命就是為了完成科技成果轉化,公益色彩濃厚,自我造血功能幾乎沒有。
2007年,當佔地77萬平方米的清華科技園建設完成開始全面運營後,啟迪開始考慮,除了樓宇經營之外,孵化器和科技服務業到底該怎麼賺錢。
沈全洪參加過內部討論。“有幾次,我們是在咖啡館裏聊,説能不能讓服務産業化,但後來被否掉了”,“小企業最缺的就是錢,還想掙它的錢,怎麼可能?”
後來,啟迪孵化器是逐漸總結出,在孵化角色不變的同時,適度參與投資,或許是一種可行的模式,而智慧財産權、財稅社保這類零碎的孵化服務就不從中賺錢了。
慶倖的是,2007年正趕上啟迪孵化器最初一些無心插柳的投資進入收穫季節,展訊通信在納斯達克上市,第一天股價就暴漲近14%。一些沒上市的孵化項目也漸漸展現出不錯的規模。
到2010年,海蘭信、數位視訊、世紀瑞爾3家公司相繼登陸創業板,啟迪孵化器曾經的投資獲得了上百倍的回報,甚至超過了地産運營收入。
2013年,啟迪推出創新型孵化器啟迪之星,也延續了“孵化+投資”模式,即先孵化後投資。
由於孵化階段的情感培養,啟迪之星能獲得低於市場價的參股價。
做“農民”不做精英
對啟迪之星來説,只選擇有把握的遊戲規則,選擇自己懂的賽道投資。
截至目前,啟迪共孵化了2000多家公司,投資了其中大概300家,完成大概20億的投資,直接上市了19家企業。啟迪投資的整體回報率也相當不錯,平均年化是40%多。
投資是孵化器一種成熟的盈利模式。對一門生意而言,找到賺錢的方式並繼續擴大,是自然而然的。但對孵化器這種從公益屬性演變而來的業態來講,向左走還是向右走,性質會變得完全不同。
啟迪的選擇是,堅持孵化為主,投資為輔。沈全洪説,“投資是啟迪孵化器的一筆生意,但生意不是全部”。
2009年,李開復帶來一種新型孵化器的理念——創新工場。李開復的玩法不同於啟迪,每個來到創新工場孵化的項目都是他已經看好或者已經約定好的投資標的,孵化和投資標準相當接近。到後來,創新工場從最初的孵化器轉型為純粹的投資機構。
沈全洪説,投資主導的孵化器好比是精英模型,啟迪之星就是農民模型,農民首先要播種,過程中再找好苗子,前期會很辛苦。但精英一上來就要選好苗子,他要在某個行業或者某個方向比所有人都懂。
“我們的組織架構一開始就不是按精英思路來的,我們沒有年薪幾百萬的投資高手,所以我們只選擇我們有把握的遊戲規則,選擇我們懂的賽道投資”,沈全洪説。
但這樣“不夠專注”的投資,結果可想而知。新京報記者從清科研究中心獲得一份2014年天使投資機構前十排名,並沒有看到啟迪之星的名字,前三分別是真格、險峰和聯想之星。
為母公司生態體系一環
啟迪的這套玩法背後,其實有更深層次的佈局。
啟迪之星母公司啟迪控股旗下重點板塊有兩個,其一為科技地産運營,其二為科技服務業。
啟迪科服集團的目的是構建一個大資本運作的平臺,考慮到未來很多公司不一定順利通過IPO退出,通過金融投行服務,以産業運作方式讓大公司收購小公司,成為一種退出渠道。
這其中,啟迪之星所承擔的使命就是蓄水池的作用。啟迪之星是科服集團的塔基,往上有啟迪創投(啟迪風險投資公司),再往上是啟迪係的多個上市公司,整個鏈條都裝在啟迪科服平臺裏。
這是啟迪目前的打法,類似于集團軍作戰。比如,啟迪科服旗下的節能環保産業鏈條已初具雛形。上層,啟迪科服集團在今年4月花70億收購了上市公司桑德環境,中層有清華陽光、亞都等一批中型公司,基層的啟迪之星也投資了一批節能環保創業公司。它們彼此可能産生的化學反應包括,打個包就能成立啟迪環保集團,還可以組團出征拿項目。
沈全洪説,啟迪的孵化器業務已經不能被單獨看待,這種玩兒法和市場上所有孵化器、投資機構都不同。
“啟迪之星現在做的工作就像在修路,先把渠道架到各個地方”,沈全洪説。一方面是把啟迪模式複製到各地,用啟迪科服的金融模型幫地方完成産業升級,另一方面,啟迪之星搭建了一個全國網路後,不僅能吸納各地創業項目,從地方輸水到啟迪科服,還能幫平臺裏各類有需求的企業對接地方資源。
一直到採訪結束,沈全洪仍在強調,啟迪之星不是一個單純的投資機構或者孵化器,它是啟迪控股龐大生態體系中的一環,不能局部地看待。
但啟迪之星又是相對獨立的,除了“對上負責”,沈全洪也要考慮它面臨的競爭和自我發展問題。
不過對於會不會趁機擴大賽道,投些高風險高收益的網際網路企業,沈全洪沒有回答。
■ 對話
啟迪之星董事長張金生:孵化器將會死掉一批
老牌孵化器“不夠吸引眼球”,讓張金生感覺到壓力。但他堅信,當浮躁退去,泡沫退去,只有那些有能力的孵化器才會活著。
被大潮裹挾前行
新京報:孵化器雖然誕生很多年,但好像從來沒有這麼火。
張金生:原來做孵化器的主體,更多的是政府,大學,國企。但在新的創新創業大潮裏,像騰訊、海爾這些大的龍頭企業,再加上各種新的模式融入進來,參與到風口裏面的人越來越多。
新京報:在這個風口上,啟迪有壓力嗎?
張金生:坦率來講,身在大潮裏面,我們自覺不自覺地也在滾滾洪流中被脅迫著前行。我們認為,其實孵化器的本質沒有發生變化。只是現在很多人在用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説法,創造了很多所謂吸引眼球的東西。所以,我們這些深耕多少年的老牌孵化器,可能不見得有創新孵化器吸引眼球,因為中國現在的環境在不斷追求概念。
新京報:你們會適應這種潮流嗎?
張金生:我們有時候也很矛盾,到底應該怎樣面對。我們原來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能為創業者、創業企業提供什麼樣的服務。但社會在追求新東西,在一個浮躁的狀態。
大潮退去會死掉一批
新京報:在這個風口,孵化器行業有沒有泡沫?
張金生:沒有泡沫,肯定不可能。國家一號召,就出來一個風口,而且中國人是別人幹什麼,就模倣。很多對孵化器運營不知深淺的熱血人士,都涌到這裡來了。
新京報:可能的結果會怎樣?
張金生:他們的涌現,一方面會進一步完善創業創新生態環境,但也有一些,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找不到好的商業模式,就會碰壁。當大潮退去,那些有能力的能活著的,能活得更好,但死掉一些不可避免。
新京報:估計熱度能持續幾年?
張金生:兩年左右。這主要受制于兩方面因素,第一,如果是宏觀經濟好轉得快,可能大家冷靜下來會快一點;另外,與這個領域現在做得不錯的一些項目最終的效果有關,如果現在很熱鬧,越到最後卻發展不太順,會讓行業降溫。
做孵化器賺快錢太難
新京報:做孵化器,盈利是不是比較大的難題?
張金生:找到適合自己的盈利模式,是很多孵化器要面對的問題。我幹這麼長時間,就覺得挺累的,做孵化器要賺大錢,賺快錢,太難了。
新京報:為什麼?
張金生:因為孵化器本身就是在幫助別人成長,多多少少帶有情懷,要耐得住寂寞,做一個長跑者。
新京報:你怎麼評價這些新出現的創新型孵化器?
張金生:很多新的模式也在不斷顛覆我們原來的思維。對這些東西,我們也是以包容的心態在不斷學習。
新京報:會不會覺得,在新的遊戲規則中,你們錯失了一些機會?
張金生:我們也在想是不是我們保守了,包括投資頻度,投資力度各個方面。新手段我們也在思考,比如眾籌平臺是否可以做。
新京報:你們現在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張金生:第一是創新創業的生態環境競爭越來越激烈了。第二,政府各方面對原有的大學科技園,支援的力度不像原來那麼大了。第三,業態的同質化,我們能做的,別人過兩天馬上也能做。在理念、做法上,已經沒有太多獨家秘籍了,關鍵就是怎樣不忘初心把它執行好,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