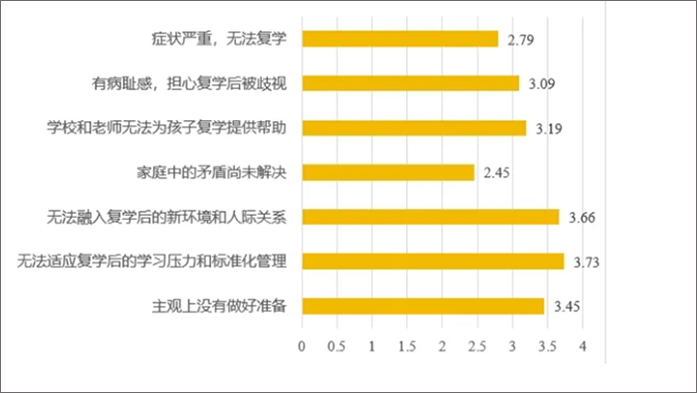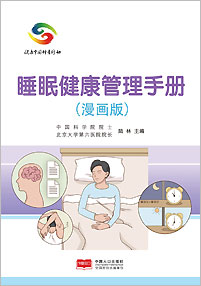心理觀察|警惕抑鬱症患者被忽視的認知困境
發佈時間:2025-10-20 10:29:34 | 來源:中國網心理中國 | 作者:譚思靜2025年世界精神衛生日全國宣傳主題為“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務”,旨在促進對常見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正確理性認知,減輕社會歧視和防止“污名化”。然而現實中,公眾對抑鬱症等常見精神障礙的認知,仍與疾病真實的面貌存在較大差距。
在多數人的認知裏,抑鬱症是“情緒感冒”,是持續的低落與悲傷。然而,真實的抑鬱症,是一場席捲情感、認知與軀體感受的全面風暴。它不僅讓人失去快樂,更蠶食著患者的思考能力、行動意願,甚至扭曲他們對自我的認知。
10月10日,第34個世界精神衛生日,記者在2025世界精神衛生日綠絲帶系列活動——“煥新認知,重回美好”公益科普活動暨抑鬱症患者藝術作品展現場,通過對兩位抑鬱症患者和他們家人的掙扎、努力康復故事的採訪以及專家解讀發現:抑鬱症,遠比想像中複雜。
看見我,而不只是看見我的問題
1995年出生的杜蔚因為長期的工作與生活壓力,在去年冬天確診重度抑鬱症,但她卻始終陷在自我懷疑的漩渦。“我真的有病嗎?”這種懷疑並非因為她症狀輕微,而是因為她的表現與大眾對抑鬱症的刻板印象不同。
“我並不像其他抑鬱症患者一樣擁有嚴重的軀體化症狀。偶爾情緒正常,甚至與朋友相處時能感受到快樂。”這種“不一致”加深了杜蔚的自我懷疑。親友“想開點”的勸慰反而加劇了她的自責:“為什麼我會生病?是不是我心眼兒太小,過於敏感?”她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在利用疾病逃避現實。“我對自己感到厭惡。我懷疑自己沒有生病,只是為了逃避困難找藉口。”杜蔚説。
之後,杜蔚感到自己的社交功能開始受損。如同“祥林嫂”般不斷傾訴痛苦,時常讓她擔憂朋友是否已對自己心生厭煩。“但很快,我又會因這些對朋友的無端揣測陷入內疚。”認知功能下降加劇了痛苦,“有時與人交談,我難以理解對方意思,感覺自己遲鈍、笨拙。”
“我整天躺在床上睡覺,媽媽覺得我太懶了。”家人的不理解使情況雪上加霜,“一切都令人疲憊,我累到不想跟任何人任何事産生任何交集。”然而,獨自一人時,杜蔚又會覺得自己或許只是懶惰,缺乏自律,“可能我需要學習一下時間管理”。
她不停地更換醫院和醫生,一遍遍地詢問醫生自己到底是否患病,又或許只是為了逃避問題和困難在找藉口?醫生告訴她:“你從進門開始,就一直在反覆詢問,質疑自己是否患病,其實我已經很多次回答過你的問題了,你確實生病了。你很難受,你應該相信自己的感受。”
與杜蔚的自我懷疑不同,封小達已經戴著“抑鬱症”的標簽生活了12年,最嚴重時他曾一度退學。
封小達的成長環境充滿不穩定因素:“小學二年級時,母親被診斷為抑鬱症。”父親每日朝六晚九工作。作為雙胞胎中的哥哥,封小達被迫承擔照顧妹妹、理解母親的責任,壓抑真實感受,“必須像成年人般承擔各種情緒”。
封小達向記者回憶小學放學時的場景:“一推開門,我就看見母親很無力地癱倒在沙發上,雙手垂落,默默流淚。”年幼的他撲入母親懷中,母子相擁而泣,他並不理解母親為什麼痛苦。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自己、對母親都産生了更多疑問,“我會惱羞成怒:為什麼你總是生氣?為什麼總是不快樂?”母親持續的悲傷讓封小達痛苦不堪,而母親也同樣無法理解他的痛苦。
高三時,封小達內心所有壓抑的痛苦徹底爆發。開學首日,他拒絕到校。封小達告訴記者,那段時間,家人極端的做法讓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回到校園正常學習。
“看見我,而不只是看見我的問題。”封小達講出了許多抑鬱症患者的心聲。很多抑鬱症患者的身邊人,他們都只看到這個人變了,變得跟以前不一樣,變得問題頻出,卻看不見那個痛苦至無法行動的“人”本身。
情緒低落背後是認知、社會功能的嚴重受損
氣溫驟降的秋冬季是抑鬱症的高發時段,但因季節性情緒失調而産生的“抑鬱情緒”卻並非都是“抑鬱症”,北京回龍觀醫院中西醫結合科病區主任、副主任醫師呂夢涵向記者解釋:“季節性情緒失調或是情緒抑鬱並不能簡單等同於抑鬱症。前者往往誘因明確,並且通過安慰等,當事人的症狀很快會得到緩解,不會對生活造成很大障礙,他們通常也無自殺傾向。後者症狀則更為嚴重,飲食、睡眠、精力、情緒等均會受到影響,持續時間兩周以上,對當事人生活造成很大影響,並且無法自行得到緩解,需要醫生和藥物的輔助。”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首席專家鄭毅認為,“公眾對抑鬱症還存在普遍認知偏差。情緒波動不等於抑鬱症。抑鬱症狀發生率約30%-50%,但抑鬱症的患病率僅3%-6%。”
“抑鬱症表面是情緒疾病,但情緒背後是認知功能與社會功能的嚴重受損。”鄭毅向記者強調,抑鬱症包含三大核心症狀:情緒問題、認知問題(自我評價降低、認知功能下降、思維遲緩)以及行為問題,如運動遲緩或激越煩躁。
鄭毅特別強調認知功能損傷的危害:“認知功能是我們對社會、世界的判斷,認識與溝通的腦功能,主要表現為注意力集中程度、記憶力、執行功能、做事效率以及對事物的判斷加工能力。”這些認知功能損傷症狀在抑鬱症早期即可能出現,卻最易被忽視。
“常見情況是,抑鬱症患者通過藥物治療,情緒往往快速改善,但動力不足、認知未恢復,患者會産生更錯誤的判斷,認為自身徹底損壞,疾病無法治愈。”治療方面同樣存在誤區,鄭毅教授告訴記者:“傳統評估只關注自殺意念是否緩解等,實則患者可能仍效率低下、功能不全。”抑鬱症患者真正的康復應包含情緒緩解、認知功能恢復與社會功能重建。
抑鬱症的恢復期比較長,鄭毅談道:“急性治療期約8-12周,鞏固治療期約6個月,維持治療期需兩年以上。”他特別強調抑鬱症復發率高達“50%-85%”,持續治療至關重要。同時也注意不可隨意停藥,“抗抑鬱藥不具有成癮性,會産生藥物依賴的觀點是錯誤的。若突然停藥,會導致嚴重的‘撤藥反應’”。
被理解、被接納是抑鬱症患者功能重建的關鍵一步
封小達的病程轉折發生在從澳大利亞留學歸來時。“回國前一個月我已無法下床”,更嚴重的是,“我睡的床塌了一角,我都沒有力氣修復,甚至無力將床墊移到平地上,我就在傾斜的床面上一直躺著”。
當他向母親求助時,出乎意料地,她立即回應:“如果實在難受,現在、立即回來。”這與封小達過去的經歷截然不同:“過去母親只接受我以良好的狀態出現,十分拒絕接納我的糟糕與痛苦。”
回國後,封小達發現母親開始學習心理學知識,“她嘗試理解我”,儘管這種理解最初僅是機械重復地在抑鬱症家屬微信群喊口號,比如“有求必應,無求不擾”,但逐漸地,“我發現她開始允許我、接納我的碌碌無為和平庸。”封小達説。
這種“允許”體現在具體行動中。封小達確診抑鬱症後出現嚴重進食障礙:“我會暴飲暴食後再催吐,吐完再吃。因為我深度抑鬱臥床時,總感覺與世界隔著一層厚牛皮,對我來説,催吐帶來的痛苦是喚醒我存在感的最有效方式。”
觸動他的是,母親不再阻止他催吐,而是“陪伴在側,不加阻攔,甚至陪同進食”。這種陪伴産生轉變性影響:“我能感受到她的理解,她開始允許我、接納我停留在痛苦糾結的狀態,她不再試圖解決我身上的問題,而是真正與我並肩,給予支援。”封小達説。
“有一次,母親在午飯後回屋摟著我入睡,1米9的我與1米6的母親,我蜷縮在她懷中。”封小達告訴記者,這種被母親擁抱的體驗讓他十分有安全感,“讓我體驗到了久違的、純粹的母愛。”他説。
隨著家人的陪伴和理解,封小達開始進行自我認知的重構。“我開始不再用受害者敘事來思考問題。”這種認知轉變是康復的關鍵。“以前,母親替我找過很多精神科專家,但我拒絕就診,認為她在控制我。後來我逐漸意識到這是我自己的事,並且我希望自己變好。”
封小達最終重拾生活的熱情與動力:“我今年騎行了2000公里,從山東到浙江。”他的感悟充滿了希望:“人生無法選擇起點,但可選擇未來如何生活。即便起點較他人艱難,需承擔困難的人生課題,我仍能決定自己的幸福。”
鄭毅強調,抑鬱症患者自救首先需正確認識疾病:“要在情緒背後識別症狀,不忽視疾病表現,也不過度敏感。”他建議,可使用PHQ-9等專業量表進行初步評估,但明確“量表不能替代醫生診斷”。
針對認知障礙,鄭毅表示,可通過專業認知訓練來改善,同時社會功能逐步恢復至關重要。他特別強調:“保持治療信心”,治療過程中“避免過度用藥,及時與醫生溝通調整方案”。
抑鬱症是涉及情緒、認知和軀體多方面的系統性疾病。封小達與杜蔚的經歷,鄭毅與呂夢涵的講解,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唯有撕掉“情緒低落”的單一標簽,看見背後複雜的認知損傷與軀體困境,理解患者作為“完整的人”的痛苦,才能實現真正的療愈。這不僅是醫學問題,更是一種深刻的社會認知。當社會與個體都能學會“看見我,而不只是看見我的問題”,我們才能為身處陰霾中的人,點亮回歸正常生活的道路。
封小達在患病期間加入了“渡過”抑鬱患者社區,跟病友互相分享、交流經驗。如今病情好轉後,他開始在“渡過”擔任志願者,幫助更多病友。(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杜蔚、封小達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 記者譚思靜)
“反向成長”風潮興起:小學生嫌棄的,對於成年人剛剛好?2025-10-20
心理好書丨告別玻璃心,提升心理免疫力,助力孩子健康成長2025-10-20
記者手記:懂得抑鬱症這種病,才能給予真正的支援2025-10-20
圖説心理丨關於抑鬱症治療、用藥 專家劃重點啦2025-10-20
心理觀察|警惕抑鬱症患者被忽視的認知困境2025-10-20
心理問答 | 給孩子手機,不妨先立這三條標準202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