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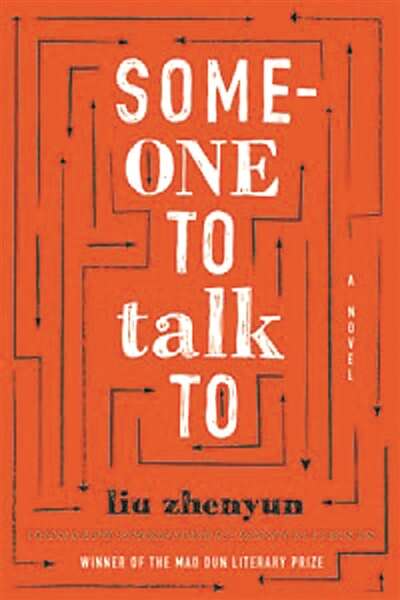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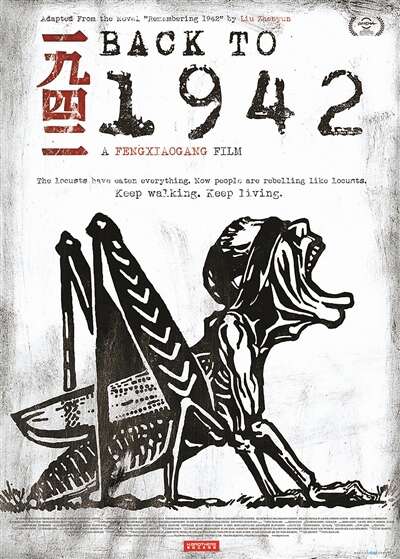
日前,著名作家劉震雲走進北京大學,來到“小説家講堂”的課堂,發表了“文學與哲學的量子糾纏”為主題的演講。本次講座也是“第三屆王默人-周安儀世界華文文學獎”系列講座活動的第一講。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文學與哲學的量子糾纏》。
所謂“量子糾纏”,指的是二者之間的穿越、交叉、混合。什麼是文學?通俗的説法是:文學是生活的反映。確實有一些文學作品是生活的反映,但是如果文學僅僅是生活的反映,這樣的作品一定是三流的作品。所以,我經常説一個觀點,好的文學出現在生活停止的地方。生活在什麼地方停止呢?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同一個情緒、同一個思緒在生活中,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反覆琢磨和思考,過去就過去了。但是文學,它有時間把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同一個情緒、同一個思緒來分析和碼放。
◤我從來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有誰聰明◢
我還有一個觀點就是,好的作家一定要嗜學。他一定要有足夠的知識和見識,知道孔子、柏拉圖、休謨、康得、薩特這些哲學家(這幾個人水準差不多)。知道他們,才能知道世界上什麼人對這個世界進行了怎樣不同角度的思考,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經常看一些作品,開篇寫得很好,中間就不行了,到後面就塌方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有一些作家,第一部作品寫得很好,第二部、第三部就不行了,為什麼呢?
當然可以牽動很多原因,有人説缺乏生活,要體驗生活。我覺得生活不用體驗,生活永遠撲面而來,誰也沒有生活在另外一個星球上。今天我來北大不是生活嗎?有人説我參加綜藝節目。其實,這不也是體驗生活嗎?新形態的生活。
我參加脫口秀有很深的體會:脫口秀演員真是不容易。呼蘭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英文説得比中文還好,又回到中國用中文説脫口秀。我覺得這個關係的結構有意思。還有徐志勝,長得跟潘安似的。相聲一般是調侃對方、調侃捧哏的,但脫口秀演員都是自嘲,説自己的長相,説自己遇到什麼糗事,把祖宗八代幹的那些不靠譜的事從頭到尾給捋一遍,從裏邊找個笑點讓別人笑。我看脫口秀演員似乎看到了魯迅。魯迅先生説嚴於解剖自己,要勝過解剖別人。脫口秀演員像解剖青蛙一樣在解剖自己,這不容易。我去了一趟脫口秀大會,對他們充滿了同情,也充滿了尊敬。
所以,到底是為什麼呢?許多作家總會把自己説成是一個寫故事的人。很對,但是每個人寫作的出發點是非常不一樣的。寫故事的人,他遇到了一個有意思的人,遇到了一個有意思的故事,包括天上飄過的一朵雲、一段情緒、一個私心、一縷炊煙都可能讓他寫東西。但我不是這樣的,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支點,這個支點就像阿基米德説的,你有一個支點能夠把地球撬起來,能不能把地球撬起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起碼能夠把一個小説給撬起來。這非常重要。
作家寫到一定階段,你會發現語言對於小説的意義也不重要,通過專業的訓練形成語言風格沒有問題;故事感人也很容易達到;最難的是故事的結構和人物的結構——這最考量一個作家思辨的能力(文學和哲學的量子糾纏在他身上的體現),當然也包括他知識的廣度與格局。
思想和認識支撐著寫作。你有多大的見識、有多大的格局、有多大的知識儲備,決定著你的輸出。這個輸出甚至可能只佔據你儲存的百分之一。如果你連古今中外那麼多的聰明人,他們認識的角度和深度、廣度,以及他們的視野都不知道,僅憑自己的小聰明,是不可能寫出好作品的。我從來不承認這個世界上有誰聰明。
◤文學的底色一定是哲學◢
文學的底色一定是哲學。白居易《賣炭翁》裏的兩句詩,“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這兩句詩好就好在充滿著哲學的思辨,一個賣炭翁,風雪天在街上叫賣,衣服很單薄,但盼著天氣更寒冷一些,為什麼?因為炭好賣一些。
《琵琶行》中寫“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反映了一個哲學思辨,人和人之間的相知和時間的關係,每天在一起工作了幾十年的人,未必相知,第一次見面卻成了那麼知心的朋友。他和她根本沒有説話,是怎麼相知的呢?通過“大珠小珠落玉盤”。“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聽哭了,而且是青衫濕,不是衣袖濕。
李商隱有一首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君問歸期未有期”是過去現在時,過去沒有微信,也沒有手機,妻子一封信寄到這裡;“巴山夜雨漲秋池”是現在時,“何當共剪西窗燭”是現在將來時,“卻話巴山夜雨時”是將來過去時。對於時空、對於命運的感觸,我覺得是相當了不起的。另外還有一種説法,他收到妻子這封信時,妻子已經去世了,詩中所寫是一種想像。如果是一種想像,這個詩的價值又翻了一倍。
凡是好的詩一定不單是情感和情愫的表達,一定有哲學的思辨。李白寫得最好的兩句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這兩句都是千古名句,就是我們見不著唐朝的月亮,但是這個月亮曾經照過唐朝的人。唐朝有個不是特別出名的詩人陳陶,他寫過“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無定河在陜北,當時的塞外,人已變成了白骨,而在洛陽或長安,一個人春回夢裏,以為他還是活著,還會回來。真正可憐的是這“閨中人”。
2016年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多人覺得評委瘋了。千萬別遷怒,先仔細想一想,仔細讀一讀鮑勃·迪倫、聽一聽鮑勃·迪倫。他去年出了一本書《現代歌詞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s)。他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手,他的詞寫得非常好,其中有一首《答案在風中飄揚》(Blowing in the wind):
一座山要佇立多少年,才能被沖刷入海;(快趕上李白了)
一些人要存在多少年,才能獲得自由;(快趕上曼德拉了)
一個人要回轉過多少次頭,才能假裝什麼都沒看見;(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答案啊,我的朋友,在風中飄揚
答案在風中飄揚。
另外,這個世界上的好作家,不但作品寫得好,作品的名字也取得不同凡響。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我沒讀的時候,以為是寫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像林黛玉和賈寶玉一樣的故事,但不是。他寫的這個“紅”是blood(鮮血),寫得驚心動魄。還有一個中國作家李洱,他的小説《石榴樹上結櫻桃》,這個作品名字也讓我非常震動,為什麼石榴樹上能結櫻桃?
但是,我説文學的底色是哲學,並不是説要把文學寫成哲學。我的另外一句話是:哲學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文學的底色是哲學,但哲學停止的地方,文學出現了,這也是一個量子糾纏。
哲學在什麼地方會停止呢?哲學力圖要把這個世界説明白,不管是《論語》,還是《道德經》,都力圖把世界深處的道理説明白。哲學説不清的事是哪些事呢?比如人的內心、人的情緒、人的情感、人的私心、人的思考和人的靈魂,都是哲學永遠説不清楚的。哲學説不清這些事誰來説?文學。赫拉克利特有一句話説得特別好,你永遠找不到靈魂的邊界,即使你找遍所有道路,也是如此。因為它的原因隱藏得非常之深。
◤文學中的“目光”:介入者與出走者◢
另外,文學中是有“目光”的。比如魯迅先生,他跟他同時代的作家有很多區別,特別是和他同時代的鄉土文學作家——當然他們也寫得非常好,但他們寫的就是鄉土文學,而魯迅先生寫鄉土寫出來的是世界性的作品。區別是什麼呢?區別並不是魯迅先生對農村的生活比那些作家更熟悉,而是魯迅先生作品中的目光和其他鄉土作家的目光是不一樣的。其他鄉土作家是從一個村來看世界,魯迅先生是從世界來看一個村莊,所以他就寫出了像阿Q、祥林嫂、孔乙己這樣的人物。
就我自己而言,寫到《一句頂一萬》的時候,感覺稍微開竅了一點。《一句頂一萬》寫的是一些不愛説話的人,比如與賣豆腐的、殺豬的、剃頭的、染布的、破竹子的,還有傳教的。我們村的人都不大愛説話,包括我也不愛説話,因為他説話不佔地方,他説話也沒有人聽,他把對話變成了自言自語,久而久之在尷尬和自嘲的情形下,他也就不説話了。
但不愛説話並不是説他沒有話。那他的話哪去了?他的話被咽進去了。過去有一句話説“打碎了牙往肚子裏咽”,“打碎了的話也在往肚子裏咽”。不愛説話到了肚子裏就變成了心事,那麼多不愛説話的人都在大街上走,萬千心事匯成萬千洪流,改變著生活,決定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這是一個哲學的辯證思考。
《一句頂一萬句》裏我寫了傳教士老詹的故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確實有很多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其中一個傳教士來到了河南延津,他是義大利米蘭人。義大利人的名字都特別長,延津人嫌麻煩,叫他老詹。老詹來的時候眼睛是藍的,黃河水喝多了,就變黃了;來的時候,鼻子是高的,但老在河南吃羊肉燴面,就變成了一個麵糰。四十年過去了,老詹在街上走,背著手,和一個賣蔥的老頭沒有任何區別。他來到我們延津四十年就發展了八個信徒。
他在黃河邊遇到了一個殺豬匠老曾,就説,老曾你信主啊。
老曾説,信主有什麼好處?(這是中國人的思考習慣)
老詹説,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誰,從哪來,到哪去。
老曾説,不信我也知道,我是老曾,從曾家莊來,到各村去殺豬。
老詹説,你説得也對,那你總不能説,你心裏沒憂愁吧。有憂愁你不找主找誰呢?主馬上告訴你你是個罪人。
老曾又急了,我跟他一袋煙的交情也沒有,咋知道錯就在我呢?
老詹的教堂後來被縣長征走了,他就住在一所破廟裏,每天給菩薩上炷香:菩薩,保祐我再發展一個教徒。他心中的教義無處訴説,每天晚上用義大利文寫信,寫給遠在米蘭的他妹妹的孫子。正因為他在延津把主的福音説出來了,所以他對教義的理解非常深刻。這些深刻和獨到的理解,漂洋過海回到米蘭,進入一個八歲孩子的世界。八歲孩子覺得老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他的信徒有幾千萬,他的教堂一定像米蘭大教堂一樣雄偉。老詹去世了,那些殺豬的、磨豆腐的、剃頭的去給他辦喪事,發現一張圖紙,就像米蘭大教堂一樣宏偉的延津第二教堂的圖紙。這時候,圖紙活了,塔頂上的大鐘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
老詹確實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他傳教沒傳給別人,但傳給了他自己。什麼地方最適合傳教,在不信教的地方。這個地方,有老詹的介入和沒有老詹的介入是非常不同的。
《一句頂一萬句》出法文版的時候,我去法國一個書店交流。一個法國女士站起來説,你知道我們老詹他妹妹的孫子現在幹什麼?我説不知道,因為他在書裏就是一個收信的小孩。那位女士説,他現在就是米蘭大教堂的大主教。聽了之後我特別震撼,也特別自責,覺得《一句頂一萬句》沒有寫好——哲學和文學的量子糾纏在我這裡出現了。如果我當時能知道有這樣的人物結構、知道八歲小孩未來成為了米蘭大教堂的大主教,如果我當時有這樣的視野和格局,《一句頂一萬句》又不一樣了。
所以孔子有一句話説得很對,“吾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對的,“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對的——但確實存在著不同的“道”。當你寫這個作品的時候,你肯定是想把它寫好,但是你回頭看也會有很多遺憾。當然缺點並不是壞事,失敗也不是壞事,它是寫下一部最大的動力。
◤不是死了三百萬人而是一個人死了三百萬次◢
最後,我想談談幽默。全世界都知道我很幽默,那是他們沒到我們村去——我是我們村最不幽默的人。幽默分很多層面:首先,是語言的幽默,但我的作品裏沒有一句話是幽默的,而是後面的故事結構和人物結構的幽默。當然,最好的幽默是結構背後道理的幽默。
小説《溫故一九四二》寫了河南饑荒那麼大的災難,但能夠看到這個小説裏的幽默。為什麼呢?那是因為生活背後的道理就很幽默。1942年因為旱災和國民政府賑濟不力等原因,河南死了三百萬人。我認為,用哲學的理論來解釋,其實不是死了三百萬人,而是一個人重復死了三百萬次。死了三百萬人是一個事實,一個人死了三百萬次是一個思考。因為這三百萬人的死法、原因、動因,包括最後的結果是完全一樣的。能讓一個事在同一片土地上重復三百萬次,而且是死亡,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他們會用這種幽默的態度來對待三百萬次的重復死亡?
在寫小説之前我回了老家,想問問1942年的倖存者,比如我的外祖母。我説,姥姥我們聊聊1942年。1942年是哪一年?餓死人那一年。餓死人的年份太多了,你到底説的是哪一年?遺忘比殘酷更觸動我。人對恐懼的恐懼是一種恐懼,對恐懼的遺忘是另一種恐懼。
行,我説為了遺忘我就試試吧。接著我就把從1940年到1945年的世界範圍內的文獻都看了,包括《泰晤士報》《民國日報》,以及國民黨政府的文件等等。看完之後,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大和小”之間的哲學問題:對一個區域來講,三百萬人很重要,特別對我們河南人而言;但是1942年發生了很多事:史達林格勒戰役、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等等,從《紐約時報》一直到《泰晤士報》,所有世界的新聞都集中在了史達林格勒,集中在了宋慶齡訪美,集中在了甘地絕食。有報道説丘吉爾感冒,卻沒有一個小豆腐塊在説河南,那就證明河南死了三百萬人,在世界的格局中是不重要的,對蔣委員長也是不重要的,他需要處理的是跟美國、英國、蘇聯之間的關係,包括進入膠著狀態的中日戰爭——那些事情稍微處理不好,中國就會向別的方向偏離。但在內地死了三百萬人,不會影響世界的格局。我突然發現他們不是因為旱災餓死的。
這些是別人對待我們的態度,我們自己對待自己是什麼樣的態度呢?我發現他們臨死的時候沒有責怪任何人,不遷怒,而是想起了自己的同鄉——他三天前就餓死了,我比他多活了三天,我值了。這麼大的災難,最後用一個笑話説出來;這樣的幽默,悲涼、殘酷。餓死的人、受災的人,他們對待自己的態度,比對待別人的態度和世界對待他們的態度更加重要。
電影《1942》中,大饑荒過去後,蔣介石(陳道明飾)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飾)在橋上的一段對話。蔣介石問: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河南省主席答:政府統計1284人,實際300萬人。這樣的幽默是從故事結構、人物結構,包括人性和靈魂的縫隙中透出來的一絲冷風。當你用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嚴酷的事實時,嚴酷會變成一堵墻,雞蛋撞上去就碎了。當你用幽默的態度來對待嚴酷時,幽默就像大海,嚴酷會變成冰,它掉到幽默的大海裏,融化了。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