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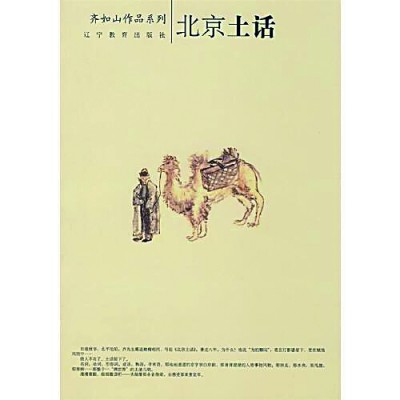
北京話,與北京建城史聯繫在一起,與北京的歷史風雲聯繫在一起,特別是與歷代的北京人聯繫在一起。從薊燕語,到幽州語、幽燕語、大都話,到明、清北京話,及至當代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多少腔調音韻的溪流匯成了北京語言的長河。
北京話源頭——“薊燕語”
北京話的源頭,出自我國古代邊邑“薊丘”的“薊燕語”。
我國古代,北京地區被稱為“幽陵”。幽者,深遠也;陵者,丘陵也。相傳,帝堯時代在幽陵一帶建“幽都”,顧名思義,它應該有邊遠城邑的意思。這種沒有文字的“傳説時代”,叫作“史前時期”;人們的記事或交流,只能結繩、畫圖畫或使用手勢、口語。若是想將見聞、經驗傳給後人,就要利用歌謠、諺語和故事,一傳十、十傳百地傳説,一代一代傳下去。
《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又稱邵公、召康公)的封地,據考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帶。但召公並沒有當即移足燕地,而是參加了平息管蔡武庚之亂的戰事。召公的原封地“召”,在今陜西岐山西南,當時的周人都城為鎬京。召公未到封地,並不等於他不派部眾前往燕地;眾多的管家、吏役、兵將等,所操語言的語音應該屬於“周語”(鎬京語音)。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發掘的棺木中,出土了西周早期甲骨文殘片,可認證當年薊燕都城的紀事,承襲了刻在龜甲或牛骨上的殷周甲骨文。
燕國有紀年可考的時間,始於燕惠侯元年(西元前865年)。後來燕襄公將都城從易遷到薊地都邑薊城。據考,薊丘城在今北京廣安門外白雲觀一帶。北京之西,被統稱為西山,屬於太行山余脈;其北軍都山東延至山海關,為燕山山脈。
當年燕都薊城人的口語,應該是融會了周語和薊地土語(多民族混居地産生)的混合語;而文字,大概是鐘鼎文(金文)或竹簡文、木簡文。在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中,收有二百多個“籀文”。據説這籀文,是周宣王時期名叫“史籀”的太史所撰。
周平王東遷,將王城設在成周城(今洛陽市東郊白馬寺之東),史稱“東周”。周平王及其部眾講説的鎬京語,漸漸與成周語融會,形成了“雅言”。雅言,成為春秋戰國時期周新王城與各方國溝通的通用語言。相傳春秋末期的大教育家、魯國人孔子,就是以雅言給來自各國的弟子授課的。
燕國是宗主周王之下的方國,自然需要在官場中推行雅言。但薊燕方言依然是燕地的民間流行語。燕昭王元年(西元前311年),昭王在易水旁修建黃金臺招賢納士,所出的告示使用的應該是鐘鼎文或石鼓文;前來應招的魏國人樂毅、齊國人鄒衍、趙國人劇辛等,自會以雅言相通。
最早的北京地方歷史文獻《燕春秋》,見於《墨子》;記述“荊軻刺秦王”的《燕丹子》,見於明代的《永樂大典》。
秦統一六國,推行“車同軌書同文”,廢“六國古文”,並在官方文書中統一為“小篆”。秦都咸陽的咸陽話,上升為大秦帝國的官話。但由於秦朝的國運僅為十五年,短時間內將咸陽官話替代各郡縣的官話有一定難度。若要覆蓋民間言語,只能是一個泡影。
秦代燕地流行的依然是薊燕方言。西漢楊雄撰有《方言》書,集古今各地同義的詞語,並註明通行範圍。其中,將冀州(河北)、并州(山西)及青州、兗州、徐州(三州為山東)一帶的一種方言稱為“幽燕話”。
“幽州語”和“幽燕語”
大唐的幽州,是漢人與突厥人、靺鞨人、奚人、契丹人、室韋人等雜居的地方。語言學者以幽州為坐標,將唐代幽燕地區語言稱為“幽州語”。
幽州語與大唐中原語言文字有密切的聯繫和傳承關係。“初唐四傑”之一的詩人盧照鄰,號“幽憂子”,幽州范陽人,他的詩集《幽憂子集》今存詩90余首。留下“推敲”典故的唐代大詩人賈島,范陽人,有《長江集》10卷,留詩370首。陳子昂雖然不是幽州人,但他隨軍于幽州時留下的《登幽州臺歌》卻是千古流傳。有“詩仙”之稱的李白,在《北風行》中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之句。
經歷了“漁陽鼙鼓動地來”和沙駝人石敬瑭的燕雲十六州之獻,契丹族的大遼升幽州為陪都“南京”。契丹是鮮卑人的一支,其語屬於阿爾泰語系;得燕雲十六州後,其領地內增添了大批漢人。其間,南京又曾改為燕京,幽都府改為析津府,幽都縣改為宛平縣。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權聯宋而滅遼。金完顏亮(海陵王)下詔遷都燕京,後改燕京為“中都”。中都城倣宋汴梁城規制,在遼南京城基礎上改擴建。原析津府改為大興府,轄大興、宛平等縣。當時中都城居住多個民族,計有女真、漢、渤海、契丹、奚等。
從遼至金,大量北方少數民族不斷涌入北京地區,同時亦有大量漢人被動或主動遷入原來的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金代,漢人被驅掠、遷徙到女真地區的為數很多。在這種不同民族混居、融會的歷史背景之下,幽州語受阿爾泰語影響(女真語亦屬阿爾泰語系),特別是在契丹語和女真語的影響下,“幽州語”演變成“幽燕語”。
金代科舉,設“詞賦科”,即取士為官,要有詞賦的筆試,由此,中都的皇室、貴族、官員,包括漢族士子,多能詩善賦。我們所熟知的“燕京八景”——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據説就是金章宗欽定的。這表明瞭金人漢化的程度。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並沒有改變古漢語及其傳承的語言,而是導致入聲和濁聲的大量消失。
元大都話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蒙古軍在攻打金中都時,這座古老的具有代表性的幽燕古城邑,也就是老北京的前身,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歷經薊、燕都邑,秦廣陽郡、東漢幽州、隋涿郡、唐范陽(幽州)、遼南京、金中都的歷史名城,被兵火毀於一旦。
1260年,奪得汗位的忽必烈從蒙古高原的都城和林到燕京,以金中都東北郊水泊中的瓊華島上所建的離宮——大寧宮為駐所。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廢棄金中都城,並以瓊華島大寧宮為中心,另築新城。漢人劉秉忠按照《周易·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理念建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將“大蒙古”國號改為“大元”;次年,忽必烈將正在新築的城定名“大都”。
老北京人自己受冤枉的時候,常有一句話叫作“我比竇娥還冤”,這句話,來源於元代的戲曲大家、大都人關漢卿筆下的雜劇《竇娥冤》。關漢卿大約生於金末,去世的年代約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年)之後。當時的元帝國將治下的百姓分成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其中,色目人包括唐兀人、畏兀兒人、康裏人、欽察人、斡羅思人、阿速人等;漢人包括北方的漢族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南人,則指南宋遺民。關漢卿雖然屬於第三等級,但從職業來説,就屬於最低等級了。那時元帝國將職業分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關漢卿就屬於幾乎是最底層的“老九”,僅在乞丐之上。
元代,自唐代實行的科舉制長期被取消,儒生也就失去了入仕立業的機會。為了生活,當時的儒生也只能混跡江湖。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等大都的儒生,就是其中的幾位。他們為教司坊所屬的戲班子乃至民間青樓歌妓寫雜劇,寫曲子,倒也成就了一代“元曲大家”。當年的積水潭(當今的後海、什剎海)岸邊的歌樓酒肆、瓦舍勾欄,就是關漢卿等雜劇作家經常出入的場所,也是他與著名女藝人珠簾秀説戲、演唱曲歌的傷情地。
現如今,我們聽不到大都話的語音,但卻可以見到寫于元大都的文字。關漢卿雜劇《感天動地竇娥冤·楔子》:“……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親三口兒家屬。不幸夫主亡逝已過,止有一個孩兒,年長八歲,俺娘兒兩個,過其日月……”從這些文字來看,幾乎絲毫不影響我們的閱讀和理解。最早見諸文字的“衚同”出現在元雜劇中。關漢卿劇本《單刀會》中,有“殺出一條血衚同”之句;張好古雜劇劇本《沙門島張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市角頭磚塔兒衚同總鋪門前來尋我”之句。
元代的大都話,並不是蒙古語,而是在遼、金兩代居住在北京地區的漢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經過幾百年密切交往逐漸形成的“幽燕語”基礎上,受蒙古語、突厥語影響而形成的。
在元代周德清所著的《中原聲韻》中,將元代北曲用韻分十九部,並首創“平分陰陽,入派三聲”之説。該書每部的字均按陰平、陽平、上、去四聲排列,以入聲分別派入陽平、上、去三聲,記述並反映了元代北方話的語音實況。成書稍後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為元代燕山(北京)卓從之著。該書也是曲韻北派的代表作,亦分十九部;但它只將平聲字分三類——大抵以陰、陽兩調相配的字另立“陰陽”類,無相配的字歸“陰”類或“陽”類,實際上平聲只有陰、陽兩調。
“內城話”和“外城話”
現代意義的北京話是在明、清逐漸形成並基本定型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由徐達和常遇春統領的明軍攻佔元大都,大都改為“北平府”。“北京”之名,起源於明永樂元年(1403年)。燕王朱棣登上皇位以後,將北平府改為“北京”,稱“行在”。這裡的北京,是在元大都(北土城至長安街一線)的基礎上營建的,移變成德勝門、安定門一線至前三門一線。
將首都從金陵遷到北京,始於永樂元年;那麼,“北京話”之名,也當始於此。
伴隨著遷都,大批江淮籍的官員、兵將進駐北京,使原來的大都話又增添了江淮話的成分。此後,來自山西等地的移民被安置在北京地區。
北京的外羅城,建成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為防蒙古俺答部侵擾,原本想建造環北京大城一圈的外羅城,因經費不足而只建了北京前三門以南的外羅城。由此,北京有了內城和外城之分。
明代北京,大批外來移民和各地考生入仕為官,帶來了外鄉省方言的語音。北京宛平知縣沈榜在其著作《宛署雜記》卷17《方言》條目中記:“第民雜五方,里巷中言語亦有不可曉者。”這一記述,反映了明萬曆年間北京城內居民五方雜處和各路方言混雜的狀況。《宛署雜記》中收錄的當時的北京方言詞語,計為80余條,其中有些是來自不同民族的語言和外地的方言,如“妗子”(舅母)等。在當時的北京方言中,“父親”的稱謂有三種,即:“爹”、“別”(平聲)、“大”。語言學者認為,“爹”為原住居民語,“大”則來自山西,“別”來自江淮語。現今北京話中常用的“爸”,在當時並未出現。
不同地區的漢語方言,如江淮話(包括南京話、安徽話等)、山西話及冀東話等,在明代融入了“北京話”語系。
北京的“內城話”和“外城話”有別的現象,形成于清初。
清太宗皇太極繼承汗位後,改女真族為“滿洲”(簡稱“滿族”),在瀋陽(盛京)正式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此後,皇太極在“滿洲八旗”之外,分別增設了“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漢八旗,主要成員為遼東人,其官兵所講的語言,大多為源於幽燕語的遼東語(又稱瀋陽語)。遼東語源於冀東語,冀東語源於幽燕語。而遼東語又有別於冀東話,因為它是受女真語影響的變體。
清入主中原,以北京為都。順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下諭:“除八旗投充漢人外,凡漢官及商民等人,盡徙南城居住。”於是,北京內城(“前三門”以北)的皇城以外,變成親王、郡王、貝勒與八旗官兵及眷屬的專用地。被遷出內城的非旗人官民及原居民,居住在“前三門”以南的外城。由是,清初的北京話也就分成了兩個區域性語言板塊——“內城話”和“外城話”。
北京內城居住和駐防的是旗人。愛新覺羅·瀛生(筆名常瀛生)在《北京土話中的滿語》中説:“清初滿人入關,在北京形成了‘滿語式漢語’。”康熙時代,滿洲八旗在漢化過程中接觸最多的是漢八旗官兵及“包衣”(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個奴僕群體)等。他們説的,是漢八旗的瀋陽話,而講出來的則是滿語和瀋陽話相摻雜的語言,也就是“滿語式漢語”。
到了雍正和乾隆時代,滿洲旗人已經使用雙語——既會滿語又會漢語。與此同時,滿語詞大量進入漢語。如:“挺”“薩其瑪”“逞能”“攛掇”“敢情”“嚼谷兒”等。
在滿清入主中原十餘年後出生,並在其後40餘年內成為作詞209首,有“清代第一詞人”之稱的納蘭性德(1655年—1685年),是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師明珠之子,為康熙朝進士、一等侍衛。他在掌握漢文化和語言方面,應該算得一個傳奇。納蘭性德以小令見長,多感傷情調。如《採桑子》:“桃花羞作無情死,感激東風。吹落嬌紅。飛入閒窗伴懊儂。 誰憐辛苦東陽瘦,也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處濃。”梁啟超評納蘭詞:“容若小詞,直追後主。”王國維説納蘭“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人物口語,有許多清雍正、乾隆時期北京話的特徵。如第七回《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宴寧府寶玉會秦鐘》:話説黛玉“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頑呢。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著我送花兒與姑娘戴。’”其中的“頑”,等同於現今的“玩”;“姨太太著我”,即現今的“姨太太叫(讓)我”。個別語詞有別,但意思可懂。再如《紅樓夢》中用的“才剛”,已在如今被顛倒成“剛才”了。
基本擺脫“滿洲式的漢語”,形成北京“旗人語”的時間,大約在道光、咸豐時期。代表當時北京方言語的文學作品,是滿洲鑲紅旗人文康(別署燕北閒人)成書于道光中葉的《兒女英雄傳》。如該書第八回“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覓究”中:“安公子此時的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樣。假如姑娘説日頭從西出來,他都信得及,豈有個不謹遵臺命的?忙答應了一聲,一抖積伶兒,把作揖也忘了……”其中幾乎全都是當今的白話,只是將“尋根究底”寫作了“尋根覓究”;將“抖機靈”寫作了“抖積伶兒”,但近似或音同,只是多了一個“兒化”。
我們常説的“京韻京腔”,可在京劇的唱腔和唸白中體驗。徽班在乾隆年間進京以後,並沒有形成純粹的“京腔”;直到道光年間楚腔(又稱漢調)進京與徽班合作,形成了“皮黃戲”。由此,皮黃戲被稱為“京腔”。隨著同治、光緒年間京劇在北京形成繁榮局面,劇中的“京白”使北京官話呈現出獨特的京腔京韻,並使其成為後來的普通話的標準音。
清代,原本生活或搬遷到北京外城的住民,大多為明代遺民,説的是明代北京方言。相對從關外而來的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明代遺民就成了“北京土著”,而“土著”講的話,就是“北京土語”;若溯其源,北京土語為“幽燕語”的傳承,幽燕語為“幽州語”的傳承。
關於北京土語,可見戲劇家、北京文史風俗專家齊如山先生的專著《北京土話》。土語的語音,我們可以從著名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的相聲段子裏領略一二:“哎,那(音“內”)天我你去啦,趕上你沒在家。我溜溜兒等你半天,你壓根兒也沒回來。我一看褶子啦,我就撒丫子啦。”
輕聲和兒化
輕聲和兒化,是老北京話的顯著特徵。輕聲,也叫“輕音”,即某些詞裏的音節或句子裏的詞,念成又輕又短的調子。北京話裏,輕聲字(弱讀音節)在整個音韻系統中佔有重要地位。一些雙音節詞,兩個音節的輕重程度大多不同,相比而言,前一個音節較重,後一個音節較輕。如北京話説的:老實、鼓搗、尾巴、窩囊、豆腐等。
北京話裏輕音的作用有多種,其中有改變詞義和詞性的:如,名詞的“言語”,即説的話,輕聲後的“你言語一聲啊”(你説句話啊),原本的“名詞”變成了“動詞”。輕聲後動詞變成名詞的,如,“不要把精力花費在沒用的地方”,其中的“花費”為動詞;若變成“天天買零食也是不小的花費”,這“花費”就變成了名詞。
所謂“兒化”,就是尾碼“兒”字,但不自成音節,而是只表示一種卷舌作用,使韻母“兒化”。
齊如山先生在《略談國劇無聲不歌——兼談念字法及小字轍》中説:“説某某衚同,則説本音,如泛泛説衚同,則説衚同兒。”如:我們説“家在茶食衚同”,不兒化;若説“我們家就在前門外的小衚同兒裏”,加兒化。對此,齊先生有一系列舉例:三條腿,兒化為“三條腿兒”;喝豆汁,兒化為“喝豆汁兒”;“票友”,兒化為“票友兒”等。
語言學者認為,北京話的兒化,是唐代的幽州語、遼金幽燕語的傳承。明代晚期,兒化音已顯成熟。北京的滿洲旗人在初學漢語,特別是在説漢語“兒”時,會顯出“大舌頭”腔調,因為遇詞尾的“兒”,他們不習慣“兒化”,而是將其單成音節。
昔時,老北京專營煤行的多為河北定興人,澡堂裏的服務人員的多為河北寶坻人。其詞語帶“兒”字的,不是“兒化”,而是單成音節。如煤行的定興話:“一清早兒,搖了五百斤煤球兒。”當年北京衚同的孩子學説定興煤行話,説煤鋪夥計是“搖煤球兒的(音‘地’)”。澡堂的寶坻夥計招呼顧客:“修腳不?還有個蠟頭兒(敷腳的熱石蠟)呢。”這兩地的方言,都屬於遼金時代古老的幽燕語系。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追究一下遼燕京話或金中都話,是不是聽一聽定興話和寶坻話的語音就能有所體驗呢?
老北京話語匯中的兒化,很有講究。比如“門”。北京的城門——正陽門(前門)、宣武門、崇文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西直門、朝陽門、阜成門、廣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右安門,一律不兒化;但有三個城門例外,一個是“東便門兒”、一個是“西便門兒”,還有一個是“廣渠門兒”。這種“兒化”與不“兒化”的區別,當是明清北京口語的習慣成自然。
而宅院的“門”,則一律兒化,如大門兒、二門兒、關門兒、開門兒、前門兒、後門兒。如果用反了,將永定門叫成“永定門兒”,或將“後門兒”説成“後門”,就不成“北京話”,甚至鬧笑話。
再有就是“閃音”(也有叫作“吞音”的),即舌尖向齒齦輕閃而成。如説前門外的“大柵欄”,老北京的口語音為“大什蠟”;或者在快速的口語中,“吞”掉中間的“柵”(什)而為“大兒臘”,或“大臘”。
往事越千年,彈指一揮間。當今廣安門立交橋附近的濱河公園,在金代宮殿遺址豎立著“北京建都紀念闕”。以金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改燕京為“中都”,定為國都計,至建紀念闕的2003年,為850年。若以西周時代的薊燕古城計,北京城建的日子就在3000年以上了。
從薊燕語,到幽州語、幽燕語、大都話,到明、清北京話,及當代普通話的推廣和普及,多少腔調音韻的溪流匯成了北京語言的長河。
普通話化,是當代新老北京人語言的總趨勢。伴隨著“普通話”的普及,近幾十年來,北京內城、外城,遠近區縣及多個部委、大學、軍隊大院,除少數地域,大多已經普通話化。與此同時,由於求學、工作等因素,原本就屬於移民城市的北京,又增添了多少新的“鄉音”。外來語詞,電腦語言、網路語言,在不知不覺中融入了北京流行語。
(作者:劉孝存,係作家、文化學者,曾任北京市地方誌學會秘書長)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