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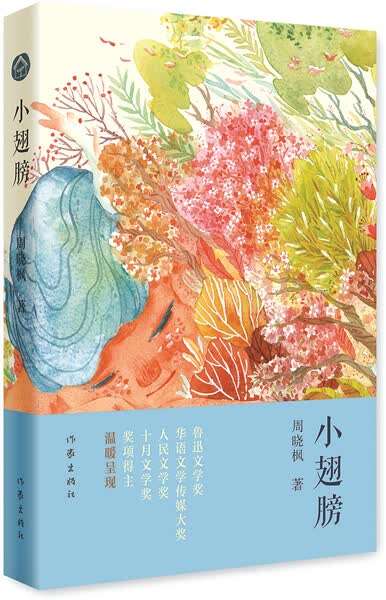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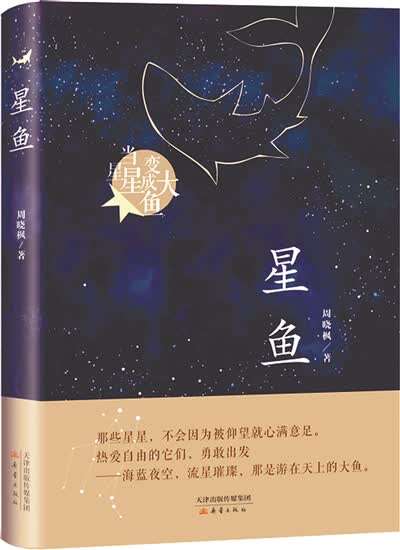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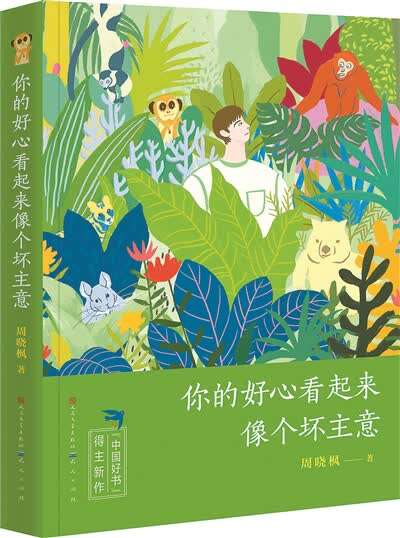
周曉楓
北京老舍文學院專業作家,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
出版有散文集《巨鯨歌唱》《有如候鳥》《幻獸之吻》等,曾獲魯迅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獎項。
出版有童話《小翅膀》《星魚》《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中國好書、桂冠童書等獎項。
這個八月,作家周曉楓的童話處女作《小翅膀》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在此之前,周曉楓已是取得散文獎項“大滿貫”的寫作者。李敬澤説她的文字“是最好的書面語,自帶魔性”,畢飛宇説“她是迷人的”,批評家張莉稱讚她“每個句子都閃閃發光”。
8月19日,周曉楓獲獎後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獨家訪談,聊了聊她寫作的那些事。咖啡廳的窗外,小雨淅淅瀝瀝,秋風帶來涼爽。一身細布長衫,剪著短髮的周曉楓説話間肢體豐富,語速快,溫和中不失犀利。
忽然之間,坐對面説得正帶勁的她,瞬間表情凝滯,兩眼放光,探照燈一樣追著什麼東西,然後從她停滯的表情裏發出呵呵的笑聲。我趕緊轉頭,以為發生了什麼大事件,卻只見一個男生正把一隻豆包大小的奶貓送進一個迷你便攜寵物籠。於是,直到她看著小貓在籠中臥下,我們才算是重新接上了話茬。
我很後悔沒把當時周曉楓看見小貓的樣子拍下來。
錯過動畫片比錯過故事片遺憾多了
北青報:你的兒童文學處女作《小翅膀》獲得大獎,起初怎麼想到寫童話的?
周曉楓:説起來特別簡單。我原來擔任過一次兒童文學獎的評委,有的作品好,有的寫得差。當時我隨口放了句大話:就這水準,我也能寫兒童文學。放完大話以後,就比劃了個開頭,然後幾乎忘了這回事兒。後來《人民文學》的編輯找我,緊急組稿補版面,説“把你的大話圓回來吧”。
答應了以後,我就玩兒命寫,寫得特別快。我記得最快時候一天寫將近5000字,一個多月就完稿了。我以前從來不敢這麼寫——前面的故事寫完,後面要寫什麼不知道,只能今天晚上寫完了,明天早上再説——屬於丟盔卸甲,容不得喘氣兒,直接往前跑出來的急就章。
我本來是個落筆相對慎重的人,但挺奇怪的是,到現在為止我的兩個急就章成績反倒不錯。當年《離歌》從開始寫第一個字到完成,初稿7萬字用了一個月零十天,特別瘋狂,後來我又拿出一些時間修改。結果,2017年《離歌》上了各種排行榜,而且排在榜首位置。《小翅膀》也是,出來獲了中國好書獎、獲了桂冠童書獎,我後來的童話《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在接下來再次獲得桂冠童書獎。桂冠童書獎的兒童文學項目下,兩年共評出13個名額,我一人佔倆,當時可開心了。
北青報:你當過八年兒童文學編輯,這段經歷對自己寫童話有什麼影響?
周曉楓:當兒童文學編輯的時候,我其實特別討厭兒童文學。看的稿子又幼稚又無趣,又沒有情感,而且把自己弄得很低智,一度覺得自己在這個時間裏消耗得特別厲害。
不過我現在極其感激那段經歷,因為我那時20多歲還一直在讀童話,等於是推遲發育了,推遲發育的好處是在於看世界的眼光不太一樣,會有一種孩子似的發現力。我為此深懷感激。
到現在為止,我是特別喜歡去電影院看動畫片的人,比如《瘋狂動物城》《裏約大冒險》之類,我都特別喜歡看,錯過動畫片比錯過故事片遺憾多了。
北青報:你寫《小翅膀》是平實的短句風格,和你寫散文時的巴洛克句式風格形成很大反差,而且你寫的童話也風格迥異,是怎麼做到的?
周曉楓:可能我自己寫作時就有點人格分裂。我花在構思上的時間特別長,而且我一直有種理念:動筆最好的狀態是把自己消化掉,跟著作品的內容走,需要我是什麼,我就是什麼。
寫童話我覺得語感很重要。在《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裏頭,寫到烏鴉家族裏,爺爺爸爸孫子一家全是騙子。寫這個故事的八個月時間裏,我覺得要死在這上面了,因為我自己的語言裏以前沒有這種風格,我根本不知道大騙子怎麼説話。比如大騙子怎麼教小騙子行騙,然後小騙子怎麼都不上道,他們又怎麼在兩邊説假話行騙……難以找到語感。寫的時候,我真的就變成個騙子,坐那兒跟演戲似的。開始特別難,我張不開嘴,後來只能一點點琢磨,在家裏自己表演。那時候,一卡殼就回想動物園。
北青報:你去動物園當過志願者,那是一段怎樣的經歷?
周曉楓:我真的就是去當志願者,每天早上穿工服去上班。寫動物的事靠想像真想不出來,我就喜歡在動物園待著,那裏有無數美妙的細節和瞬間。
我在《幻獸之吻》裏寫過一個小長臂猿,它跟飼養員的關係親得不得了,然後見著我給它帶來實惠,飼養員又不在旁邊,就跟我特別好,飼養員來了它又假裝不認識我,一心一意只信任飼養員的樣子,演技就跟影帝似的。現場就是那樣,動物世界的層次太豐富、太精彩了。
我從獸醫那兒才知道,許多動物都恨獸醫,因為治療過程讓它們疼痛和恐懼。我還見過鸚鵡正在孵化的蛋,最初生長出來的是心臟,然後那些細密的血管像樹枝一樣,包裹整個蛋膜,特別漂亮。還有比如兩隻放在外面架子上跟遊客互動的鸚鵡,特別逗,到了5點,“咔”它倆自己就跳下來了,知道下班了,“咔”的那個點,就跟鐘錶那麼準。我覺得動物園裏,處處有妙趣。
我寫的故事裏,自己挺偏愛《星魚》的。寫《星魚》之前我在海洋世界住了一個禮拜。每天早上一開門就去水族館。開始沒感覺,我就天天去。到第六天晚上,我夜宿水族館,找到了靈感。沒有靈感時,就在那慢慢觀察、慢慢等待,總會有美好的意外,而且我真的樂此不疲。
跑馬拉松的時候聽見鼓掌,沒人會站那兒聽一會兒掌聲再跑
北青報:你的散文、童話,到現在都拿了最高獎,你對獲獎這事怎麼看?
周曉楓:我自己高興的是,我沒有為獲獎做過一件經營性的、輔助性的、祈求式的事。這讓我心裏敞亮。我每一個獎不管是大是小,我沒做過額外的工作,我只在作品本身下力氣,所以我覺得是感恩的。
我覺得在情感和創造力上,人不能被獎項所收買。得獎當然是個證明,能給我帶來持續的動力,就像“又加了一箱油”。但這不是自鳴得意的時候,我可不願喪失了謙卑和審慎而不自察。我老這麼想:得了獎我也不能止步,否則就是技止此耳;我希望,接著寫得更好,至少讓人覺得獎項給得應該。
沒有人在跑馬拉松的時候聽見鼓掌,會站那兒聽一會兒掌聲再跑。得不得獎不會影響我的“配速”。得獎時我用余光看看耳朵聽聽,但它不會干擾我的行進節奏。
我覺得寫好手頭兒這個是最重要的,這麼説吧,我的注意力都在即將誕生的這個“孩子”身上,其他的“孩子”,生完了,讓他們自立去吧,上學的上學打工的打工,而我懷裏的這個是我最需要養育的。
北青報:你之前在散文篇目裏寫過不少對經典童話的思考,到你自己寫童話時會堅持什麼原則?
周曉楓:我希望我寫的童話不流失智力和情感的成分。我寫特別溫暖和特別殘酷是一樣的,我寫特別複雜和特別簡單也是一樣的,我心裏的原則並不亂。從小寫作文,到現在寫作,就一個原則,在保護自己和保護他人的情況下,怎麼把真話説好。不論是散文還是童話,都以我最大的真摯去寫。
北青報:在創作中代入自己會覺得受“內傷”嗎?
周曉楓:我覺得所有寫作都是要打磨自己的內心,觸及內心世界,肯定疼。可一旦這根火柴點亮,我覺得即便“內傷”也沒關係。這個過程可以説是“內傷”,也可以説是在幫助你成長,變得更強大,變得更豐滿。
當然寫作的過程中,有時情緒會很痛苦,真的像一個小丑演員一樣,最後會流淚,會疲憊,會沉默。但這是我的孩子,我理應承擔孕吐、承擔生産的疼痛。如果沒有這種代入,我自己寫得也不嗨。我每次寫都到有點吃力、有點沉重、有點自我懷疑、有點自我焦慮的程度,但把它承受下來,可能就變成了我寫作上的“肌肉”。
別人知不知道不重要,我要保證自己沉浸在裏面
北青報:你沒有微網志、不開公號,甚至關閉朋友圈,沒想過擁抱網路,去親近更多讀者?
周曉楓:我這種人沒辦法開這個口子,其實是膽怯。比如萬一我開了抖音或公號,我就得整天住在上面了,我會每秒鐘都得看看有沒有量變。別人觸網能控制尺度,我控制不了,不是因為我多有定力,其實是因為特別沒有定力。
而且我不會處理朋友圈這些事。假設我開了朋友圈,那將是一個無限的麻煩,我為不為朋友轉發或點讚?有的點讚有的沒點讚,有的轉發有的沒轉發,怎麼處理怎麼解釋……我平衡不了這些,沒辦法,只能把門關上。
北青報:原來是性格所決定的。
周曉楓:對,我是比較心重的人,而且後勁很大,這點我非常清楚。
我從來不敢養寵物,偶然養的土撥鼠左左、右右,它們不在以後,我在抖音上關注的全是土撥鼠的視頻,每天花大量時間看。土撥鼠長得差不多,其實內容也都差不多,但我還是看來看去。假設博主更新特別慢,我就生氣,因為我得把舊視頻再看一遍。到現在左左、右右已經走了一年多了,可我還是斷不了這個習慣。每天困得我,頂著個烏眼青還在看,有的視頻我看了無數遍。氣死了。這算我的一種長情吧。
原來我當過電影策劃,也真當不了。雖然我在電影裏所能發揮和控制的因素很小,但電影拍出來以後,我就會幾天幾夜難以入睡,在網上一遍又一遍看評論,控制不了自己。
北青報:指的是當張藝謀文學策劃的那段經歷吧?對你有什麼影響?
周曉楓:我現在很認同張藝謀當時説的話——他第一次演《老井》時為了保持狀態,就天天練習背石頭,不拍戲時也背,他説要保持肌肉的狀態。為了演困在井裏三天沒吃飯的樣子,他就真的三天沒吃飯。他説三天沒吃飯,跟三天吃飯的效果,其實鏡頭裏覺察不出來,但是三天沒吃飯之後,演起來心裏更踏實。
這個對我有很大影響,也受到啟發,那就是別人知不知道不重要,假設自己齣戲,中間一大撒把,再收起來的狀態它不是續接的。所以每當我寫不下去的時候,我就想各種辦法,能不能先寫幾句對話,能不能先看看相關的書,我要保證自己沉浸在那種情緒裏面。
北青報:那在寫作過程中遇到了“坎”怎麼邁過去?
周曉楓:寫作就是跨欄賽,過程中有障礙是正常的,是必然的。我現在明白了,寫作時間越長,越容易見底、遇坎,這説明能力不足以支撐有速度的寫作了。比如我《小翅膀》,有元氣在,也莽撞,可能就有它渾然天成的東西。《星魚》有很多海洋知識,得做許多基礎準備,速度自然慢下來。《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涉及的小動物更多,我得先查閱很多知識,設計情感和情節的脈絡,差不多心裏有數了,才敢下筆。如果過程中找不到童話的語感,不知道對話怎麼銜接,就先拿散文把這事串下來,然後慢慢翻譯成童話的樣子。
別無他法,只有寫作能解決寫作本身存在的問題。障礙和瓶頸,只能邊寫邊克服。我覺得寫作是與未來的自己博奔,一點點接近絕對可能的那種絕對不可能——只有你輸給了明天,才是妙處;這種“輸”既可以讓你精進技藝,又讓你戒驕戒躁。一旦你贏了,那才不幸,意味著你輸掉了自己未來的可能性。
就算不能所向披靡,也希望自己能勇猛無畏
北青報:看你的文章,會覺得你是個很清冷、很犀利,甚至有點狠的人。但是一見面卻覺得嘻嘻哈哈,反差特別大。
周曉楓:我特別矛盾,是個挺合群的人,同時也是個非常害羞的人。我倒是很喜歡自己的矛盾,好處就是寫作的時候會把各種可能性融進去。我會模擬情境,模擬心態,模擬表達,自己在心裏表演,一點點攢那些瞬間的感覺,直到找到流暢的表達。
北青報:有點理解了你説放棄二十年的編輯生涯當職業作家,一點不糾結。
周曉楓:我是一個非常怕負責任,因而顯得極度負責任的人。我心理責任感特別重,特別怕對不起別人。原來在人民文學雜誌社和十月出版社上班的時候,我看稿時校對水準很差,別人看我像神經病,人家校一兩遍我校三五遍,其實就是怕出錯。
生活中我挺怯懦的,但我寫作挺無畏的,我那點勇敢全在寫作中集中釋放了。隨便讀者覺得我是什麼人,反感我或厭惡我,沒關係。但生活中我沒這種勇氣,特別怕善待我的人受連累,特別怕無辜的人受我牽扯。本心上我一方面不願意害人,一方面也承受不了後果帶來的反芻。我在生活中對人對事最簡化,不太會用心機,我願意把精力全用在寫作上。
北青報:做直播,很多年輕人喜歡周老師,他們覺得你會和盤托出。
周曉楓:講寫作課,我對理解和技術確實沒有什麼隱瞞。幫別人指導的過程,其實也是訓練自己的過程。如果是把精力用到保留、計較甚至説謊上,以後寫自己的文字時也會出問題。有些作家能夠寫到所向披靡,我雖然沒有那樣的功力,但希望自己能勇猛無畏。
而且即便是有資歷的寫作者,也要有誠心跟年輕人學,跟新經驗學,不要以為自己的資格老,好像訓練多了,經驗多了,其實經驗本身也會帶著它的副作用,也許還會拖累你。我在“得到”的啟發俱樂部剛剛講過這個問題,假如我所經歷的,能夠讓其他寫作者避開一些坑、走得更穩一點,我會很愉快。
我認為,作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準確”,它的好處在於,這個世界千變萬化的時候,只要你拿到準確的原則,你就可以千變萬化。
北青報: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未來對自己會有怎樣的規劃?
周曉楓:目前,年齡除了使我眼睛花得厲害,還沒給我心理上帶來什麼巨變,我很少意識到自己年過半百。而且我由衷地越來越熱愛寫作。別的我也不會。文學收容我了,我幾乎心懷那種對恩人的感激。我就這性格,讓我負責的時候我盡心盡意,一旦這事與我無關,我一耳朵都不想聽。我的精力有限,只能放在我無限熱愛的事情上。
供圖/周曉楓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