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讀《奶酪與蛆蟲》:這本遲到的經典為什麼值得等45年?
近年來,微觀史學在國內逐漸“出圈”。出版界也大量譯介了西方具有非虛構色彩的歷史研究著作。微觀史學關注歷史中的日常生活與普通個體,以“顯微鏡”視野研究局部,在豐富綿長的細節中深入歷史內部,這樣“以小見大”的敘述方式收穫了不少大眾讀者的喜愛。
説起微觀史學的代表作品,繞不開的便是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自初版以來,這本書一直被認為是微觀史的經典之作,金茨堡也因此被認為是最早倡導這個研究取向的歷史學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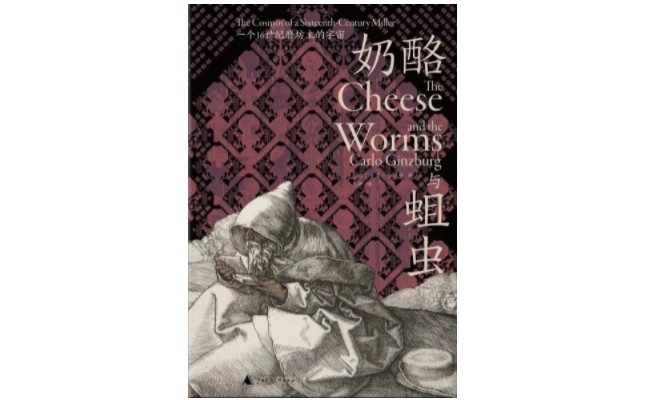
《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意]卡洛·金茨堡著,魯伊譯,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
金茨堡利用宗教裁判所檔案,建構起一個16世紀義大利北部偏僻山村小磨坊主的心靈史。這個小磨坊主把宇宙看成一塊被蛆蟲咬得到處是洞的奶酪,書名也因此而來。
這本書要解答的問題是:這位小磨坊主的奇怪思想來自哪?金茨堡根據他閱讀過的書和審訊的口供進行了分析。他讓我們看到了小人物的內心世界,並由此去解讀當時社會、宗教和文化。這本書致力於研究普通民眾,是書寫大眾文化史和微觀歷史的一個典範。
近期,這本遲到已久的微觀史經典著作終於在國內面世。我們特別邀請到澳門大學歷史系傑出教授王笛撰文。王笛是國內微觀史學代表學者。他此前出版的《茶館》《袍哥》等作品聚焦歷史中的日常生活與普通個體。在這篇文章中,王笛從微觀史學的概念本身出發,細緻解剖了微觀歷史的思想根源與對歷史中普通人的重新發現。
撰文 | 王笛
(澳門大學歷史系傑出教授)
什麼是微觀史?
《奶酪與蛆蟲》是我讀的第一本微觀史的著作,那是1996年,我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著手寫《街頭文化》(Street Culture )那篇博士論文的時候,我的指導老師羅威廉(Willian T. Rowe)教授便推薦我看由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25年來,這本書不知道翻了多少遍,在美國和中國澳門,我一直開設新文化史的討論課,也多次使用這本書。2010-2014年連續5年的夏天,我在華東師大思勉研究院給研究生開設大眾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的課程,但是遺憾的是,由於沒有中文翻譯本而無法使用該書。
這些年來,我一直自己踐行微觀歷史,力圖改變歷史研究者、學生和讀者對普通人歷史的漠視,而微觀史可以説是歷史研究範式轉移的一個重要契機。但是,對於中國的廣大讀者來説,什麼是微觀史則並不是很清楚的,畢竟這是一個新的歷史書寫形式,特別是我們習慣了歷史寫作要有重大意義和宏大敘事,對這種研究小人物的歷史,還有諸多的不習慣和不理解。
需要説明的是,並不是説歷史寫得瑣碎、有許多故事和細節,就是我們所稱的微觀史。例如,如果我們寫一本曾國藩或者胡適的書,哪怕細節再多,無論多麼細緻,也不是我們所稱的微觀歷史。微觀歷史的前提之一,就是要寫普通人的歷史。金茨堡認為,微觀歷史分析的基本單位應該是人,可以通過各種檔案,包括稅收記錄、出生登記、法院案件等,進行故事的追蹤。
根據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什麼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中的討論,“微觀史學是對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碰撞做出的反應”。按照他的説法 ,是“顯微鏡成為取代望遠鏡的一種有吸引力的選擇”。另外,微觀史學也是對“宏大敘事”的失望而做出的反應。所謂的“宏大敘事”描述了人類的進步,歷史研究中充斥著古希臘羅馬到基督教的興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等等。這些固然是歷史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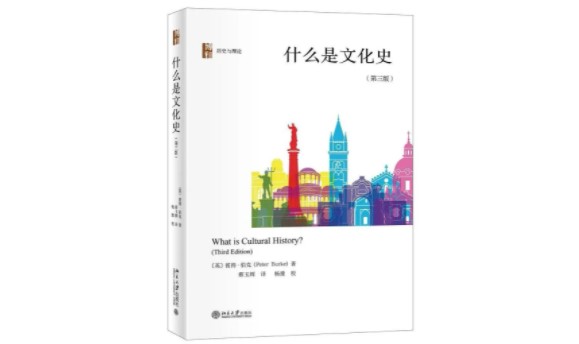
《什麼是文化史》,[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
在金茨堡看來,微觀歷史重視“那些被迫害的和被征服的人”,而這些人 “被許多歷史學家視為邊緣人物而不予理睬, 甚至通常全然無視”。他不去研究上層,反而去研究一個默默無聞的磨坊主。在過去,哪怕資料再有趣,再獨特,如果要使用的話,最多不過“是一條註腳的素材”而已,然而現在“卻成了一本書的主題”。就這樣,金茨堡便將這本書與過去的主流歷史學清晰地區別開來了。
微觀歷史的思想根源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感興趣的是,金茨堡“開始學會如何去當一個歷史學家”的過程。在1950年代末,他開始嘗試從宗教法庭的審判記錄中,追尋普通人的歷史。這個努力,顯然是受義大利共産黨的領導人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獄中札記》(The Prison Notebooks)的影響。葛蘭西在墨索裏尼的監獄裏,寫下了這部影響深遠的對底層階級(subaltern classes)文化的反思。雖然金茨堡受到葛蘭西的影響,很早就有研究下層的打算,但是按照他自己在《奶酪與蛆蟲》2013年版前言中的説法,1970年代的“激進政治氣候”,也給予了他這個研究思想上的準備。他對這個“激進政治氣候”沒有做進一步的説明,但應該是指當時全球左翼思潮的廣泛散佈。

卡洛·金茨堡
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也是在義大利(乃至歐洲)史學轉型這樣一個大背景中出現的。1966年創辦的《歷史筆記》(Quaderni Storici)在微觀史的興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圍繞這個雜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學術共同體。他們批評主流歷史把過多的精力給予了統治者和精英階層,忽視了廣大的民眾,特別是下層民眾。那些有限的不多的有關民眾的研究,常常是被扭曲的歷史。
金茨堡在前言中回顧了這本書的起源。1960年代初,他在義大利的烏迪內(Udine)翻閱一個18世紀宗教法庭審判官的彙編, 其中有義大利宗教法庭1000次審判的手抄本目錄。他無意間讀到一條不過寥寥數行的案情介紹,便産生了極大的興趣:被告是一個小磨坊主, 因為對上帝有不同的看法而受到指控。金茨堡想以後有機會再回來讀這些檔案,於是把卷宗編號抄在了一張小紙片上。哪知一晃就是七年,直到1970年, 他才有機會讀到審判的縮微膠片,便立刻被這些記錄所觸動。又是差不多七年,他出版了《奶酪與蛆蟲》 。也就是説,從他知道這個檔案,到書的最後出版,經歷了漫長的14年。
發現庶民的聲音
微觀歷史的研究所面臨最大的困難,就是怎樣去發現下層民眾的聲音。正如金茨堡所指出的:在文獻資料中,下層民眾從來就沒有自己的聲音,他們的思想和意識全是由記錄人來書寫的。下層人的聲音哪怕能聽到,但是“已經經過了重重過濾”。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資料,這些記錄下來的文字,實際上是已經被扭曲的東西,並不是真正的他們的聲音,所謂的“大眾文化”也是強加在下層民眾身上的文化。因此,這本書的寫作,就是尋找他們聲音的一個過程。
以對這個小磨坊主的審訊記錄為例,其中便包括了審訊者的提問,書記員的記錄,最後的整理和抄寫等。金茨堡進一步表示,雖然梅諾基奧給兒子寫的信可以視為他直接的思想表達(下面將提到這封信),但是監獄和審訊給了他心理和肉體上的雙重壓力,因此,“作為歷史文獻而言, 究竟有多大價值”,則是值得懷疑的。然而,當我們讀完這本書,發現經過金茨堡的解讀,這種價值已經完全地展現無遺。
本書的主人翁是小磨坊主梅諾基奧,他因傳播“異端邪説”而被宗教法庭起訴,在長達十多年的審訊之後被處死。宗教法庭對他的審訊記錄被完整地保存下來,金茨堡從這些完整的記錄中,竭力挖掘他的內心世界。
令人驚奇不已的是,梅諾基奧這個農民,在回答審判官問題的時候,竟然經常是長篇大論,詳細地闡述了他對宇宙的看法。這本書的書名便是取自梅諾基奧的信仰:在混沌之初,天地萬物出現,猶如奶酪中生出蟲子一樣。這個研究還揭示了隨著印刷業的發展,書籍不再由上層階級壟斷,梅諾基奧也可以得以閱讀一些“禁書”,他顯然在意識形態上已經超越了其他同時代的農民。

16世紀宗教法庭。圖為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因被指控“異端邪説”而接受審判。
金茨堡分析這個小磨坊主怎樣理解那些文本,從而能夠通過研究這樣一個在歷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建構一個小磨坊主的心靈史,並由此去解讀當時社會、宗教和文化,展示當時義大利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關係和衝突。他研究的焦點,實際上是與精英文化相對的大眾文化和庶民文化(subaltern culture)的歷史。
從這本書的結構看,倒不像是寫學術書,而是小説的謀篇佈局。本來書的篇幅就不大,卻分成了62章,有的章只有1-2頁,是非常另類的學術專著。但是正是因為這種結構,哪怕幾乎全部資料都是根據檔案,卻有了讀小説的感覺,把我們帶入了“黑暗的中世紀”的義大利鄉村世界。
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農民不屈服於教會,對所謂上帝創造人的批駁,而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釋。他明明已經在危險之中,仍然管不住自己的嘴,喜歡辯論,喋喋不休地闡發自己的見解,稱《聖經》是騙人的,耶穌也不是為了拯救人類而死,從而讓自己陷入了危險之中。
其實他的觀點都是公開的,口無遮攔,到處講他的世界觀,大家也是聽之任之。雖然被認為是一個怪人,但是多年來安然無恙。不幸的是,他被一個神父所告發。但是第一次長時期的審判後,他居然能夠逃過了一劫。本來應該已經成功著陸,卻被人第二次告發,最後喪失了生命。讀罷這本書,更讓人感到他的死,似乎被一隻隱藏的上帝之手所操縱著。
審判的細節
羅馬宗教法庭(Roman Holy Office) 對審訊有著嚴格的要求, 其記錄詳細到在法庭上發生的一切, 都被完整記錄下來,包括審訊的提問,被告的所有答覆,一切陳述, 刑訊過程中的一言一行, 甚至包括他的嘆息、哭泣、痛悔、淚水,等等。書記員的職責, 便是如實地、一字不差地將所發生的一切記錄下來。問和答都是以第三人稱語氣轉述的。
在每個案例宣判前,羅馬的最高法庭會對審判記錄進行仔細地審核, 之所以要求這麼詳細的記錄,便是試圖防止審訊中的不正當行為, 比如一些審判官提出誘導性或暗示性的問題。而且宗教裁判所並不急於得出結論,一個案例便反反覆復地審訊,哪怕持續經年。
從本書的描寫看來,梅諾基奧沉醉於自己的表達,他似乎還很享受在法庭上有這麼多有文化的人聽他的滔滔不絕的辯論,是和過去只能對著一群幾乎不通文墨的農民和手工藝人的聽眾,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他不相信世界是由上帝創造,他説耶穌基督不過是一個 人。他憧憬一種當時流行小説中描寫的“新世界”,一種烏托邦,所謂“安樂鄉”的世界:奶酪堆成山,從山洞裏涌出牛奶的大河,沒有家庭,還有性自由,男女都赤身露體,既無酷暑也無嚴寒......
從梅諾基奧自己的招供看,他內心對教會充滿著仇恨,在他被審訊之後,有時候他“幾乎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宣稱“想要跑出去,搞點兒破壞”,還想要“殺掉那些教士,放火焚燒那些教堂,做點兒瘋狂的事”。他感到的孤立無援,面對自己遭遇的種 種不公,他唯一的反應,就是向那些迫害他的人報仇雪恨。不過最後他沒有付諸實施,無非是顧及兩個年幼的孩子。
在監獄裏受了將近兩年的折磨,梅諾基奧終於屈服了。1586年,梅諾基奧寫信表示了懺悔,請求原諒:首先苦兮兮地説自己是“身為囚徒”的可憐,“懇求”宗教法庭考慮“是否值得原諒”,承認自己有“過錯”,願意做出 “更多補贖”。他説自己“極度窘境”,“乞請”赦免。
他陳述了自己自從被從家中帶走,“投入這殘 酷的監獄受罰”,已經兩年多的時間,被剝奪了與妻子的見面,而他的孩子 們,因為“日子貧苦也被迫棄我于不顧,令我唯有一死”。似乎他經過兩年的審判,已經徹底服軟,願意放棄自己過去那些“奇談怪論”,承認“自己犯下 的大罪懊悔悲痛,乞求原諒,首先是來自我主上帝的原諒,其次是來自神聖的宗教法庭的原諒”。他請求法庭“恩賜”,將他釋放,並保證“依照神聖羅馬教會的教誨生活”。
在外人看來,梅諾基奧的身體也真的是日漸虛弱,他身患疾病,有一次人們甚至認為“他會死掉”,他在監獄裏“居然熬了這麼久”,也是出乎人們的意外。他經常對監獄看守談起,他懊悔“以前相信的那些蠢事”,還表示其實他“從未堅持過那些東西”,不過是因為受了“魔鬼的誘惑”,才造成那些“奇思異想”進人到他的頭腦。看起來,他是要“真心誠意地痛悔前非”了。
讀懂“黑暗的中世紀”
宗教裁判所對所謂“異端”的審判,是我們談到“黑暗的中世紀”最常用的例子。這本書提供的宗教審判的具體過程,給我的印像是,哪怕罪名是荒謬的,但是審訊是嚴肅的、認真的,所以才留下那麼詳細的記錄。
那封懺悔書遞上去以後,主教和審判官並沒有束之高閣,置之不理,還真傳喚了梅諾基奧。他陳述了牢獄的狀況:“條件惡劣,泥涂遍地,昏黑陰暗,潮濕不堪”,徹底毀掉了他的健康,他躺了4個月下不了床,兩條腿和臉都浮腫了,聽力幾乎喪失,“倣如離體遊魂”。他哭泣著苦苦哀求,俯伏在地上卑微地請求原諒:“為冒犯了我主上帝而深感後悔”, 説是自己“愚蠢地被魔鬼所蒙蔽”,其實自己並不明白“魔鬼告訴我的那些東西”。他説自己並不為被投進監獄而感到不幸,還説假如不是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寧願在牢獄中度過余生,以此補償他對耶穌基督的冒犯”。但他很窮,必須靠著兩座磨坊和兩塊租的地養活他的妻子、7個孩子和幾個孫兒孫女。
似乎主教和審判官被他的懺悔所打動,對其給予了很輕的懲罰之後,便把他釋放了。但是令他不得離開所在地,禁止他公開談論或提及那些危險的想法;還必須定期懺悔,在衣服外面穿上一件繪有十字架的懺悔服,也就是説他在公開場合是一個戴罪之身。他要出獄,還必須有一個保人,一個叫比亞西奧的朋友出面為他作保。如果梅諾基奧違反釋放條件的話, 將繳納一筆罰金。梅諾基奧回到了家,“身心俱已殘破不堪”。
難以置信的是,他還“恢復了自己在鄉里鄉鄰中的地位”。儘管觸犯了教庭的天條, 遭到了懲戒,還被投進了監獄,但是居然1590年,他被任命為教堂的管理人,還監管教區基金。新的教區神父是梅諾基奧的童年好友,金茨堡猜想,他可能在這一任命中幫了忙。當時沒人覺得讓一位異端分子,而且實際上就是一個異端的頭子擔任這個職務有何不妥。按照金茨堡的説法,管理人的這個職位,經常由磨坊主擔任,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有一定財力墊付教區管理所需的資金,而他們通常都會延遲交付從信眾那裏收集的什一稅,從中賺上一筆。
隨著時間的流逝,梅諾基奧便試圖去除判決給予他的那些懲罰,即擺脫身著懺悔服和不得離開居住地的禁令。於是,在他被釋放的大約6年後,他決定前往烏迪內,去見新上任的宗教法庭審判官,請求免除這兩項責罰。雖然關於去除懺悔服,得到的回復是否定的,然而他行動自由的要求則得到了同意,可以在各個地方營生,以“紓解自己和家人的貧困處境”。
過去我們所知道的“黑暗的中世紀”,宗教法庭的審判就是為了清除異端,其實當我們進入到歷史的細節,卻發現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對照走出中世紀以後世界所發生的許多事情,我有時候認為,我們都不配稱之為“現代社會”和“現代人”,因為在近現代林林總總的對待人的野蠻殘酷和草菅人命,經常是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所望塵莫及的。我們看到夠多的實例,無數無辜的人被處死,並沒有審判,或者只是裝模作樣地、潦草地審判,成千上萬人的死去甚至並非他們有什麼離經叛道的思想,而只是那些主宰他們命運的大人物的隨心所欲,或者不過是滿足其個人的野心。
塵埃落定
按照金茨堡的説法,本來梅諾基奧過上了正常的生活,“昔日那場審判所帶來的後果,一點一點地被抹除了”。沒有想到的是,他想要去除兩項對他的限制,可能重新提醒了本來宗教法庭已經遺忘的案子。就是説,他本來已經度過了最嚴峻的時刻,雖然生活上有一些窘迫,但應該沒有生命之憂的。也可能他認為這個案子已經被遺忘,於是他自己口無遮攔的老毛病又犯了,最終斷送了卿卿的性命。
而置他于危險境地的,起因于一次稀鬆平常的談話。那應該是上一年的狂歡節期間,梅諾基奧在得到宗教法庭審判官的許可後,離開蒙特雷阿萊前往烏迪內。某天的晚禱時分, 他在廣場上遇到了一個叫盧納爾多·西門的人,開始閒聊了起來。他們曾經因為參加宗教節日慶典活動而相識。然而這次閒談,卻要了他的命。
盧納爾多給宗教法庭寫了一封告密信,彙報了這次談話的內容。哪怕是今天看來,這次談話與他在第一次審判的交代中,都算不得什麼驚世駭俗。梅諾基奧問:“我聽説你打算當個修士,真的嗎?” 盧納爾多:“這難道不是個好故事嗎?”梅諾基奧:“ 不是 , 因為這跟伸手要飯差不多 。”在隨後的談話中,梅諾基奧卻又開始攻擊教會,表明瞭多年前信裏面的懺悔並非是真的拋棄了他那些奇談怪論。
其實,這次告發並沒有得到及時處理,直到兩年後,即1598年10月,可能是出於偶然,宗教法庭的審判官在審核現有記錄時,把這個告發信與過去的審訊聯繫了起來,於是“宗教法庭的機器再次開動了”。
有趣的是,他再次被抓之前,知道對他的調查已經啟動,顯然他是有機會逃跑的,而且“他知道,他會因此而死”,但他並不想逃跑,因為他還記得他朋友對宗教法庭替他作的擔保 ,否則“他是會逃到日內瓦去的”。可見他還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他決定坐以待斃,哪怕“已經在展望自己的生命盡頭了”,他等待著“迫害者的到來”。
1599年6月末,他被抓了起來,7月他出庭受審,法庭問他是否想要聘請一位律師,他回答道:“除了請求憐憫之外,我不想再做任何其他辯護了;不過,如果我可以有個律師的話,我會 接受的,但我很窮。”當我們讀到這個細節,一定是沒有準備的,在中世紀的義大利,法庭難道會為一個貧窮的“罪犯”指定律師嗎?或者這個指定的律師會為那位“罪犯”真正地辯護嗎?
但是事實卻是一名法庭委任的辯護人被指派給了梅諾基奧,隨後,這名律師向法官們提交了一份很長的案情摘要,替“窮苦可憐”的梅諾基奧辯護。他宣稱,證據都是二手和自相矛盾的,這些證據顯然表明瞭被告人的“頭腦簡單和愚昧無知 ”,他請求將被告無罪釋放。這就是説,這位法庭所指定的律師,真的是站在被告人一邊,為他受到的指控竭力地洗刷,雖然並沒有成功。1599年8月,宗教法庭一致裁定梅諾基奧為“累犯”,決定對被告進行刑訊逼供,以獲取共犯名單。梅諾基奧的房子也被搜查。隨後,梅諾基奧被判處死刑並執行。
微觀歷史的生命力
除了卡洛·金茨堡,還有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Emmanuel Le Roy Ladurie)、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等活躍于微觀歷史的研究,他們的代表作不但得到了歷史學界的認可,也為領域之外的讀者所喜歡。
例如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Montaillou),研究的是14世紀法國一個山村的日常生活。宗教裁判所法庭案卷記錄,猶如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事無巨細,為重建若干世紀前法國山村生活提供了可信的資料。稍晚些時候的這個取向的作品有羅伯特·達恩頓的《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他依據不同的資料來源,包括民間傳説故事、手工工匠的自傳、城市指南、警察密探報告、狄德羅的《百科全書》、讀者與出版社的通信等,側面討論了早期近代法國的社會和文化。

《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美]羅伯特·達恩頓著,呂健忠譯,三輝圖書 | 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
還有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講的是16世紀中葉法國農村發生一個傳奇故事。農民馬丁·蓋爾離家出走多年沒有音訊,後忽然回到家鄉。幾年後,岳父把他告上法庭,指控他是冒名頂替者,但是他差點就讓法官相信了他的説辭,真正的馬丁·蓋爾出現了。這個故事在法國長期流傳,早年就有兩本書以這個案件為主題,其中一本還是參與此案審訊的法官所撰。以這一案件為藍本的演繹作品還有劇本、小説、電影等。戴維斯以微觀史的方法,不僅講述了生動的故事,還再現了當時農民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
由於這些年來對微觀歷史的興趣,使我對金茨堡的研究十分關注。幾年以前,當前文提到的《歷史筆記》雜誌做一個微觀歷史的主題,邀請我提交一篇論文。在邀請信中,專門提到了金茨堡與這個雜誌的那段歷史,我有幸成為這個雜誌的作者,似乎與金茨堡有了某種學理上的聯繫。雖然對這本書非常喜歡,也喜歡作者,過去在美國教書的時候也經常去洛杉磯(他退休前是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的教授),但是卻沒有想到要去拜訪他。不過,由於疫情,線上活動多了起來,當得知今年3月3日淩晨1點,他線上上有一個對話,還是決定看看這個線上講座,我看完了才上床睡覺,算是第一次見到了他本人,雖然是通過線上上,算是滿足了見到本書作者的好奇心。
上面提到的這些微觀史學的代表著作,中文翻譯本出版已經很多年了。金茨堡的第一本書《夜間的戰鬥》(The Night Battles: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中文本,也早就出版了,唯獨《奶酪與蛆蟲》這本書,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些年來,雖然關於此書的介紹甚多,但是讀者始終不得其真面目。非常高興這本書的中文版終於正式出版了。我想這本書的出版,對微觀歷史在中國進一步受到關注,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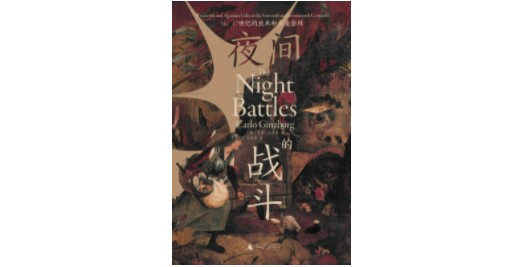
《夜間的戰鬥:16、17世紀的巫術和農業崇拜》,[意]卡洛·金茨堡著,朱歌姝譯,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
作者 | 王笛











 敦煌莫高窟: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敦煌莫高窟: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中國精神之工匠精神
中國精神之工匠精神 日本牡丹,花開時節艷無邊
日本牡丹,花開時節艷無邊 似是故人來
似是故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