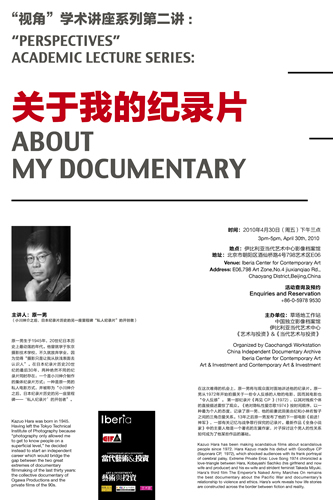 這是穿插在原一男先生回顧影展中的一場講座,被安排在《前進!神軍》放映剛結束後。原先生作為日本“私記錄片”的開創者在這次放映活動中被帶入國內觀眾的視野。他作品中的“私”,不簡單地意味著拍攝者和他的生活作為影片的內容被記錄,甚至不僅僅是指影片中作者“強加”的視角和“設計”的情景,原先生賦予他影片的“私性”一層更潛在的涵義。原先生的紀錄片誕生於他對那些早于他的日本六十年代紀錄片和紀錄片工作者的思考中。像小川攝製組那樣集體式的工作方式,以及從宏觀的社會結構和大的社會問題中尋求變革的可能性,在原先生看來是屬於“上一代人”的,他感覺自己已不再能認同那種集體的觀念,轉而從個體和自身出發,尋找社會中權力真正存在的地方——人的內心。在這次講座中,原先生以問答的形式談到了他提出的虛構紀錄片的概念,製作紀錄片對於他的意義,以及一些影片畫面外的內容…… 原一男:大家有任何問題想要問的,都可以現在説一下。我可以講很多事情,但是不知道你們想聽什麼。從那個小小的日本過來的,年紀已不輕的我,你們想聽什麼呢?你們已經看了三個片子了。 提問:看了《前進!神軍》這部影片後我非常感動,感覺那個片子裏男主角奧崎的表情,包括他非常迷信的表現很關鍵,在整個片子的質感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導演在拍和構思的時候是不是跟他之間有一個很有效的溝通?還是本身他的個性就很強? 原一男:對奧崎來説犯罪是他自我表達的一個方式,他一見到人就説:“我其實有三個前科。”對他來説這個前科是他的“勳章”,他的想法和我們普通人是完全相反的。他每次犯罪之後就被關到監獄裏,每次他都是單獨的一個房間,在那裏什麼都不能做,但就是那個時候他才會放鬆,在那兒他是自由的。這是一種悖論——他只能是在被關起來,沒有任何自由的時候,才是最自由的。每次從那兒出來,他又不自由了,又開始想,我還要幹一些什麼。他給自己一個壓力,就是我必須要做些什麼。他的人生就是這樣的反反覆復,你能理解他這個人嗎? 其實這個電影也是關於我的自我探索的,對我來説,我是一個非常懦弱的人,但儘管我懦弱,在我內心深處還有某種暴力的衝動。我一直對自己感到害怕,我要壓抑那部分東西,要不然它會把我弄瘋的。整個電影花了五年時間,但是拍攝的時間跨度是一年半。最後在奧崎和山田對峙的鏡頭裏,他們兩個激烈地爭論,那個時候我突然有了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他們兩個都是把自己整個人生的能量和激情拿出來在那兒相互對峙,那是種最激烈的能量之間的一個較量。我當時有種衝動,不是説當時出於任何理性,就是到他們最激烈交鋒的力量中心點去。一般的話兩個人在對峙,我們應該在他們第三角的位置,來回搖著拍攝。那個時候我在他們倆之間,激烈對峙線的中間,我站到那個中間去了,於是我就拍了這個狀態,一般不會是這個狀態的。一直拍了十一分鐘,那個時候一盤膠片只能拍十一分鐘。在那兒我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暴力衝動發泄了,每個電影裏都會有這種東西,這個電影就是在這個地方。於是我就用這種方式來制服我內心的野獸,這樣我才能活到今天。 在《絕對隱私•戀歌1974》裏面也有這樣的地方,就是生孩子那場戲,因為我不用投入其中了,她就是正對著我,那個孩子就生了出來,我已經是在那個接受的狀態上。然後在最強烈的磁場裏面,把自己內心的東西散發出來。可以説這是我拍紀錄片的最大動力。其實奧崎在電影裏顯得好像是很強悍,很粗暴的一個人,他不是那樣的。有一次他在東京開著車亂轉,碰到右翼的那些人,那些人就説:“哎,靠邊兒。”然後那個車就停在奧崎車的前面,上面有一個年輕人就下來走到奧崎身邊,他怕那個年輕人過來打他,所以他就在兜裏拽著一個扳手,那個時候他必須得把自己全身的殺氣充好了電,等年輕人過來的時候就先發制人了。奧崎總談起暴力,他知道自己不是那麼強硬,其實對他最重要的不是跟一個人打架,是跟整個國家政權在打架,所以必須要有很大的能量才行,他每天想的都是我怎麼才能充滿這種能量,然後他想了一個招就是積攢憤怒,理解嗎?他利用錄影機,在這個電影裏積攢他的能量。我們都是這樣,被拍攝的時候是比平時更有能量的,更注意力集中,所以他其實喜歡被拍攝是這個意思,就是他要利用錄影機的在場攢夠了能量,真的去殺影片中那個中隊長。經常有一些觀眾跟我説:“也許你不拍他的紀錄片,他就不會去殺那個中隊長,讓中隊長受重傷。”我也同意。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拍紀錄片是一個可怕的,危險的行為,但是奧崎渴望這種危險。 紀錄片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在這個電影裏,奧崎認為自己是“神軍平等兵”,平時他是一個很好的商人,態度特別謙恭有理,客人是很多的。一説要拍攝了,他就開始變成“神軍平等兵”了。這個“神軍平等兵”在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的,奧崎的想法是日本的天皇制的國家發生了戰爭,沒有給人們帶來幸福,他覺得應該否定這個國家,建立神的國土,這個神的國土才是自由的,沒有限制的,才能給人帶來真正的幸福,他要為了實現這個而去鬥爭。在錄影機面前,奧崎在表演變成一個神軍平等兵,在電影裏他是作為神軍平等兵來活著,電影中有兩個他自己,一個是平常的自己,一個是電影中的自己。神軍平等兵是他理想的自我形象,他在錄影機前表演他的理想形象。如果説從推理上來説,他就是想在電影裏面表演,來實現他理想的自我性,以此做一種自我完成。他有一次對我説:“能夠表演奧崎謙三的,只有我奧崎謙三本人。”當然了,誰能演他呢?你能感覺到吧,他先看了,我那邊是不是準備好開始拍了,才開始正式地説話。我特別討厭他每次都是這樣,然後我就想他的演技很糟糕,他其實真的是從頭到尾都想實現自我解放或是自我完成,其實從電影語言上來看,這就是虛構。所以我的這些紀錄片,最基本的東西是“虛構”。《戀歌》裏最重要的就是她自己生孩子的那個鏡頭,前邊都是為這個鏡頭做鋪墊的。對美由紀本人來説,她不想向她的母親一樣被制度和社會束縛著,她要通過自主生孩子來從那種束縛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其實是這樣的,她來演出一個女人如何從束縛中解脫出來,完成了成為新的她自己。 日本有一個非常權威的電影雜誌,叫《旬報》,非常有名,每年都要評最佳女演員,最佳男演員。最後武田得了最佳女演員獎。然後還有很多批評家來、選奧崎為最佳男主角的候選人,武田得的是第二位女演員,奧崎也是第二,這個聽起來其實是不可能的,因為紀錄片的人物跟劇情片不一樣。紀錄片和虛構電影、劇情片之間的疆界已經取消了。我不是説所有的紀錄片都是這樣的,我指的是我自己的這一類紀錄片。我認為十個導演有十種電影方法和理論,對我來説紀錄片是這樣的。我的這種電影方法是在七十年代,自己考慮和實踐出來的。説得太長了,你們有什麼想提問的嗎?我剛才回答那個電影,現在講演怎麼辦呢?已經走到這兒了就這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