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龍之介:不愛魔都愛帝都
在中國,芥川龍之介(1892—1927)是知名度最高的日本作家之一,就排名來説,大約緊跟夏目漱石,穩居第二。這主要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芥川文學獎,二是《羅生門》等電影,最近又多了一部新片《異鄉人:上海的芥川龍之介》。可是,芥川獎是在芥川歿後,由菊池寬創設的純文學獎項;《羅生門》雖然是芥川的小説,但廣為國人所知者,與其説是小説原著,毋寧説是導演黑澤明。換言之,國人對芥川龍之介的“了解”,多借助於文本之外的途徑,其實蠻可疑的。

根據芥川龍之介《上海遊記》改編的日劇SP《異鄉人:上海的芥川龍之介》(NHK,2019年上映)
芥川是小説家,也寫隨筆,《中國遊記》可以説是他最重要的隨筆作品。所謂“成名要趁早”,芥川是踐行者,早在東京帝大讀書時,便發表了代表作之一《羅生門》,受到大正文壇的矚目。1919年,芥川結婚,隨後辭去了海軍機關學校英文教員的教職,加入大阪每日新聞社(“大每”),成為領幹薪而無需坐班的簽約作家——這是與國民作家夏目漱石同等的待遇(1907年,漱石加盟朝日新聞社,成為專業作家),標誌著財務基本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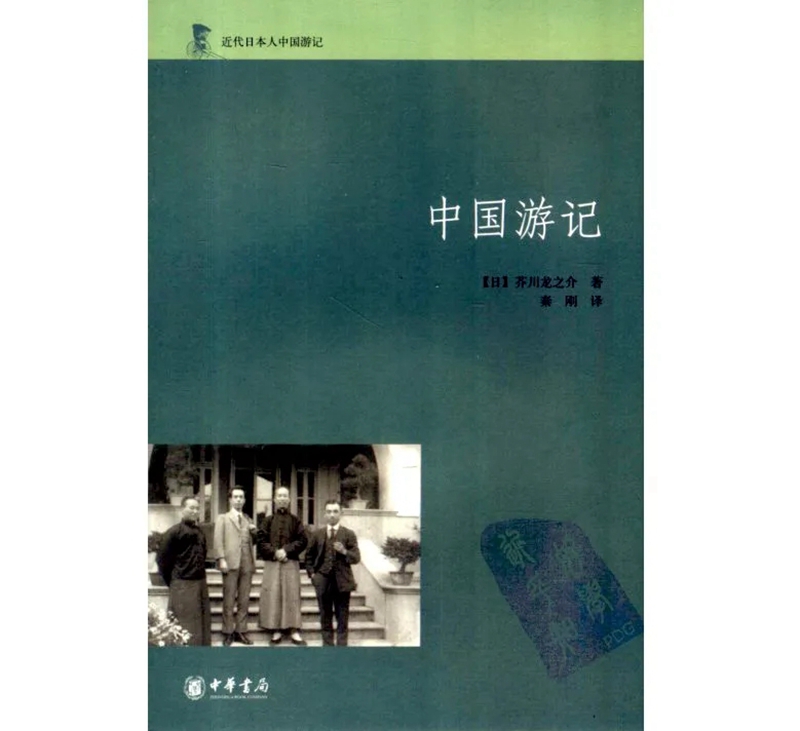
中華書局版《中國遊記》,芥川龍之介著,秦剛譯,2007年1月出版
芥川簽約大每後的頭一個大項目,就是中國行,也成了文壇大事。1921年3月9日,大每在東京上野的靜養軒,舉行盛大的壯行酒會,出席者多達四十人,其中不乏文壇頭面人物,如菊池寬、久米正雄、裏見淳、與謝野晶子、松村梢風、山本有三、室生犀星等。芥川抵達上海後的翌日(3月31日),“大每”在版面上廣而告之:“近日將連載特派員芥川龍之介的《中國印象記》”,報道“新興作家眼中新的中國”。……中國乃世界之謎,也是一個魅力無窮的國度。儘管古老的中國仍如老樹橫斜,新的中國卻已是嫩草吐綠。在政治、風俗、思想等方方面面,中國的固有文化無不與新興勢力犬牙交錯,而這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按報社當初的計劃,芥川應每天寫一節內容交付連載。可不承想,作家還在船上時就發起了高燒,加上暈船,以至於人一到上海就病倒了,被診斷為乾性肋膜炎,住進了醫院,且一住三周,日發一篇的計劃遂流産。芥川是頭一次出國,而上海是第一站,“這不僅是我對上海的第一瞥,同時也是我對中國的第一瞥”。

《異鄉人:上海的芥川龍之介》劇照。初到上海的芥川龍之介
芥川和前來迎接他的三位新聞界朋友(兩名大每特派員和一名路透社的英國記者朋友)一齣碼頭,“幾十個黃包車夫一下子就把我們包圍了”。被這一幕嚇到了的芥川作家,內心感到了強烈的違和感:
説起來車夫一詞,在日本人的印象中絕非一副臟兮兮的邋遢模樣。反倒有種威猛的氣勢,不無江戶范兒。可中國的黃包車夫,説他們是不潔的代名詞,也不為過。而且乍一看去,個個長得怪模怪樣。他們從前後左右各個方向各自伸著脖子大聲叫喊,不免令剛上岸的日本婦女感到畏懼。在被他們當中的一個拉住了袖子的時候,連我都情不自禁地往高個子的瓊斯君的身後退卻了。……看來在上海,倘無決死的氣概,輕易是坐不了馬車的。
就這樣,對黃包車夫的觀感便定格為芥川對上海和中國的“第一瞥”。此後,這種負面印象一路增殖,不斷被強化。作為日本人,芥川跟大每同僚學的頭一句中國話,不是“對不起”“謝謝”,而是“不要”,其內心的拒斥感可想而知。去梨園看戲,坐定後,馬上會有店小二遞過來熱毛巾和劇目單。對大壺茶、西瓜子之類,芥川會堅決地説“不要”,但熱毛巾還是要的。可自從他有一次目睹鄰座一位儀錶堂堂的中國紳士用剛擦過臉的毛巾又擤了一通鼻涕之後,索性連熱毛巾也“不要”了。

《異鄉人:上海的芥川龍之介》劇照。學會了第一句中國話“不要”的芥川龍之介
二十世紀初葉的上海,既是老牌列強“東方主義”想像的對象,也是新晉列強連結西方的入口。德富蘇峰、谷崎潤一郎、松村梢風、佐藤春夫、橫光利一等作家文人競相去魔都朝拜,出版了一大批遊記文學和隨筆小説。摩天樓、霓虹燈、夜總會、鴉片窟……既是人生冒險的“收藏夾”,也是知識人對自身的近代想像的調試和綵排——某種意義上,東洋知識人的“魔都體驗”,其實就是“近代體驗”。先於芥川兩年半,首次去上海的谷崎潤一郎,正值其藝術上的西洋志向的高峰期,魔都初體驗爽到不行,甚至動了“可在此置業”的念想。不過,那些表層的紙醉金迷般的浮華,對東京帝大英文科出身的芥川來説,卻無甚誘惑,他顯然更看重文化身份,或者説文化的“原産地”。殖民地的二手勾兌“假洋酒”,反而敗壞了他的胃口,令他有種虛無感:
這間咖啡館,比起剛才的“巴黎”來,檔次似乎要低得多。在漆成桃紅色的墻邊,一個留著大分頭的中國少年坐在一架碩大的鋼琴前,彈奏著樂曲。另外,咖啡館的正中是三四個英國水兵,正與幾個濃粧艷抹的女人跳著格調低下的舞蹈。最後,在入口處的玻璃門邊,一個賣玫瑰花的中國老太婆,在吃了我的一通“不要,不要”之後,茫然地看著水兵們跳舞。此刻,我的心情猶如在欣賞著畫報上的一幅插圖。這插圖的標題,不用説叫做“上海”。
芥川原本身子就弱,素有潔癖,加上在魔都生了一場病,人變得更加神經質。一個陰雨的下午,從1900年起就生活在上海的俳人島津四十起陪他遊覽魔都,在城裏轉悠,走到一處有名的湖心亭,芥川目擊了更駭人的一幕:
言歸正傳。那位中國人悠然地衝著水池撒起小便來。管他陳樹藩扯旗反叛也罷,白話詩的流行已日漸衰微也罷,日英續盟論甚囂塵上也罷,這些事兒統統不在話下。至少,從這個中國人的態度和臉色上看,有一種十分悠閒的神色。一間聳立在陰沉沉天空裏的中國式破舊亭子,一泓佈滿病態綠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這不僅是一幅調子憂鬱的風景畫,同時也是我們老大之國辛辣諷刺可怖的象徵。我對著那個中國人的身影凝視了許久。
“你瞧,這些石板上流淌的,不全是小便嗎?”四十起面露苦笑,三步並作兩步,拐過池邊去了。經他這麼一説,果不其然,我嗅到空氣中飄蕩著濃重的尿騷……
不過,千萬別以為芥川作家對上海的“偏見”,會損害文本的價值,他畢竟是有深厚漢學修養的大作家。我個人傾向於認為,芥川只是性格與魔都的氣場不合,僅此而已。但他對風俗文化的細節觀察與描寫,與章炳麟、鄭孝胥、李人傑等中國知識人的交流,均頗有可觀。如他也曾考察過魔都的鴉片窟和堂子等風月場所,對滬上文人叫局的風習,有相當細膩的描繪,有些細節恐怕只有日人才能體會並記錄下來,如雅敘園的局票上,“角落裏還印有‘勿忘國恥’的字樣以鼓動反日的氣焰”。諸如此類的小掌故,俯拾皆是,頗具史料價值。

《異鄉人:上海的芥川龍之介》劇照。拜會李人傑。李人傑原名李漢俊,中國共産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他家裏秘密召開的,會議後來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繼續舉行,並宣告了中國共産黨的誕生。
讀《中國遊記》,明顯會感到芥川對江南地區的熱情要大於上海,在《江南遊記》部分,對蘇杭寧和西湖靈隱的紀遊文字中,擬古趣味煥發,白樂天、趙孟頫等人的詩句信手拈來,在蘇州城的孔廟,一瞬間感到“蒼茫萬古意”,踏上長滿青苔的石橋,不禁吟出日本漢學家、詩人今關天彭的兩句詩:
休言竟是人家國,我亦書生好感時。
而今關當時正在北京。

20世紀初,駱駝商隊經過北京的城樓下
芥川最喜歡北京,“我在中國從南到北旅行了一圈,最中意的城市莫過於北京了”,“那裏的確是一個住起來十分舒心的地方”。他在北京逗留了差不多一個月,遍訪名勝古跡,寫下《北京日記抄》,文字帶“色溫”:如他喜歡登上城墻放眼遠眺,“數座城門看上去像是在青青的白楊和洋槐中被漸次織繡出來的一般”,如他注意到“北京城裏處處有盛開著的合歡樹”,“駱駝漫步在城外曠野中的景致,更是讓人涌起一種難以言表的感懷”,等等。他在北京見到了胡適和高一涵。原本也想見周作人,但周在西山養病,終緣慳一面。芥川與胡適見了不止一次,還一起吃過飯。據《胡適的日記》1921年6月25日記載:
今天上午,芥川龍之介先生來談。他自言今年三十一歲,為日本今日最年少的文人之一。他的相貌頗似中國人,今天穿著中國衣服,更像中國人了。這個人似沒有日本的壞習氣,談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芥川從3月下旬訪中,從南到北,一路鞍馬勞頓,生了不止一場病。但對他來説,北方好于南方,不僅“眼界為之一變”,而且“所見之物皆在無聲地展現著大中華和幾千年古文明的風采,我不禁被其雄渾與博大所深深打動”。他甚至預言:“將來中國實現統一之後,必然仍舊定都于北方。”可惜他沒能看到預言兌現。

在北京身著長袍馬褂的芥川龍之介(左)
總之,芥川作家頗接帝都的地氣,怎麼待著怎麼舒服。乃至後來偶爾以北京為半徑,到周邊地區做小旅行時,竟然平生了一種對北京的鄉愁。他在《雜信一束》中,記錄天津行旅的文字“十八”中寫道:
我:“走在這樣的西洋式街道上,真有一種莫可名狀的鄉愁啊。”
西村:“您還是只有一個小孩嗎?”
我:“不,我不是想回日本,而是想回北京!”
作者介紹:
劉檸,作家,譯者。北京人。大學時代放浪東瀛,後服務日企有年。獨立後,碼字療饑,賣文買書。日本博物館、美術館、文豪故居,欄杆拍遍。先後在兩岸三地出版著譯十余種。











 敦煌莫高窟: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敦煌莫高窟: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中國精神之工匠精神
中國精神之工匠精神 日本牡丹,花開時節艷無邊
日本牡丹,花開時節艷無邊 似是故人來
似是故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