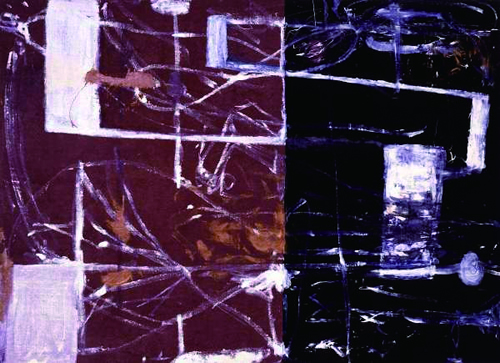 對於語言學家而言,他們關注表述與言語行為理論,已經強化了如下事實:某些語言成分,平行于它們熟悉的意義和指示的傳統功能,通過明確言説主體的各自位置或者形成某些情境結構(經典的例子是宣佈“學期開始了”的校長,這樣,學期確實開始了),能夠獲得特殊的語用效果。但是,這些語言學家已經斷定,他們必須將他們發現的意義限定在他們的專業化記錄(register)之中。然而,實際上這第三種“存在主義化的”功能——他們強調了這種功能,從邏輯上講,應該意味著與結構主義的控制明確分裂,不過語言學家繼續迫使語言限定在這種結構主義的控制之中。 這並非按理説是語言能指佔據了資本主義主體化已經提供給它的高貴位置,因為它為其普遍化對應物的邏輯提供了基本支撐,它形成了關於權力抽象價值資本主義化的政治學。其他政制能夠“管理”世界事務,這樣從其關於塊莖(rhizome)的超驗位置上能夠顛覆能指,而塊莖則是由象徵-意指的極權編織成的,以媒介為仲介的權力的現行霸權就根植于這種象徵-意指的極權之中。但是這些政制肯定不會通過自然發生説誕生的,相反,它們將會在新的分析、審美和社會實踐的交叉點上被建構和培育,這些實踐不能由後現代主義自發性輕易地提供給我們。 這些新的主體化實踐出現于後媒介時代,將由通訊和數據處理技術的一致性重新佔用大大地推進了,它們逐漸地使如下情況成為可能:1.提出集體協議和互動的新形式,最終實現民主的再創新;2.經由機器的個人化和微型化,經由表達的機制上協調方式的重新特異化,人們可以在這種聯繫中假定,最令人驚嘆的前景將會由數據庫向網路擴展的趨勢提供的;3.“存在論方法”的無限增多使之有可能同意改變創造性領域。 我們最後指出,後媒介經營者的去中心化和主體自主化並不等同於退步,也不等同於後現代主義的釋放類型。未來的後媒介革命將不得不由那些少數群體導向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今唯有這些少數群體仍然認識到了對人類來説具有致命危險的哪些問題:例如世界饑荒、不可挽回的生態惡化、大眾媒介對多樣主體性的腐化。 至少這是我所期待的,我的粗陋之言也是你們努力所尋求的。如果未來沒有遵循這些路徑發展,那麼它將不可能比目前即將結束的這個世紀持續得長久。 (董樹寶 北方工業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