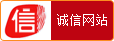大運河:載起文化之舟
大運河貫通南北,跨越多個區域,是一項水利工程,更是一個文化系統,學界對大運河文化的研究呈現出多樣化、多學科化、多區域化的趨勢。這一趨勢中蘊含了兩種學術旨趣。一種受實證科學影響,強調大運河的物質性,以水利工程和文化遺産價值為重點,推崇實證、量化研究,追求客觀性,避免主觀性。另一種受年鑒學派和文化功能論影響,強調大運河及其形成的文化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被建構,是人的認識、觀念的産物,突出人的主體性。應該説,從物化與人本角度認識大運河各有其理,只不過不能偏執一端,而需全面解讀。
物化與人本,是指大運河文化研究的基本意識和認知層次。物化是指哲學意義上的“物我界限之消解,萬物融化為一”,即大運河“物”的特性與“人”的融合;人本則更加突出“人”在“物我合一”中的尊嚴、價值、創造力和自我實現。具體而言,在分析大運河本體時,不能忽視相關人群對大運河物質本體及其文化的理解,以及這些現象之於當事人的意義,唯其如此,大運河文化分析才不至於死板僵硬;在詮釋人本價值和現實生活時,不能忽視人群背後因運河存在而産生的社會關係和權力框架,唯其如此,大運河文化詮釋才不至於空泛、玄虛。

張家灣運通橋作者/供圖
物化形態
大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的不同有二:一是人工開挖與維護。人工河是運河的基本屬性。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運河河道全由人工開挖。二是連接南北。與多數河流“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自然流向不同,大運河貫穿南北,“縮短”了南北區域之間的地理距離,勾連了不同水系,並因此形成對自然水系和生態環境的人為影響。因為“人工”,大運河註定多了“人事”的內容;因為更大範圍的“溝通”,大運河從開挖到斷流,每一次改變都意味著經濟與政治資源的重新配置,也意味著社會人群上下調適平衡模式的重建。但無論如何,大運河文化的各種“呈現”,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大運河的物質基礎決定的。物化的大運河是運河本體、運河影響下的生態環境以及文化遺産三者的疊加與融合。
狹義上的大運河本體是指水道工程、水源工程、工程管理設施、運河附屬建築工程及設施。歷史上,完成這些工程以維護運河暢通,不僅需要克服地形、水文、氣候條件的種種限制,還需要巧奪天工的技術支撐。大運河非一時之功,亦非一代能為,而是春秋戰國以來中國東部地區諸運河水利工程在不同時期因疏浚、拓寬、裁彎取直而被關聯起來的整體,是由多段運河、多種工程類型構成的相對獨立的工程體系,代表了中國古代水利規劃的最高水準。其水源工程自南而北,類型豐富,分別利用自然河流、泉水、江潮、水櫃等方式獲取水源,同時創造性地運用閘壩、供水涵閘等節制工程,實現水源供給,反映了時人“治水行漕”的經驗與科技創造。大運河的物化性上升至文化層面,最突出的就是人在其中的創造力以及物化之中的社會關係。
大運河開挖、暢通對於區域自然環境造成了影響。若從功能角度來區分,這影響有積極與消極之別。積極者,在綜合利用水資源的原則下,大運河對灌溉、排澇、泄洪都有一定作用。但同時,大運河造成的負面影響亦不可忽視,一是為獲取水源以維護河道通暢,人為改變原有自然河道的流向、流量甚至流經區域,築堤壩、建水櫃等攔水、儲水工程設施,改變了區域的生態平衡。如明中後期,為維持運道,黃河水流向徐、邳、淮、海地區,人為製造了洪澤湖,修建高家堰,造成蘇北地區水文環境的嚴重惡化。二是運河與農業灌溉爭水,影響到農業生産。如在會通河流域,清康熙皇帝嚴令禁止民間截水灌溉。
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後,它又增加了一個新的身份——世界文化遺産。《大運河遺産保護管理辦法》將大運河遺産界定為:“包括隋唐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的水工遺存,各類伴生歷史遺存、歷史街區村鎮,以及相關聯的環境景觀等。”歷史上,大運河流經區域包括了八個省市,具有運河元素的歷史“文化遺産”則無以計算,大致可分為運河水利工程設施遺址、古跡建築、古墓葬、古跡遺址、文物古跡、近現代重要史跡六個亞類。在斷流區域,運河本體河道已然不存在,成為真正的遺産而被保護和利用,人們更多地在“向死而生”的哲學領域和生活領域中找尋其文化傳承意義;而在依舊暢通的河段,則延續運河的活態功能和遺産價值。可以説,在一定程度上,文化遺産是大運河物化本體的現代身份。
河道本體、生態環境以及遺産身份,是大運河在不同時期物化形態的存在方式,三者都以有形的“物質”為載體而被修建、被保護、被利用,也被忽略甚至被破壞,人在其中的“主動而為”又使之演化成具有“運河”特性的制度、信仰、習俗、藝術、思想和生活方式等。

運河四大名塔之一的臨清舍利塔作者/供圖
人本意涵
大運河“人本”的意涵是指生活中凸顯運河人的主體價值、研究中探索大運河文化的模式與價值觀念,把運河文化的制度與習俗當作人們主觀態度的表現來看待,以獲取大運河文化的價值意義。對於人本的理解,應首先著眼于運河人這一主體,從運河的開挖、暢通、斷流的過程和現象中,討論歷代帝王、政治家乃至普通人對運河的利用;從運河文化的系統中,考察民眾對運河文化的創造與傳承。前者是“人定勝天”與“順應自然”的辯證,蘊含著政治家的謀略、管理者的技術甚至普通人的經驗和勞動,也是時勢與國運的一種體現;後者則是群體乃至個體的日常生活和集體記憶。二者的結合提供了運河人生活的場境,其中包括權力結構和制度框架,也包括把人定位於權力結構和制度框架的觀念和符號,它嵌在歷史之內,其特徵由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進程塑造並反過來影響了這些進程。
“運河人”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不是地域意義上的界定,而是以人與運河的關係為標準。當然,生於斯、長于斯的人對運河文化的認同度更強。運河人享受運河之利,也承受運河之重,但無論如何,運河都是一個巨大的磁場。“漕河全盛時,糧船之水手,河岸之縴夫,集鎮之窮黎,藉此為衣食者不啻數百萬人。”與同時代其他區域人群相比,職業化和流動性是運河人最突出的特點。職業化是指運河運輸功能所帶來的人群職業分化,比如漕軍(漕丁)、腳夫、船夫、閘夫、壩夫、驛夫、縴夫等,伴隨著國家賦役制度的變化,運河人實現了從“以農應役”到“以河為業”的改變。流動性強是運河人的又一大特點。雖然流動並非運河區域所獨有,但是作為政治、經濟和生活通道的運河,卻加快了流動的速度,並因此形成了運河人特殊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帶有更加強烈的“體制生存”和“市道依賴”傾向,並滲透到信仰、價值觀、社會關係、語言和習慣之中,變成了人們的生活日常和社會心態。
在新的歷史時期,與社會變革進程相伴隨,以等級為核心的生活方式、等級序列和倫理道德三位一體化的傳統社會文化體系,逐漸向以人為本轉化,生活的一切內容以提高人的生存、發展、享受、素質為宗旨,回歸日常的生活世界。當下,運河人在運河文化創造與傳承過程中的主體性,似包含著兩個層面,一是運河人自覺地參與大運河文化建設,“民眾在遺産地進行記憶傳承、地方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建構、塑造自我身份等文化實踐”,人們有意地進行遺産保護並實現大運河文化的價值再生。二是運河人生活狀態的自然呈現,人們在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等日常生活中沿承、構建著“大運河文化模式”。
因而,人本的大運河研究,本質上是把運河本體及其衍生出來的制度、習俗等當作人們的主觀表現來看待,追問什麼樣的大運河文化模式能給予人們的行為以意義,並能將這些行為統合於文化整體之中。
相互關係
物化與人本及其相互關係,是大運河文化研究的基本問題,同時也是認識大運河文化的兩個層次。在這兩個層次上,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大運河,還有其中蘊含的共同價值觀和人們的行為方式。對二者及其關係的考量與思辨,既有知識層面的凡事求真,也有思想層面的創造性解釋。解決物化與人本合一這一根本性問題,或可沿循這樣的路徑:在時空變化脈絡中勾勒大運河文化變化的態勢,關注不同時期的人在這個態勢發展節點中的“作為”,探討這些“作為”的文化意義。為此,有三個關鍵性的關係需要理順。
其一,趨同還是見異?“大運河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遺産廊道,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紐帶”,這是對大運河及其文化價值的基本認知,也是大運河文化的精神核心。作為國家工程,大運河的暢通依賴的是強大的國家機器,其流經區域在自然、地理、資源、人口、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天然差異。近代以來,黃運地區的衰落以及當下斷航區域運河文化“向死而生”的事實,都在説明文化塑造的區域差異。所以,理性認識大運河文化的關鍵還在於“見異”。但“見異”並非僅關注具體,相反是更加注重大運河文化精神的價值,注重大運河文化的獨特性在中華文化塑造中的作用。
其二,生生不息還是向死而生?大運河物質載體的存在,是大運河文化得以延續的物質基礎。生生不息是大運河的一種人文精神。那麼對於斷流區域而言,沒有運河的“運河文化”何以存在?在新陳代謝自然規律面前,衰退是一種必然之勢,即便在暢通河段,運河文化的內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大運河文化的生生不息,實際上包含著延續性與再生性,即所謂的“向死而生”。一方面,大運河文化遺産的存在,提供了再生的資源,一定程度上“將遺産的物質載體看作是可再生的,致力於在保護物質載體與發揮遺産的功能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必要時優先考慮遺産功能的延續”;另一方面,文化不會伴隨著物質載體的消亡而消失殆盡,因為在人的代際傳承中,它已經沉澱在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之中,顯于生活,隱于精神。
其三,百姓日用還是道法之常?如果説歷史上的大運河文化是國家機器運轉的副産品,那麼現代的大運河文化就是託生于強大民族文化自信基礎上的“文化塑造”。這種塑造建基於傳統,也來源於生活。家常日用,乃“道”之所寓。大運河的“人文”內涵涉及人性、人事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涵育、道德修養、倫理教化等,這些都來自於人的生活。所以,實現文化的再生以及人本運河的研究,需要進入到大運河的“細部”,將觸角下沉,從日常的勞動、消費、宗教、閒暇、交往中了解運河之於民眾的影響,以及民眾所創造的生活背後的文化發展軌跡、文化體系、文化民情,從中發現大運河所蘊含的道法原則。可能只有做到這一點,大運河的道才能夠其義自見。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民間文獻與京杭運河區域社會研究”(16AZS014)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煙臺大學學報編輯部)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