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軍為何不曾征服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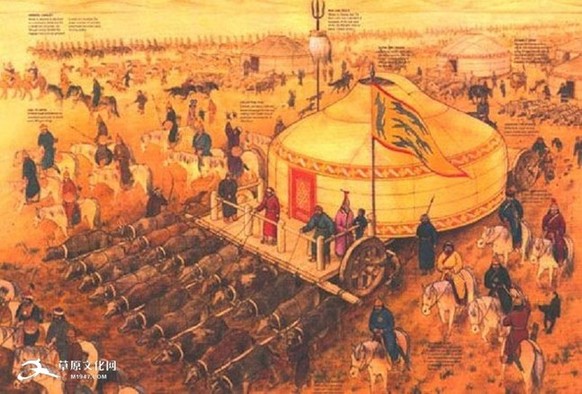
蒙古帝國在十三世紀的興起可以説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異數,幾乎沒有人會想到一個上一個世紀還默默無名的遊牧民族,竟能快速征服大半個歐亞大陸。蒙古彪悍的騎兵像狼群般狂飆過漠北草原與中原大地,終於來到了遙遠的南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小小的安南,蒙古大軍卻接連三次沉沙折戟……
三度敗北的蒙古軍隊
1252年,蒙古軍隊從甘肅出發,途經川西高原遠征大理。這些從北方乾燥的草原上來的將士和馬,居然能夠抱著吹足了氣的革囊,伏在被急流衝得起伏不定的筏子上,勝利渡過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進入雲南。戰爭本身是不值一提的,翌年,大將兀良合臺就率軍擒獲大理國王段智興。雲南自唐朝天寶年間起脫離中原政府管轄的局面結束了。
攻滅大理是蒙古帝國對最頑強的敵人——南宋——形成戰略合圍的重大步驟,在雲南被納入蒙古版圖之後,南宋在陸上已經陷入C形包圍,只剩下了與安南的邊界尚不在蒙古人的掌控之中。也正因此,安南成為蒙古軍隊的下一個目標,在遣使勸降被拒之後,1257年兀良合臺率軍三萬入侵安南,揭開了蒙古帝國與陳朝激戰的序幕。
大元與小小的陳朝
這是安南軍隊首次在戰場面對全世界最強大的蒙古軍隊,雖然擺出了步象騎兵的混合陣勢,仍被兀良合臺擊潰。蒙軍趁勢進入安南首都升龍(今河內),卻只得到一座空城,僅呆了九天,以暑熱難耐兼之糧食已盡,被迫撤軍,路上又遭到安南地方豪族武裝的襲擊而大敗,沿途疲憊不堪,所到之處亦不敢劫掠,故人們稱之為“佛賊”。這對小小的陳朝而言,當然是一次巨大的勝利,後世的陳仁宗為此寫詩云:“白髮老頭兵,常談元豐事。”
隨後二十多年裏,蒙古(元)忙於對宋作戰,無暇顧及僻處一隅的安南。等到滅亡南宋統一中國之後,忽必烈決心兼併安南。1285年初,元軍兵分六路進攻陳朝。鋻於第一次戰爭的經驗,部隊中增加了一些曾參加過征服南宋和習慣於在中國南方作戰的高級將領,比如崖山之戰時擔任張弘范副手的李恒這次亦在主帥鎮南王脫歡(忽必烈第九子)帳下。元軍的人數也大大增加,據《大越史記全書》載為五十萬人(這當然是誇大其詞)。正面戰場上,元軍再次擊潰陳朝軍隊,佔領升龍,但安南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元“軍困乏,死傷亦眾,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脫歡遂于當年五月撤兵,歸途又遇安南軍隊伏擊,李恒膝中毒箭,歸國後毒發身亡;脫歡本人則是鑽在銅管裏,讓士兵抬著,才免於一死。
忽必烈不甘失敗,又集中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漢軍7萬,附船500艘和雲南兵6000人、黎族兵1.5萬人捲土重來。1287年12月,元軍由脫歡率領,分兵三路第三次進犯安南。兩路是從廣西、雲南來的步兵和騎兵,此外還增加了一支水兵,從海路沿著白藤江(鄰近越南北部下龍灣的入海口)進犯。陳朝軍隊再次放棄升龍,堅壁清野,迫使元軍于次年三月糧盡而退。
白藤江,陳朝軍隊事先從森林裏砍伐樹木,削尖後插入江中,當元軍戰船魚貫而入白藤江時,潮水正在下落,陳軍出其不意地猛烈進攻,把元軍船隻驅至暗樁水域,當潮水下落時,元軍的船多數撞沒于木樁上,全殲元軍水軍,是為白藤江大捷,陳朝大儒張漢超在越南漢賦名篇《白藤江賦》中稱之為“再造之功,千古稱美”。而到了2016年3月初,根據越南媒體報道,越南總理阮晉勇日前也批准了在這裡建設白藤江戰役遺跡保護區的議案。
白藤江戰役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小小的安南再次擊敗了龐大的大陸帝國。元軍戰敗的消息甚至傳到了遙遠的波斯,伊兒汗國的史學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記載,“他們(陳朝)的軍隊突然從海上、森林裏和山上的埋伏中出來了,擊潰了正忙於搶劫的脫歡的軍隊。”
“興道大王”的功績
對於蒙古(元朝)而言,陳朝實在是個難纏的敵手。陳朝朝廷甚至下令“凡國內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于山澤逃竄,不得迎降”。雖然也出現過一些叛降蒙元者,比如陳仁宗的一個弟弟及《安南志略》的作者黎崱,但整體而言陳朝統治集團的抵抗意志是極為堅定的,幾乎可與同一時期的日本鐮倉幕府相垺。只不過,“元寇襲來”時的鐮倉幕府更多依仗的是從天而降的“神風”不戰而勝,陳朝卻更多的需要在戰場上真刀真槍地與蒙古軍較量。
陳朝本身是作為外戚篡奪了原本屬於李朝的皇位,影響至今的一個結果是強令越南李姓者盡改姓“阮”,使後者成為越南第一大姓。為防止自己重蹈覆轍,陳太宗(1218年-1277年)規定宰相和重臣都由宗室擔任,確保了宗室對皇帝的忠誠。在眾建諸侯的體制下,擁有領地的皇室貴族們不僅僅是為了他們的國家,也為了他們自己的封疆而需要努力驅除外來入侵者。
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興道大王陳國峻(?-1300年)。從私人角度講,他其實是完全有理由去當“帶路黨”的。陳國峻其父陳柳為陳太宗兄,陳朝的實際建立者陳守度強迫陳柳把老婆讓給陳太宗,陳柳咽不下這種奪妻之恨,臨死時告誡兒子陳國峻一定要為其報仇。結果當元軍來襲,手握兵權的陳國峻卻放下私仇,沒有聽從父親遺言去奪取皇位。他不僅凜然誓言“先斷臣首然後降”,更寫作了名篇《檄將士文》(《諭諸裨將檄文》)以鼓舞士氣,這篇滿是中國歷史上忠勇人物(從為智伯復仇的豫讓到堅守釣魚城的宋將王堅)典故的檄文直斥“蒙韃乃不共戴天之讐”,告誡部下“汝等既恬然不以雪恥為念,不以除兇為心,而又不教士卒,是倒戈迎降,空拳受敵,使平虜之後,萬世遺羞,尚何面目立於天地覆載之間耶”!在其激勵下,許多陳朝的普通士兵都在手臂上刺上“殺韃”二字,發誓抵抗到底。
除了鼓舞士氣之外,陳國峻更重要的貢獻是為弱小的陳朝找到了一條取勝之道。所謂“彼恃長陣,我恃短兵,以短制長,兵法之常也”,“若用蠶食緩行,不務民財,不求速勝,則拔用良將,觀其權變,如圍棋然,隨時制宜,收得父子之兵,始可用也。”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在正面戰場無法抵禦蒙(元)軍的陳朝軍隊每每主動後撤,以拖待變;並在敵軍後勤補給力有不逮時趁勢反擊而獲勝。
選擇白藤江作為決戰戰場也正是出自這位興道大王的計劃,當時越南的水軍可以説是唯一勝過敵軍的兵種,就連元人也承認,陳朝戰船“船輕而長,船板甚薄,尾如鴛鴦翅,船弦兩側甚高。每船有三十人划槳,多可達百餘人。船行如飛”。以己所長擊彼之短,豈有不勝的道理。
天時·地利·人和
除去陳朝本身的抗戰,可以説蒙古軍隊也輸掉了天時、地利、人和。連西方史家都發現了這一點,《多桑蒙古史》記載,第一次入侵時,元朝軍由於“熱不能堪,班師”;第二次入侵時“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眾”;第三次入侵時又是“軍中將士多被疫不能進”。安南屬熱帶季風氣候,氣溫高,濕度大,風雨多,旱、雨季明顯,大部分地區5月至10月為雨季,11月至次年4月為旱季。元軍士兵多來自北方,故元軍出兵多在下半年,正值安南為冬天旱季的時候。一旦被拖至雨季,瘟疫肆虐,蒙(元)軍隊實在是在“鬼天氣”裏吃夠了苦頭。雖然不能説蒙古軍隊是完全敗給了天氣,畢竟此前已經征服了同樣有暑雨並流行瘴癘的嶺南地區,但入侵安南,某種程度上的確是在逆“天”而行。
另一方面,安南的地形複雜,山地、高原、河流互相交織在一起,很少有一馬平川的大平原。連元朝將領自己都意識到,這樣的地形“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使得遠征安南的元軍已不是單一的騎兵,而是以步兵為主。對安南的戰爭,也更多是傳統中原式樣的戰爭:既無依靠隨行羊馬和狩獵解決給養的條件,也不能靠“因糧于敵”之法獲取給養。軍隊給養只能靠國內供應,勢必“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而不能“羊馬隨行,不用運餉”。漫長而脆弱的補給線也確實成為入侵安南的“阿喀琉斯之踵”。
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忽必烈“內用聚斂之臣,視民財如圖苜,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實在是窮兵黷武,殘民已極。常年對外作戰使得“老兵飽嘗征戰味,聽説安南愁滿面”;兵糧多聚,徵丁從軍更導致田地無人耕種,江南一帶“群生愁嘆,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産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至元二十年(1283年),江南“相挺而起”的起義“凡二百餘所”,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激增為“四百餘處”,幾乎遍及整個長江以南。面對如此之多的起義叛亂,元廷不得不抽調一部分軍力進行鎮壓,從而削弱了元軍南征的力量,因此,雖然忽必烈仍不甘心,先後三次圖謀再徵安南,但終於無法如願,國內反對聲浪卻日甚一日。當1294年忽必烈去世後,元廷立即下詔停止征討安南。
就這樣,在蒙古軍對其他地區以秋風掃落葉之勢進行武力征服的時刻,越南卻在歷經三次與元軍激烈的軍事對抗之後,固然其國內也是一片“往年大軍在此,燒燬屋舍,開發先人墳墓,骸骨零露”的慘狀,卻基本上阻擋了元軍的攻勢,保住了自主統治,以致當時已是太上皇的陳聖宗(?-1290年,1258年-1278年在位)在拜謁陳太宗陵時寫下了如此自豪的詩句:“社稷兩回勞石馬,山河千古奠金甌。”(郭曄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