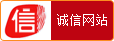千年運河貫穿古今 江南文脈奔涌不息
大運河,上下2500餘年,綿延3000多公里,流經中國版圖的8個省市,是世界文化遺産,更是中華文明的標誌。清波一脈通古今,開鑿于先秦時期的江南運河,作為中國大運河的組成部分之一,將江南的各個城市如明珠般串聯起來。大運河帶來的是城市發展的滋味源頭,是城市騰飛的汩汩清流,它帶來了江南的千載繁華,見證了江南城市的興替更疊。時至今日,江南運河始終是京杭運河運輸最繁忙的航道,在區域經濟社會生活中扮演著無可替代的角色。
繁盛社會經濟的源頭活水
江南運河與長江、江南自然水網所共同形成的資源優勢,是江南社會經濟繁盛的源頭活水。江南運河,北起江蘇鎮江,繞太湖東岸經常州、無錫、蘇州,南至浙江杭州,貫穿長江、太湖和錢塘江三大河湖水系,同時,又通過吳淞江、太浦河連接上海。從經濟學角度講,所有運輸當中,水運是最便捷且便宜的。自春秋戰國以來,江南運河與天然的江河湖海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水網,形成了四通八達的水運交通網路,奠定了水鄉澤國的自然與人文生態。隋朝開始開挖疏浚的江南運河,被納入到全國統一的漕運體系,是眾多江南地區運河中最主要的漕運水道。
在長三角地區,江南運河與長江一起,一橫一縱拉開了整個江南地區最重要的水系骨架,它與長江共同成為江南水運交通網路的兩條主幹線,同時,又與江南自然水網一起共同構成了影響江南社會經濟文化繁盛的源頭活水。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曾説過:“隋唐時期交通相當發達,運河和長江的水上交通尤為當時後世所稱道。運河有不同的渠道,渠道相互連綴,可以通到許多地方。”
以三江之一的吳淞江為例,《尚書·禹貢》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記載。吳淞江的別稱“松江”,其實就是現在上海地區古代行政建置“松江府”的命名來源。吳淞江下游近海處被稱為“滬瀆”,是上海市簡稱的命名來源。據資料記載,吳淞江(蘇州河)上海段是上海近代最早的工業區,民國年間有修造船、麵粉、棉紡織、絲織、化工、冶金機械,甚至水電煤器具的加工廠,在蘇州河岸線,集中了數以千計的工廠,其中的紡織廠、麵粉廠、火柴廠、鋼鐵廠、造幣廠、啤酒廠、無線電廠、制藥廠、石油化工機械設備廠等,都曾在上海乃至全國工業經濟史上創下紀錄。
以蘇州為例,蘇州有“水韻古城”之稱,其“水陸雙棋盤”的城市格局一直延續至今。“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水城的格局,是由乙太湖為源頭和大運河為骨幹的江南水系將星羅棋佈的湖泊河蕩和縱橫交錯的水巷河道連成一片,從而形成的一片舉世無雙的水鄉世界。黃金水道的運河水系、水鄉古鎮的風貌水系、三橫四直的城內水系以及逐水而建的園林水系,各類水系結構交相輝映,融匯合璧,形成了一組世界上罕見的東方水城風貌圖。而依靠這樣的水網系統,蘇州成為歷史上南來北往人員、物流的重要集散地和中樞地。借助大運河,漕運和海運在蘇州形成了彼此呼應的聯動效應,為南北物資平衡與往來、塑形全國統一性的社會與市場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孕育江南文化的豐沃土壤
大運河,尤其是江南運河的暢達,為江南文化的發展孕育了豐沃的土壤。江南是一個依水而生、依水而興的地方,大運河滋養了江南的經濟發展。在歷史長河的絕大多數時期,江南運河沿線受戰爭襲擾相對較少,隨著“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亂”後的三次南遷,江南地域的人口快速增長。據史書記載,“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於此”。同時,發達的水運又催生了商業文明的萌芽與發展,南北經濟文化的頻繁交流,使江南沿運河地區長期成為古代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蘇州更是在明清時期一度成為江南乃至全國文化中心地帶。朝鮮人崔溥在其《漂海錄》中有一段話:“蘇州古稱吳會,東瀕於海,控三江,帶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淵藪。海陸珍寶,若紗羅綾緞、金銀珠玉,百工技藝、富商大賈,皆萃於此。自古天下以江南為佳麗地,而江南之中以蘇杭為第一州。此城尤最。……閶門碼頭之間,楚商閩舶,輻輳雲集。又湖山明媚,景致萬狀。”
清代宮廷畫家徐揚用了24年時間畫了一幅全長1225釐米,比《清明上河圖》還要長一倍的畫卷,取名為《盛世滋生圖》,後改名為《姑蘇繁華圖》。畫面自靈岩山起,由木瀆鎮東行,過橫山,渡石湖,歷上方山,介獅和兩山間,入姑蘇郡城,經葑、盤、胥三門出閶門,轉山塘街,至虎丘山止,畫筆所至,連綿數十里的湖光山色、水鄉田園、村鎮城池、社會風情躍然紙上,被稱為研究250年前“乾隆盛世”的形象資料。這幅畫是研究江南運河和江南文化最好的資料之一,但其本身,也是江南文化最好的表達之一。
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統計,明清兩朝全國錄取進士51681人,其中明代為24866人,清代為26815人。江南共考取進士7877人,佔全國15.24%,其中明代為3864人,佔全國15.54%,清代為4013人,佔全國14.95%。總體而言,明清兩代每7個進士,就有一個出自江南。
英國文化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提出了“狹義文化”的早期經典學説,即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複雜整體。江南文化,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其文化門類繁多,文化內涵深遠,文化品質高超,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超越了文化本身而存在於所有嚮往精緻、典雅、宜居、詩性生活的國人的心裏。
明清時期的人,凡是有一定文化的,中過舉的,做過官的,可以説沒有不經過運河的,運河“是聯結中國南北、貫通中國與世界,集中展現明清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里程的人類寶貴遺産”。
傳播江南文化的不竭動力
江南運河的流通,為江南文化的輸出與交融暢通了渠道,是江南文化傳播不竭的動力源泉。事實上,大運河全線貫通後,不但成為南方漕糧北上的輸送線,而且成為南北之間商品往來、人文交流的最大通道。其實,作為古代中國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上文化的南來北往從未停止過。如翁俊雄先生説:“德宗興元以後,汴河復通。此後,南來北往的旅客,多經此路。”
不止是唐宋,在明清時期,江南經濟與文化獲得更高層次的發展,大運河的交通樞紐意義也變得更加重要。
以崑曲為例,嘉靖年間崑曲興起後,到明末“今京師所尚戲曲,一以昆腔為貴”,一時間竟出現了“多少北京人,亂學姑蘇語”的盛況。明末徐樹丕説:“四方歌曲,必宗吳門,不惜千里重資致之,以教其伶伎。然終不及吳人遠甚。”
以崑曲為代表的江南文化的北上傳播中,運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蘇樣、蘇意、蘇酒、吳饌、蘇作等也通過運河傳播至全國各地,以致明代萬曆年間的王士性説:“姑蘇人聰慧好古……又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又如齋頭清玩、幾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為尚,尚古樸不尚雕鏤,即物有雕鏤,亦皆商周秦漢之式,海內僻遠皆效尤之,此亦嘉隆萬三朝為盛。”不僅如此,這些江南的物件以及引領的潮流甚至於一度因其魅力而流傳至日本、朝鮮、琉球和西歐各國,如姚士麟曾援引中國商人童華的話説:“大抵日本所需,皆産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絹,松之棉布,尤為彼國所重。”
而因為有了運河,江南文化北上之路暢通,中原地區的士大夫則因為仰慕、追捧江南文化而紛紛南下。戲劇大家孔尚任在《郭匡山廣陵贈言序》中寫到:“天下有五大都會,為士大夫必遊地,曰燕臺、曰金陵、曰維揚、曰吳門、曰武林。”其中三個是運河城市,而且集中在江浙兩省。這一來一往,文化交流、融合的良好動線便形成,在文化的南北交融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融匯貫通。
1843年,上海正式開埠。國外勢力進入,開闢租界,獲得了沿海和長江的航運權,帶來了工業化的因素。江蘇省社科院王健教授論述:“上海的崛起,標誌著中國的經濟重心區域由‘運河時代’走向‘江海時代’。”其實,運河時代也好,江海時代也好,乙太湖流域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自始至終都是地緣相接、同根同源的。應該説,自宋以來的杭州,到明清時候的蘇州,到民國以來的上海,再到現代的長三角一體化城市群,江南文化的城市表達在千年運河的起落中呈現。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熊月之對此有精闢的論述:“在宋代‘城市革命’的大背景下,江南的城市逐漸取代了原來農村的文化功能,尤其伴隨著明清以來大量鄉間士紳移居城鎮,江南文化最精華的部分都已經轉向城市和城鎮之中。近代的海派文化也是直接繼承自江南的城市文化。”
因此,新時代,對接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江南文化品牌的打造、“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與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戰略的協同發展問題,擦亮中國大運河的金字招牌,以國際化的視野做大做強“江南文化”品牌,不僅是薪火相傳活化千年文化資源資産的需要,更將是面向未來增強文化自信和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的戰略選擇。
陳璇(作者係蘇州市職業大學石湖智庫副秘書長、教授,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副院長。)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