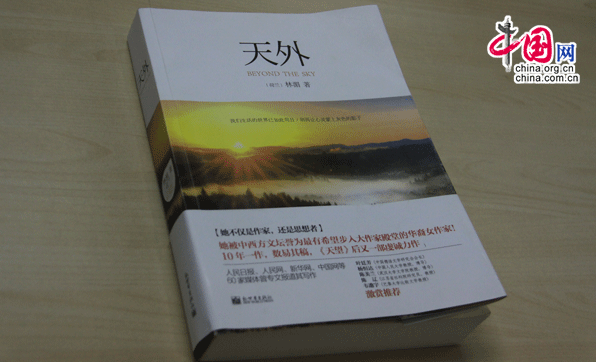實錄

林 湄
林湄:十年磨一劍,文學即人學

王紅旗(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女性文化》學刊主編):尊敬的各位導師大家好!非常歡迎大家百忙中抽出時間親臨中國女性文化論壇,參加“荷蘭華裔作家長篇新作《天外》的研討會”,這次研討會是我們和新世界出版社聯合主辦。外面是寒冷的冬天,會議室裏暖意熔融,我們相聚在這裡談論文學,是非常幸運的事。
首先介紹一下林湄老師,林湄老師是海外女作家,可能大家不像對國內女作家那麼熟悉,林湄老師新出版的長篇小説《天外》,是《天望》的姊妹篇。她是十年磨一劍,她到歐洲的第一部長篇小説《漂泊》是1995年出版,《天望》是2004年出版,再十年磨一劍,新長篇《天外》2014年出版11月才出版問世。
她是世界華文文壇上非常重要代表作家之一。我説明兩點,第一點,她富有大悲憫的宗教境界,追求普世價值的經典情懷,是一位嚴肅的純文學作家。在這樣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裏面,這樣的作家能夠堅守創作幾十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我們尊敬的。2004年出版《天望》一齣版,就受到世界華文文學評論家的關注,贏得廣泛讚譽,我們曾做了題為“洞察世間萬象,尋找人類文化與靈魂救贖之策”的專題論壇。第二點,她的作品不是那種特別宏大的架構,是畫卷式的網狀結構敘事。她能夠把詩歌、散文、學術、哲學、宗教等都融入她的小説裏,在閱讀她的小説的時候,牽動你的可能不是情節,而是她的思想和精神流向。所以,評論家們常説林湄老師不僅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思想者。這在海外華文作家裏是不多見的。這次她特意為新作《天外》出版而回國,今天我們對她的新作《天外》進行研討,大家一起鼓掌,祝賀她的新作出版。下面首先讓林湄老師來談一談,她從《天望》到《天外》的創作感受,大家歡迎!
林湄:(荷蘭華裔作家歐華文學會主席)
謝謝各位專家、老師的到來,在純文學不景氣的當下,有機會與祖國同行者座談文學,實在難得,我再次對各位深表謝意。
我祖籍福建福清市,出生在絲綢之路的泉州,華僑世家,70年代移居香港,90年代移居歐洲,現在是荷蘭籍,一生經歷了社會主義、殖民地香港及資本主義社會,雖仕途坎坷,命運多舛,但植于我靈魂深處的根本東西還是中國文化。
我從小就喜歡文學,頗有文學天賦,但今天看來不算什麼,主要還是靠勤奮和契而不捨的毅力。在香港中國新聞社工作的時候,除了工作外業餘時間寫散文、短篇小説、長篇小説等,題材大部分跟我個人的經歷與週遭人的命運有關係。
我是到歐洲後才對“文學即人學”的感悟,確信了無論歐洲人還是東方每人平均離不開人的共性和個性,隨著生存環境的變化、歐洲深厚的人文主義思想以及21世紀資訊科技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促使我想起歌德1827年1月對愛克曼論及的“總體文學”,即對“世界文學”的再思。
“世界文學”不分民族、身份和國界,觸及的題材也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即人的徬徨,迷茫,生存處境以及對財色生死問題的探索,居住地球村裏的人,任何榮辱福禍均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何況還有諸多形而上的問題困擾著人類——人活在世上到底是為了什麼?每天忙忙碌碌又為了什麼,精神和物質、靈與體、有限與無限等等問題引發我思考的興趣。
1995年6月,在荷蘭召開了我個人的作品研討會,有50多位學者專家參會,80多歲的《紅樓夢》法語翻譯家李治華説“林湄的小説題材多是關注社會的重要問題”,比利時漢學家魏查理院士表示“林湄的小説兩種文化背景的每人平均能接受”,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當代文學教授戴翊上交萬多字評論“女性的命運與輝煌”,等等論文,以及會後有20多家的傳媒報道,但我覺得文學藝術是無窮無盡的,與世界經典文學作品還差得遠,決意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
此後,我拒絕一切誘惑,甘於清寂、淡泊名利,沒有辦法去改變社會現實,只好將思考融入我愛好的文學創作裏,用十年時間完成50萬字的長篇小説《天望》,男主角是有救贖思想的人,他以簡單對付世界的複雜,世人覺得他傻,他卻覺得世人傻,認為眾人活得又累又愚昧,個個均在追求財色和物質東西-------
《天望》寫完了,出版後獲中外專家好評,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生活在繼續,社會在改變,科技在發展,生命短暫,文學卻沒有完結------更重要的是,其間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也影響了海外華人。華人帶著完美主義的理想,從東方到西方,不料西方漸漸沒落,東方卻在崛起,漂泊者自然對離散、移居、身份等詞語有著更多的解讀和理解,我不由想起《聖經》裏的一句話意,一生勞苦愁煩卻只得一口飯吃。
可見,現代高科技與經濟發展並沒有帶給人類真正的快樂和幸福,相反,其帶來的付作用卻隱約地影響了人類的精神生活與靈魂力度,使其潛移默化的異化,或怪誕、或萎縮、或不知所措-----
藉著對社會人生的憂患和擁有的創作激情,我再次用十年時間完成了《天望》的姐妹篇《天外》。
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思想相當複雜,思考多於書寫,每一章,每一個人物均寄託了對社會、人性、生存、高科技發展的沉思,於是,以第三空間的視角敘寫眾生相,集平凡人的生活、際遇和命運表達人生的勞苦與愁煩及無奈焦慮的存在。書裏的人物均是現實生活中群體的代表,如一個慾望的結束就是世人另一慾望的開始,永遠不會滿足,中國人如是,西方人也是如是。
物欲的充塞,使人的靈魂都丟失了,作為作家就有了負擔,只是無法改變現實,幸好依然熱愛文學,加之在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天真無知,常常做蠢事,因而,寫作是我承受命運的最佳狀況,也是我祈禱似的生存方式。
有人説,你的小説不入流,難讀,難懂,與中國傳統小説藝術形式和表達方式有距離,給閱讀和審美習慣帶來難度與費解。確實,近20多年來,我的創作理念和藝術追求不盡與傳統文學觀不同,也與自己1995年之前的創作不一樣了。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我離開祖國已41年,“根”既移植,吸收的養份就有所變化,結出的果子自然也會不同。為什麼要一樣呢?事實證明,即使在同一社會環境下成長、同校同係的畢業生,也會出現不同的求索精神與出路。何況,古今中外,沒有一成不變的藝術觀,也無永遠絕對的“正確”,或出於我智、識的求索,或與我生存環境有關,或因我較具前緣性意識,所以,行走在文學藝術的求知路上,喜歡獨立特行,希望在探索中創作獨具一格的作品,將傳統小説強調故事、情節、重懸念、衝突、高潮等創作法與西方的慢節奏、細觀察、重視人內在意識和心理變化的特徵相融或摻合,在敘述命運和各人性格裏反映社會人生,讓藝術結構和形式更好地表達人類生命底本質,當然,更希望作品對讀者有所思,有所啟迪,不是看完就完事的感覺。
我崇善經典,有些“離經叛道”是求索。即楊老師所説,形而上思考,形而下觀察,通過幾個家庭各人的命運和日常生活各式各樣的麻煩,反映現代人的心靈被物化、財化、色化等扭曲了,其心態與作為就是社會的寫照,讓人思索生存的艱難、無奈與感嘆!
以天上的視角,對於紅塵滾滾中人類的貪婪和無知充滿憂患和悲憫,兩位楊老師已看出老祖祖的符號是救贖,人類究竟往何去?等等------
總之,我做了自己喜歡的事情,並從中享受快樂和滿足,至於後果如何,那不是作家的事了。現在的年輕人比起我們時代同齡人聰明得多,要相信和尊重他們的才智和選擇,因而,無論當下純文學是如何地舉步艱辛,我依然會癡癡地擁抱它……


楊匡漢
楊匡漢:談《天外》的啟示
楊匡漢(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博導):

作為讀者,《天外》這部書到我手裏是用了十天時間讀完的,寫林湄寫作則用了十年。我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中間沒有間斷。首先感謝林湄十年辛苦不尋常,在我們北京的寒冬(荷蘭也是寒冬),《天外》給我們送來了溫暖;同時感謝新世界出版社,不計成本,不計市場,首先考慮社會效益,在北京連綿不斷的霧霾中給我們帶來了清新的風。這部《天外》比《天望》又前進了一步,從“天外”俯視蒼生悲歡、世態炎涼,很有思考,很有生活的寬闊度,很有情感的濃度,又有靈魂的高度。我想,《天外》可以給我們三點啟示。
第一點啟示是,《天外》使我們思考中國的文學,應該有一個世界性的角度,中國現當代文學連同海外的華文文學,我覺得應該放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來看問題。我們過去習慣的一些觀點和提法要不要做一些調整和修正?例如,我們講“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這個提法現在看起來是有問題的。實際上中國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都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又例如,説我們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都是“從五四以後才起來的”,這個説法也不科學,不準確。剛才林湄提到歌德,歌德在1827年和艾克曼談話當中首先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後來1848年《共産黨宣言》裏面也提出“世界文學”。歌德為什麼提出這個概念,是看了中國的傳統小説以後啟發了他。歌德考慮問題是有世界的眼光。這樣看的話,我們中國的近現代文學,首先會看到海外華文文學。這個海外華文文學,經歷了幾波。鴉片戰爭後國門打開,一方面我們受辱,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反思,派出留學生、外交使官。陳季同等等都留下了很多的作品。陳氏留法,他寫了長篇小説《黃衫客傳奇》,非常棒。羅曼·羅蘭日記裏面都提到陳季同,中文法文很流利。還有黃遵憲。胡適的前面是梁啟超,梁啟超又對黃的“詩界革命”崇拜得五體投地。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文學要重新溯源。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又有一批人出去了,胡適、魯迅、郭沫若等等。20年代末到49年,像老舍、朱自清、錢鐘書、巴金、傅雷、艾青、季羨林等等,他們出去回來是大師。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陸出去的到蘇聯,到東歐去,多數是學工程技術;但從臺港出去是主動放逐,去了歐美,成就了一批像白先勇、於梨華等等文學家。七八十年代以後,又一波留學、移民風潮。林湄是89年到歐洲去的。這一批人,情況很複雜。其中從大陸走出去至今大約200多萬人,大部分去了歐美,而且文學成就大的也出現在歐美。這批人當中,有一些人出去以後寫東西,不斷地遊走,家園來去;也有一些人長期甘於寂寞,躲進小屋,管它冬夏與春秋,寫自己的生存體驗,心靈的體驗,林湄就屬於這一類。現今文學可能是被邊緣化了,世界範圍內都是這樣。但紮根邊緣、立在邊緣,同樣是可以寫出好東西的。純文學是寂寞的世界,不是熱熱鬧鬧的,不應當被資本、被媒體所裹挾的。這一切,我覺得《天外》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示,即應該放在世界文學當中看這一批海外華文作家。儘管他(她)們的作品有長有短,但是對中國的文學發展是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是對中國文化進行反哺的。所以首先值得我們尊重。
第二點啟示,是《天外》的特色。《天外》的特色,我想大致有這麼五點。
其一,把傳統和現代聯繫起來。這裡面有普世的對立面,非惡非善,示惡示善的人。《天外》實際上體現了浮士德式的追求,為傳統的文化符號作出表證,用各種方式穿插在當中,和作品的主人公進行對話,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展開了非常豐富的、多變的、複雜的生活,把傳統的、現代的聯繫起來。其中幾首詩穿插進來也蠻有意思,很有味道。
其二,歐陸和亞陸互聯。這一互聯,就能觀察到、探索到人類有哪些問題。我們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作家,假如眼睛盯著別人的缺點,這就沒有境界了;但假如這個作家能盯著全人類的缺點,就是有境界的作家,有水準的作家。林湄在《天外》這部作品裏,通過歐亞的互聯、比較,讓我們看到人類的問題,共同性的缺陷,這樣的作品是有思想的。
其三,不同文化觀點、不同文化氣質的交集與融匯。傻氣、闊氣、福氣、火氣、人氣等等的氣的交替,很多觀念上有分歧,兩性關係上也有歧見,但是對功利主義都進行了嚴厲抨擊,對於死亡和命運關係也可以達到共識,這種可能性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小説還有一個長處,即對於不同的民族之間的求同問題,對多元文化的不對抗的原則,體現了一種價值取向。有的人物讓人聯想到上海的小癟三,但這類人也不是絕對的壞。林湄有悲憫情懷,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採取的是不對抗的原則。人沒有完人,凡事沒有完美無缺的,小説正是給不同文化語境中的人,提供一個自我救贖的可能性。
其四,深細的兩性交流和人性的探索。這個不多講了,像第11節夫妻面臨離婚這樣一個問題怎麼辦,寫的非常好,有很精彩的心理描寫。
其五,從肉體到靈魂的拷問。歌德的詩劇《浮士德》説,在我心中有兩個靈魂。歌德本身是既偉大又渺小的。歌德是一個傑出的、天才的詩人和劇作家,但他又是渺小的,有的時候難免平庸。林湄在《天外》這部作品當中,對不少問題,既有形而上的思考,又有形而下的觀察,對各色人等,從形上到形下,都有觀察,都有叩問,都有思考。總之《天外》有這麼五點特色值得我們重視。
第三個啟示是小説的結構。剛才王紅旗教授講到網狀結構,我想現在的新小説,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結構,不像過去那種單一的線性推進。小説結構更多樣化了,有非形小説,兩道線互相不搭接,各又支流;有蛇形小説,搖頭擺尾的彎彎曲曲;有蟬聯形小説,有套形小説,還有單線的分岔小説等等,那麼《天外》呢?我的看法是像一把雨傘,傘形小説,花團錦簇地鋪展,但它最終集于一個思想的主線。這條主線體現在552頁,最後是一個生命面對宇宙,面對老祖的生命浩嘆!那麼美好,那麼甜蜜,那麼神秘。所以522頁這一段是這部傘形小説在同一個時空下鋪展後的集聚。以上三點,是我作為一個作者受到的啟發。

肖復興 楊恒達
肖復興、楊恒達談《天外》
肖復興(《人民文學》雜誌前副主編 著名作家):

首先祝賀林湄的小説出版。夏天的時候林湄給我發郵件還為出版小説的擔憂,這部小説,她付出了十年的心血。不是每個作家都熬得住十年,可以感受到她付出的辛苦,理解她的擔憂,出版社能夠接受這個小説,對林湄和出版社還是充滿著敬意,我想從讀者和作者雙重的角度談談,現在小説我讀的很少了,我原來是一個職業的讀者,現在好不容易不看小説了,現在只挑有難度的小説看,去年和今年這一年當中,我覺得對我來講一個是林湄的小説,一個是加拿大的一個女作家門羅的小説。門羅的小説很瑣碎,她小説的障礙是在於她敘事策略的變化,她讓日常瑣碎的生活變成她獨特的敘事方式,小説看到尾的時候,重新再看一遍的時候才能體會到她的味道,她的小説不是從門進來帶到每一個房間,而是從中間看所有的風景。林湄小説是我遇到的第二個有難度的小説,她打破了傳統小説的寫的方法,完全是開放式的,將多種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調製而成。她的小説難度不在於敘事策略,而是敘事的整個精神思想,融入到小説的過程當中去,如果我們不能接受她的思想,或者我們對她表述思想精神上的東西表示懷疑或者本身我們不喜歡這個,對她的小説閱讀難度更大,有這種障礙和難度,説明瞭我和林湄的差距,對精神上的需求,對精神深度的拷問,靈魂上自我的這種責難自己,我跟她確實相差很遠,所以閱讀才有障礙。無論是這種敘事策略的變化還是敘事精神的變化,都會給我們小説閱讀和小説創作帶來新的東西,而這些新的東西是值得探索的,值得肯定的,相比較而言,我們大陸的這種文學評論是非常勢利的,沒有獨立的評論,錢在左右一切。對海外華人的作家,我們對他們的分析,對他們的評價是欠缺的。重新看待他們的小説,特別重要看他們勾勒出了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是非常難得的。拿白先勇為例,他把一代人跟國民黨政府,跟世界之間的碰撞和交流,能夠寫的這樣帶有歷史性,帶有精神性,成為一個斷代史。現在我們的小説非常豐富,非常眼花繚亂,而且對海外作家這些小説家,他們真正的位置,真正的價值,我們關心確實很少,我們評論的也不到位,我們關注還是那些跟影視比較密切的,耳熟能詳的極少的海外作家,而認認真真十年寫小説的作家我們得他們的評價是很少的,在世界文學格局之下,世界文學當中海外華人作家格局之上跟大陸之間的對比和關聯來評價他們的作品,我覺得確實很少,這是我講的第一個感受。
第二個感受我覺得從《天望》到《天外》林湄有什麼變化,她為什麼跟天較勁?按理説文學跟人較勁,為什麼林湄她從天,不是説把人拋棄了,她是從天這個角度來看人,她是從天這個角度來跟人之間的一個碰撞,這種寫作在我們當前來講確實新潮,我覺得《天望》是天人之間的關係,《天外》更多是從天外看人生的視角是俯視眾生,充滿著宗教悲憫的情懷,整體來講沒有蔓延開來,離開她自己創作的整個中心。無論是《天望》還是《天外》,這種對世界對自己的叩問,這對於林湄來講是她的一個寫作的魂,缺了這個就沒有《天望》和《天外》。《天望》是世界的視角來寫的,跟大陸作家不一樣,大陸作家更多願意是風花雪月式的,男歡女愛的,是一地雞毛的,是人和人之間或者是人和時代和歷史和環境的天長地久的爭鬥,缺少人天之間的碰撞。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粉碎四人幫的時候剛開始寫作實際上是對那個時代,不公正的時代,動蕩的時代,文化摧殘時代的一種反彈,更多是對當時歷史的碰撞,而不是對天和人的,我們精神支點不是那麼明確,所以在《天外》這個小説當中,林湄是借助了中國古代和西洋的多種文化,多種哲學美學以及宗教的多種的元素融入了小説當中,其中最重要就是浮士德,就是歌德,浮士德跟郝新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跟林湄也有撕扯不斷的關係,他作為一個精神的形象存在,這在德國的歷史上在鄭國歐洲歷史上都是非常顯現的。我今年夏天到美國去,一個德國人開的老餐館裏吃飯,餐館裏其他東西我不太熟悉,但其中有一個壁爐上的木雕就是浮士德給我印象很深,它是作為一種文學形象,存在於民間。我們的文學形像是什麼,孫悟空,賈寶玉,林黛玉?但是沒有一個像浮士德那樣強烈,浮士德那樣的更民間化,這一點來講浮士德的形像是《天外》小説裏支撐的重要一點,是天的化身的一種。這種從天外俯視人生,對生活中遇到的種種的瑣碎的困難也好,人是如何生存,如何走向未來,能不能跟世界相和諧,能不能找出一條人生存的價值,這是她寫作的很重要一個方面。
所以,我覺得林湄小説的價值恐怕也在於這個,剛才大家分析她是網路式的寫作方法和傘狀的寫作方法,我覺得都是很好的概括。在我看來,跨學科式的寫作在她寫特別明顯。當年王蒙提出來的作家學者化,後來有人諷刺,有人贊同,學者化的作家對文學有沒有幫助,一直有爭論。多元化的文化交流相融,需要做爹學問才行。作者不是學者,但是學問做的深這裡頭不光是浮士德的文化,也有中國的傳統文化,在這個小説當中跟這個人物糾結在一起,無論中國的文化還是對於寫作是有幫助的,這一點,林湄的小説就是明證。
當然,她所做的那些學問,我們能不能接受,西方文化能不能救贖郝新這一代人,救贖他們的心靈,我對這個問題,説老實話有點糊塗。浮士德能夠救贖完全沉淪的一代人嗎?我們是一直把敘事的帶有情節性的文體叫小説,小説就是給老百姓看的,國外這個是咱們翻譯成小説的,國外人家這個詞也不叫小説,小説裏是我們給他的定義,我覺得林湄這部小説,她是努力想把小説寫成大説,這就是她寫作的價值,我覺得應該給予充分肯定,所以在林湄的小説當中,她其實我看她的小説裏頭包括《天望》在內,她不注重故事的情節,這裡面幾個人物互相碰撞,這裡面沒有新鮮的地方,但是她有意打破了這些,注重這些生活化的東西和精神上的東西碰撞,所以她的小説當中這個情節不張揚,情節是淡化的,重視的還是她的精神上,把她思考的這些東西統統融入小説,而且希望跟這個人物結合在一起,這是她寫作的根本東西,所以我覺得如果説從今天寫作來講,林湄小説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也就在這兒,她跟我們今天傳統寫作方法跟我們流行的寫作方法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很多小説有一些確實不錯,但是有一些確實太差了,為什麼呢,我覺得我們很多文學是被權勢,被影視,被資本三架馬車所綁架,林湄她遠離大陸,她也不靠這個生活,也不靠這個揚名,所以她的小説是沉靜的,小説裏面都是她自己的想法,在現在這個文學背景下,林湄能力堅持自己寫作的方式,我覺得是難能可貴的,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和評價的。
當然我對這個小説説心裏話,我讀《天望》的時候讀這個小説我仍然有我的意見。小説還是要照顧更多的廣泛的觀眾,在思想精神和小説的情節和人物的性格如何融為一體,希望林湄給予重視,讓它更好融合在一起,而不是貨賣兩張皮,應該合為一體,成為一個有機的肌體,這是她小説創作當中更需要得到解決的。如果她重視這一點的話,小説會更好看一些,大家閱讀起來更容易接受,更有利於小説的廣泛傳播。我很期待林湄的下一步小説,她的小説雖然給我帶來了閱讀的困難,也給我帶來了閱讀的快樂,閱讀當中有難度的閱讀,才會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感受,在此非常感謝林湄,謝謝。
楊恒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

我很同意楊匡漢教授的感受,在這個基礎上我談點我自己在讀了這部小説以後的內心想法。因為時間很緊張,我的感受目前還有限,我還可以繼續挖掘。
首先我贊成剛才楊先生説的中國文學走出去,這個確實是,在我們文學界有人説我們要中國學派,中國要發出聲音。你走出去,不能以井底之蛙的觀點走出去,井底之蛙和井外之蛙到底有沒有共同的東西?在走出去的時候,把中國的土生土長的東西介紹出去,這些東西是不是和世界各國的文學、各國的人性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或者我們強調中國文學有別於其他文學或者中國人性有別於其他人性,中國文化有別於其他文化?如果是後者,實際上是把中國文學、中國文化、中國人同世界隔離開來,自己孤立是走不出去的。林湄的作品是站在世界的高度,她看到了東西方文學,世界各國人之間的共同的東西,也看到他們共同的精神追求,也看到他們存在的共同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
因此,她寫出來的東西就非常豐富,我看了之後首先第一個感覺就是她這一部作品的豐富性,有著豐厚的文化的思想。無論是中國文化儒釋道,中國文學從古代文學(從《詩經》到《紅樓夢》)到現當代文學,這些都有涉及;世界文學她講的是浮士德精神,但是實際上他這裡麵包含外國文學的內容,從古希臘一直到現當代,這裡面的豐富性是一般作家很難企及的。只有林湄這樣的有著豐富的生活經歷,有著豐富的閱讀經歷,也有自己豐富的思考和反思,這樣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來,所以我覺得這部作品長于它的豐富性,文化上的豐富,思想上的豐富。
進一步,從她這裡面所涉及到的人物來講。郝忻是一個非常平常的人,但是他崇拜浮士德,追求浮士德的精神,使他由平庸變得有非凡追求,浮士德這種精神所面對的還是一些至少不是像我們20世紀以後人的平庸化。浮士德所面對的誘惑,其實要更加強烈,有王公貴族,有財富,甚至有驚艷的美色。
現在社會發展,特別是當代社會,人的平庸化是一個總的傾向,浮士德精神是否符合當代社會,特別當代社會有各種各樣的歌德當時沒有預見到的東西,這些東西需要靠什麼來面對?浮士德身上所積累起來的那種人文的精神,是否可以在當代社會中繼續發揮作用?林湄用郝忻這個人物做出了回答。郝忻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誘惑,他有各種各樣的缺點和毛病,也面對著各種各樣的矛盾。這些問題,幾乎是每一個現代社會的人都會面對的,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不需要鬥爭,需不需要精神上的追求?這個也在作品中做出了回答。
當然,人的缺點是無法避免的,人因為相對世界來講是那麼渺小,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窮盡,人的局限性、人的眼光的局限性、人所處地位的局限是無法避免的,這也就預示著郝忻遇到的這些問題還會繼續遇到。以前很多文學作品到了大結局就皆大歡喜,實際上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出現。林湄這部小説結構上是開放的,郝忻還會遇到什麼問題,會變成怎麼樣,這留給讀者考慮。但是如果不去弘揚這種浮士德精神,完成精神上的追求,對靈魂的追求,他走向墮落是必然的。所以在這裡又從另外一方面突出了浮士德精神的一種普視性,人類共有的價值。

張志忠
張志忠:《天外》是大陸文學傳統的傳承
張志忠(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天外》閱讀起來確實是一個重活,一個是篇幅,一個是內在的思路。篇幅是一個方面,60萬字,現在大陸作家寫這麼長的小説不太多,因為他有各種考慮,而且用十年寫這麼一本書,大陸能寫作的十年恐怕會寫出五本書來。再一個是它的問題意識,關於人的存在的思考,看著從一個很小的切點進入,就從郝忻的人生的轉捩點開始。他的思想背景很開闊,從浮士德到紅樓夢,從弗洛伊德到中國的孔子孟子老子,甚至還有很多關於自然科學方面最新的成果和問題。比如説我看到作品中某一個人為他自己辯論,世界上許多精英,包括拿坡侖,都是小矮個,這讓也是小矮個的我很高興,突然書中又看到一個最新統計,世界五百強領袖,他們身高平均身高都高於常人;我們再統計一下做人文研究或者文化創新的人是什麼情況,我想我希望再有一個統計數據。這也是戲言了。這説明她材料的豐富,思想非常開闊。
我覺得《天外》這樣的小説,一方面現在大陸作家很少寫或者寫不出,但它畢竟還是我們大陸文學的一種傳承和繼續,我覺得這樣的小説大約就像我們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謂歷史新時期伊始,一個時代的轉折給大家帶來很多希望也給大家帶來很多思考,七八十年代之交,有一批在哲學的層面上,在思想的高度上思考的文學,那個年代比如説像《公開的情書》,《人啊!人》,我覺得《天外》這樣的小説是有它內在的文脈勾連的。中國的作家在80年代充滿了理想氣息,所以能夠寫出《紅高粱》;但是到今天,經歷市場經濟的時代,也經歷了慾望膨脹,人欲橫流,我們大陸作家不會寫出《天外》這樣純粹的形而上的作品。《天外》寫郝忻這樣一個中年知識分子,中年的思想者,他的心靈和肉體,他經歷的震撼性遠遠沒有我們大陸同類作品有那麼強烈的戲劇性,那麼強烈的場面和慾望。我覺得這就是講,可能海外的作家,尤其是大陸出去的海外作家,我覺得很多人是帶著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新時期的文學精神,沒有經歷過90年代的動蕩,不是社會動蕩,而是心靈的動蕩。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郝新這樣的“文呆呆”和我自己也有點像,就是那種對現實和人際關係比較淡漠,沉浸于自己的內心世界的書獃子,但我自己受到的人生的困惑遠遠比郝新經歷的要激烈得多,內心的衝突各方面都要強烈。相對來講,在80年代離開大陸,或者像林湄這樣的,我看她先是到香港,後來又到歐洲去,她離開大陸更早一點,從思想文脈上來講是我們新時期文學初期那樣一種探索精神的一種延續,而且到今天來看,他們沒有經歷過大陸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經濟的大的轉折,沒有切身在這個場合裏面,經受心靈的震撼,相對而言他們的思想狀況或者人物命運的表現,確實還是説比較單純,理想氣息,比我們大陸作家要強烈。
還有中國作家寫歐洲,這也是經過文化震驚之後的沉思。當年趙淑俠從台灣到歐洲去,移居之初有兩種文化的磨合,兩種文化的衝撞,兩種文化差異帶來的兩種文化的震驚,趙淑俠對歐洲是沒有什麼好的評價的,我讀過她一篇短篇小説,她到了歐洲,在德國,她也到了荷蘭和周邊歐洲各個國家去度假,她會帶著很強的本土意識,對於歐洲的這種人際關係,她會有很多的不習慣,或者有很多的差評。那麼到《天外》來看,作者是1989年移居到歐洲,那麼也是20年或者25年期間的這種長期的體悟。從我們大陸的有關新聞媒介來講,我們經常會看到,經常在講美國政府如何佈置或者策劃要遏制中國的崛起,我自己到美國去待過不到一年,越過傳媒的政治宣傳親身體驗,當時就是感受所謂文化的震驚,深有體會;但是我太太他們很多同學也是八九十年代到美國去,他們都是學醫的,他們的生存狀況今非昔比,他們經過了文化最初的震驚,他們講起什麼事情似乎都有一個新的角度。《天外》也看到文化震驚期過後有一個比較平衡,比較坦蕩地面對另一種文化,另一種社會形態,另一種文化和社會傳統下面的人際關係。這是《天外》兩個大的文化背景,一個是説大陸新時期初期的理想信念,但是又有單純而執著的追問,再一個是文化震驚期過後對於歐洲的描寫。
這個作品我也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概括,概括了三句話。
任何一部作品讓評論家一説就沒有趣味了。但是,如果不能把問題抽象出來我們也不能把60萬字從頭到尾復述一遍。第一句話是:生活是一團麻。人到中年,郝新這樣的夫妻走過最艱難的時期,突然生活出現了轉機,還有一條,人的生命到一個檻上,有一些問題恐怕像小周這樣的年輕人沒有經歷不會意識到,我看到郝新我很親切,人的生命,人到了中年一定要明確你到底要做什麼,我記得當年大概是1992年,1993年寫一個什麼東西,我覺得到了不惑之年我充滿了困惑,如何面對90年代初中國的社會現實。郝新有他自己的特定的環境,也有他家庭的狀況,但是他確實遇到了一個説個人生命也好,思想也好,人生目標也好,向何處去。所以就産生了第二個問題,你到底要什麼。而且郝新確實是文呆呆的,他做什麼事情其實不是太難,對於很多人都不難,但是他一定要找到一個參照係,沒有經過思考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沒有意義的生活,他一定要去思考。你説他想在生活上,在個人的情感和慾望方面有所放縱,你説越軌也好,你説冒險也好,很多人説這樣的事情根本不用想,做就是了。他一定要想浮士德怎麼講,浮士德提供什麼樣的啟示,那麼反覆地追問自己,你到底要什麼。生活是一團麻,這是當年電視劇裏的一句歌詞,你到底要什麼,這是蘇聯作家柯切托夫一篇長篇小説的書名,來責問當時蘇聯的青年人你到底要什麼。
我覺得你到底要什麼,或者講浮士德的啟示對於郝新來講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在作品裏面,我覺得可能限于郝新他的人生,難以大起大落波瀾疊起。這個衝突放在大陸不得了,90年代到現在,像我們這樣的年齡,如果想在官場上發展,可能今天就是周永康,徐才厚,當然也有可能是李克強,如果想在商場上有所發展,那就是今天的馬雲,王健林這都有可能,這樣的話他會像浮士德的經歷,要有非常大的波動,大的衝突,大的選擇;郝新進入的是一個非常日常化常態化的社會,他的選擇,他的機遇還是少了一些。對於浮士德,歌德賦予他的非凡的命運,經歷過財富,娶過美女,各種各樣的誘惑,人生各種滋味都要品嘗。相對來講,郝新要承擔浮士德的追問,客觀上,主觀上都受到局限。作品裏面有一些地方我很喜歡,但是也許不一定是切合林湄老師的設想,我就覺得講了半天,需要什麼樣的理想呢,躺在海邊沙灘上曬太陽看風景,作品裏面有好幾處寫海濱,寫看風景的人。我們既然做不了浮士德,在不愁溫飽的情況下躺在沙灘上看看風景,看看海邊的男男女女,我們可能眼睛發亮,但是也僅此而已,我覺得這是我讀《天外》時的歪解。當然這個作品最後的結局,我有一點困惑,就是講郝新經歷了那麼多,外表看著很平常,但是內心很激烈的矛盾衝突,那麼到作品結尾的地方還有兩個結局的糾纏。第一個講那一位叫卜馥淑,願意給他提供一種選擇,我有經濟實力,可以給你提供相當的條件來可以實現你的寫作夢,思想夢,但是另一個是他自己的妻子,她也覺得經過各自的這種人生曲折冒險之後,兩個人重歸於好,建設曾經的家庭和婚姻。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講起來這應該也是給他提供新的選擇,新的矛盾,作品寫到這裡突然打住了,我覺得當然也可能講是留有餘味,但是相應的提示,相應的這種郝新的新困惑,在這裡表現的沒有給讀者提供想像的線索或者思考的線索,似乎閱讀感受是這樣。也許這麼一部作品作家寫了十年,我們閱讀連十天的時間也沒有,讀的時候沒有體會出作家的苦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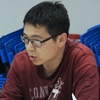
周顯波
周顯波:閱讀《天外》的收穫
周顯波(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學院博士):我的發言簡單概括一下,就是兩個“一”、兩個“二”。
首先,第一個“一”是指一個驚訝。《天外》如此大部頭的作品,60萬字,積十年之功完成,非常可貴,它一方面顯示了在今天浮躁的商業環境之中文學的自律與文學的力量,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作家的努力、毅力和堅持。
第二個“一”是指一種寫作狀態。林湄老師這樣的海外寫作,我將之定義為另一種意義上的孤島寫作。前面肖復興老師講到了,林湄是沉靜在世界一角在安靜地寫作。今天是純文學邊緣的時代,在這樣形勢下從事大部頭的寫作,沉靜在世界的一角安靜地寫作的行動,可謂淹沒在商業海洋之中的一隻孤島。另外林湄身處海外,而且書寫所用的語言是中文,在這樣一個海外背景之下進行寫作,也同樣是邊緣的,孤島式的。所以説林湄在精神狀態和文學寫作狀態上都是孤島寫作。這種孤島寫作給作家帶來挑戰,如何應對這個挑戰就可能為一種別樣的文學意義的生發提供了契機,也因為這種孤島的狀態讓林湄平心靜氣抒寫這樣一個厚重的故事。可以説,《天外》是深陷孤島的作者,寫于孤島時期,並嘗試突圍孤島狀態的一部有關孤島精神生活的小説。
以上是兩個“一”,下面我來講兩個“二”。
第一個“二”,是指作品背靠的兩個文學傳統。其中一個是西方文學傳統,小説裏有大量對西方文學的互文式書寫,特別是對於《浮士德》的引用。這一點前面幾位老師談的非常充分了,在這裡我不再多談。《浮士德》對小説的影響是明顯的,外在的。我們在這裡還應該留意另外一個文學傳統。剛才張志忠老師談的是作者與1980年代啟蒙文學思潮的聯繫,我則想擴而廣之,從一個更大背景來談。《天外》除了與《浮士德》互文式書寫之外,其實受《紅樓夢》影響頗大,這不僅體現在小説裏多處引用、借用、改用《紅樓夢》語言和典故,還體現在小説對人物氣質塑造方面與《紅樓夢》的某種類比性,比如主人公郝忻有賈寶玉那種呆,比如吳一唸有王熙鳳的幹練與務實等等。還有,整部作品的結構架構,以及對於精神的追索也有《紅樓夢》的氣質,例如真與幻的追求等等。
第二個“二”是指小説的兩個關鍵詞。小説的第一個關健詞是移民。《天外》以很大篇幅書寫了移民的生活狀態。《天外》不是採用旅遊文學的寫法,不是用一種外在的、旅遊者的視點,以一種旅遊者的身份來關注周圍。另外小説也不是用一種返鄉式的寫法,也就是説不是用那種外部世界遊歷之後重新回歸本土,然後重新發現和闡釋本土的書寫方式。林湄老師的寫法是用一種從容的、自在的心態來看待已成事實的移民生活。這是真正在海外生活很多年並紮根在海外的人才有的一種心態、一種狀態,由此才生發出一種自在的眼光。所以林湄面對海外世界不是用奇異的眼光、旅遊者的眼光來打量週遭一切,而是用一種自在、從容的心態和眼光來書寫文本。對林湄來説,這種心態意味著周圍一切是我熟悉的,它們就是我的一部分,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是這個生活之中的。所以她以這樣的眼光和心態來觀察這個移民的空間,呈現在作品之中的就不再是旅遊、奇觀化的視角,故事的寫法也不是刻意用本土精神拼接移民故事,而是內在於這個環境之中,也就是移民環境之中,把它當成一部分抒寫。我讀《天外》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林湄筆下雖然書寫的是移民生活,但有關這個移民生活故事是比中國還中國的故事,這大概是我們今天全球語境之下,個體面對的問題是有著某種共通性的——我想這是《天外》容易被我們理解和覺得心有慼慼焉的重要原因。我們注意到《天外》有很鮮明的中國內核。這個以郝忻為主線的故事,放在中國本土一樣能夠容易理解。郝忻一家雖然孤懸海外,但他面對的家庭問題、精神困境一樣也是我們生活裏需要解決的。小説裏寫到,郝忻婚姻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想著是“保住家,一切均好辦”。吳一念對改善生活的那種執著,“一面在‘丈夫’和‘情人’的視角下穿梭,另一方面想方設法賺錢繼續努力實現原先的夢想——住大屋買名車提高生活的水準”等等——這既是世界性的矛盾,也是中國人處理矛盾的方法。我們來讀《天外》這個孤懸于海外的故事,沒有感到陌生和隔膜,原因就在於通過這個文本其實就是重新在打量我們自己,重新在看待我們自己的生活。人物的這種內核精神狀態,包括他的思考方式、精神狀態等非常中國化的。
第二個關鍵詞是思想性。小説裏對於《浮士德》、基督教和佛教的探討都能夠表明小説的思想性追求。舍斯托夫認為,優秀的文學應該有對世界和世界中個人的雙重警覺,《天外》在這兩個方向上均有努力,難能可貴。
這就是我對小説的一些粗淺看法,因為只有一個星期來閱讀和體悟,所以一些的觀點還需要深入辨析和思考。
王紅旗:各位教授的精彩發言,觀點我都非常贊同,而且得到很多啟發。感謝諸位從不同的視角,真誠地為我們打開閱讀《天外》的窗口。我認為,林湄老師從《天望》到《天外》的突破,首先在於《天外》從人類文化的深層矛盾,從東西方家庭的性別倫理與情感秩序問題,考察了個體人性的多層面相與內在本質。以跨族群、跨國界、跨文化與跨性別的“第三時空”,看到了人類現世代的困境,並執著地在尋找救贖之策,希望是存在的。
她的《天望》裏,講述的是一個女兒微雲從中國江南鄉村走向了歐洲,與一個叫弗來德的歐洲混血兒組建一個家庭,東西方文化聯姻的符號是很明顯的。小説從結婚之夜開始寫,以婚姻家庭的倫理關係日常生活衝突,書寫東西方人類的互視,互用,互補的平等對話。更進一層的衝突是,對宗教信仰的理解,按理説信仰宗教是不圖回報的,但是,丈夫狂傲與偏執,就是要為拿“天國大獎”而傳道。是不是在揭示,整個人類宗教信仰的物化,越來越實用主義?一個非常依附丈夫的妻子也只能離開了他獨自去闖世界。後來在她丈夫眼睛瞎了的時候,她回到丈夫身邊,一個愛的擁抱打開了他丈夫的“心眼”。因此,我覺得還有一層意思是女性的愛對人類靈魂的救贖。尤其是小説末尾,面對那“可怕的貪婪的、吞食世界的咆哮著的大火”,高聲地呼喊“救人啊,救人!”幾乎是絕望的望天吶喊。此時林湄老師“救世意識”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
到《天外》的時候,是通過數個新移民家庭的夫妻情感糾葛,東西方聯姻的家庭倫理衝突,在解剖個體人性靈魂經歷磨難之後的新生。郝忻和吳一念夫妻都是改革開放後回復高考的大學畢業生,可以説是出國的新移民,他們之所以出國,是在國內遇到太多不如意,或是出國尋找更大發展空間。但是,沒想到歐洲的生活也是如此物質化,沒想到“翰林院”的經營一直不景氣,就連妻子都天天逼著自己下海經商,他們都被慾望、金錢誘惑迷失,但最終卻走向內心平靜的回歸本我。其他幾個不同形式的“東女西嫁”或“西男東家”的婚姻也是危機重重。她是以一個個家庭在思考人類存在的人性缺限。
剛才楊匡漢老師説,林湄老師思考的是“人類的缺點”,實際上是通過您的女性生活體驗,女性文化經驗,來思考人類缺陷的,是從男女兩性的個體人性思考人類經驗的,是從女性的愛情、婚姻、家庭、以及女性對子女倫理關係,來反思個體人性共同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説,每個家庭各有各的矛盾衝突,但是其困惑焦慮卻是相似的,即對物質慾望的永不滿足。無論是東西方文化的“傻性與奴性”都是不健全的人性,而現世代人有被“物性”所異化變得“精明”。從而揭示出“人類心性”的困惑。這是很發人深省的。更難得的是,小説在敘事過程中流露出人性“善與愛”的溫暖無處不在。尤其是小説結尾,作者把郝忻和吳一念夫婦置身於大自然美麗祥和的田園風光之中,預示著人類經歷了靈魂困惑、精神磨難之後,擁入大地母親懷抱而重生的多種可能性。這就是作者在“第三時空”,也就是站在“天外”洞察到滾滾紅塵東流去,靈魂沐浴暖陽“在唱歌”的人類希望。我認為,《天望》與《天外》都是很值得文學史記載的兩部小説。
謝謝各位老師!辛苦了!盼有機會再相聚。
本期資訊
時間:2014年12月9日上午9-12點
主題:荷蘭女作家林湄長篇新作《天外》研討會
地點:中國網貴賓會議室
嘉賓:王紅旗 林湄 楊匡漢 肖復興 楊恒達 張志忠 張奇 周顯波
嘉賓介紹
|
|
精彩片段
活動預告及報名
活動報名:請將姓名+職業+聯繫方式發送至female@china.org.cn,報名成功會有郵件回復
聯繫方式
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中國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王紅旗
助理 周顯波
責任編輯 蔡曉娟 張林
聯繫電話:88828425
電子郵箱:female@china.org.cn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聯合出品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聯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