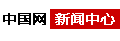林湄談十年磨一劍之新作《天外》
我祖籍福建福清市,出生在絲綢之路的泉州,華僑世家,70年代移居香港,90年代移居歐洲,現在是荷蘭籍,一生經歷了社會主義、殖民地香港及資本主義社會,雖仕途坎坷,命運多舛,但植于我靈魂深處的根本東西還是中國文化。
我從小就喜歡文學,頗有文學天賦,但今天看來不算什麼,主要還是靠勤奮和契而不捨的毅力。在香港中國新聞社工作的時候,除了工作外業餘時間寫散文、短篇小説、長篇小説等,題材大部分跟我個人的經歷與週遭人的命運有關係。
我是到歐洲後才對“文學即人學”的感悟,確信了無論歐洲人還是東方每人平均離不開人的共性和個性,隨著生存環境的變化、歐洲深厚的人文主義思想以及21世紀資訊科技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促使我想起歌德1827年1月對愛克曼論及的“總體文學”,即對“世界文學”的再思。
“世界文學”不分民族、身份和國界,觸及的題材也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即人的徬徨,迷茫,生存處境以及對財色生死問題的探索,居住地球村裏的人,任何榮辱福禍均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何況還有諸多形而上的問題困擾著人類——人活在世上到底是為了什麼?每天忙忙碌碌又為了什麼,精神和物質、靈與體、有限與無限等等問題引發我思考的興趣。
1995年6月,在荷蘭召開了我個人的作品研討會,有50多位學者專家參會,80多歲的《紅樓夢》法語翻譯家李治華説“林湄的小説題材多是關注社會的重要問題”,比利時漢學家魏查理院士表示“林湄的小説兩種文化背景的每人平均能接受”,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當代文學教授戴翊上交萬多字評論“女性的命運與輝煌”,等等論文,以及會後有20多家的傳媒報道,但我覺得文學藝術是無窮無盡的,與世界經典文學作品還差得遠,決意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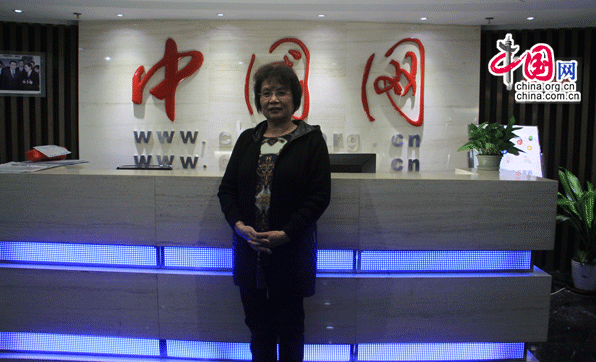
此後,我拒絕一切誘惑,甘於清寂、淡泊名利,沒有辦法去改變社會現實,只好將思考融入我愛好的文學創作裏,用十年時間完成50萬字的長篇小説《天望》,男主角是有救贖思想的人,他以簡單對付世界的複雜,世人覺得他傻,他卻覺得世人傻,認為眾人活得又累又愚昧,個個均在追求財色和物質東西-------
《天望》寫完了,出版後獲中外專家好評,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生活在繼續,社會在改變,科技在發展,生命短暫,文學卻沒有完結------更重要的是,其間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也影響了海外華人。華人帶著完美主義的理想,從東方到西方,不料西方漸漸沒落,東方卻在崛起,漂泊者自然對離散、移居、身份等詞語有著更多的解讀和理解,我不由想起《聖經》裏的一句話意,一生勞苦愁煩卻只得一口飯吃。
可見,現代高科技與經濟發展並沒有帶給人類真正的快樂和幸福,相反,其帶來的付作用卻隱約地影響了人類的精神生活與靈魂力度,使其潛移默化的異化,或怪誕、或萎縮、或不知所措-----
藉著對社會人生的憂患和擁有的創作激情,我再次用十年時間完成了《天望》的姐妹篇《天外》。
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思想相當複雜,思考多於書寫,每一章,每一個人物均寄託了對社會、人性、生存、高科技發展的沉思,於是,以第三空間的視角敘寫眾生相,集平凡人的生活、際遇和命運表達人生的勞苦與愁煩及無奈焦慮的存在。書裏的人物均是現實生活中群體的代表,如一個慾望的結束就是世人另一慾望的開始,永遠不會滿足,中國人如是,西方人也是如是。
物欲的充塞,使人的靈魂都丟失了,作為作家就有了負擔,只是無法改變現實,幸好依然熱愛文學,加之在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天真無知,常常做蠢事,因而,寫作是我承受命運的最佳狀況,也是我祈禱似的生存方式。
有人説,你的小説不入流,難讀,難懂,與中國傳統小説藝術形式和表達方式有距離,給閱讀和審美習慣帶來難度與費解。確實,近20多年來,我的創作理念和藝術追求不盡與傳統文學觀不同,也與自己1995年之前的創作不一樣了。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我離開祖國已41年,“根”既移植,吸收的養份就有所變化,結出的果子自然也會不同。為什麼要一樣呢?事實證明,即使在同一社會環境下成長、同校同係的畢業生,也會出現不同的求索精神與出路。何況,古今中外,沒有一成不變的藝術觀,也無永遠絕對的“正確”,或出於我智、識的求索,或與我生存環境有關,或因我較具前緣性意識,所以,行走在文學藝術的求知路上,喜歡獨立特行,希望在探索中創作獨具一格的作品,將傳統小説強調故事、 情節、重懸念、衝突、高潮等創作法與西方的慢節奏、細觀察、重視人內在意識和心理變化的特徵相融或摻合,在敘述命運和各人性格裏反映社會人生,讓藝術結構和形式更好地表達人類生命底本質,當然,更希望作品對讀者有所思,有所啟迪,不是看完就完事的感覺。
總之,我做了自己喜歡的事情,並從中享受快樂和滿足,至於後果如何,那不是作家的事了。現在的年輕人比起我們時代同齡人聰明得多,要相信和尊重他們的才智和選擇,因而,無論當下純文學是如何地舉步艱辛,我依然會癡癡地擁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