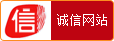回憶中的大運河
原標題:回憶中的大運河

回憶中的大運河,總是會首先想到蘇東坡。作為一個文化人,蘇東坡讓後人永遠懷念。晚年的他從海南流放歸來,在蜀地的一個叫玉局觀的道觀挂職。蘇東坡沒去寺廟裏就職,他一路向南,再向東,朝著江蘇的方向直奔而來。我對他來江蘇的具體路線,已記不清楚,當年曾經為此很認真地做過一番研究。現在只記得到了江蘇境內,沿著大運河,最後進入常州。正是天氣最悶熱之際,船艙裏更熱,熱得只能光膀子,裸著上半身,也就是我們南京人説的赤大膊。
常州人民聽説蘇東坡來了,立刻萬人空巷,都來到運河邊上,一方面歡迎他,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想見見偉大的蘇東坡風采。於是大家見到了裸著上半身的東坡先生,他老人家袒胸露腹,從船艙裏走了出來,向常州人民拱手致意,同時嘴裏忍不住念叨: “這樣歡迎,折煞人也!”
我喜歡這樣的一個熱情場面,總是無法忘了大運河邊的這一幕。天氣那麼濕熱,揮汗如雨,常州人民中一定也有許多光著膀子的男人,他們站在運河邊上看風景,對著詩人指指點點。而今天的我們,卻是穿越了一千多的時光,欣賞著風景中的他們。當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到了常州,想到蘇東坡,崇敬之情頓起,寫詩紀念,在運河邊艤舟亭附近,他老人家居然一連寫了三首詩,其中之一是這麼寫的:風流蘇髯仙,遙年此係艇。遺跡至今傳,以人不以境。
乾隆皇帝的這首詩,強調了以人為本,在他眼裏,大運河也就這樣,重要的應該是人,是蘇東坡本尊。中國古代的京杭大運河,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千百年來,南來北往,無數遊客匆匆走過,習以為常,習慣成自然。沒人太把大運河當回事,大運河就是今天的高速公路,就是今天的高鐵,因為有了高速公路,有了高鐵,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得更加方便,對於古人來説,大運河也談不上多偉大,它就那樣。
我們今天很喜歡説大運河的文化含量,文化也是慢慢才形成的,有時候,文化也就那麼回事,人文化成,文化這玩意要是離開了人,什麼都不是。
江蘇境內的大運河,最早只是與戰爭有關,為了去征伐別人,為了稱霸,為了開疆拓土。有一種流行説法,就是大運河的第一鍬,是春秋時期的吳王夫差開挖。當年的江南,水網四通八達,吳國軍隊要想遠征,要想逐鹿中原,就要考慮如何將長江與淮河溝通。在古代,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辦到的事情,只能更多地利用自然河道,多繞點路,多繞很多路。因此,最初的河道,東自太湖出發,沿胥溪西上,直到今天的蕪湖附近,才能進入長江,再渡過長江往北,沿柵水到巢湖一帶,然後北入淮水。再以後,為了走近路,便有了人工開挖的邗溝,路程大大地縮短,南北距離被拉近了。
古邗溝是江蘇境內大運河中非常重要的一段,雖然最初目的,只是為了軍事,為了定鼎中原,實際效果則是極大地方便了老百姓,方便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出行。事實上,人工開挖大運河,自吳王夫差的第一鍬開始,從來就沒真正停止。秦朝和漢朝,以及後來的南北朝,大運河一直在斷斷續續挖掘,越挖越遠,越挖越長。因此,隋煬帝在古邗溝的基礎上,花了六年時間,完成的京杭大運河,也只是充分利用了前人成果。
因為吳王夫差,因為隋煬帝,因為這兩個既富傳奇,又是悲劇性的人物,江南的命運就此改變。不管怎麼説,大家都會明白,大運河的功要遠遠大於過。而大運河的歷史功過,也用不著我來過多評價。唐朝詩人皮日休甚至把隋煬帝修大運河,與大禹治水相提並論。過去的很多年,大運河都是中國的經濟命脈,皇家政權要想維護自己統治,必須要依靠大運河,必須要管理大運河。
事實上,大運河帶給我們的聯想,更多的還應該是蕓蕓眾生的普通人。真正要回憶大運河,我會更多地聯想到古代遊子,想到當年的南船北馬,想到南來或北往的文人。大運河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它不是始終暢通。我們都知道,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到了明清之際,北方的大運河,漸漸地已失去了通航能力。
遙想當年,北方人南下,到今天江蘇的淮安境內,必須下馬坐船,從此開始一段行舟的詩意生活 。南船北馬是古代南北交通,最常見的出行方式,很顯然,長途旅行中,與顛簸的馬車相比,船上的感覺可能會舒適一些,磨墨題詩也方便得多。
有了高鐵,從南京去上海,只要一個多小時。可是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滬寧鐵路還沒開通,清華四大教授之一的趙元任先生,從家鄉常州去上海,必須先坐船繞道南京,再坐江輪赴滬,要走一個三角形,要花一週時間。
自從有了火車,一個舊時代結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時間開始有了全新的意義,不過仍然還有不同的理解,譬如在民國時期,豐子愷先生從家鄉去省城,乘火車只要四個小時,可是寧可坐船,坐船要四天,他認為這樣可以看到更多的風景。快還是慢,這可以是人生的兩種選擇,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喜歡快,喜歡快捷,然而有時候,我們也可能會希望慢一點,為什麼不能慢一點呢。
我有過兩段大運河上的親歷,一次是從蘇州去杭州,一次是在蘇州古運河上夜遊。第一次的舟行説來非常奇特,那是三十多年前,在大學讀研究生,我們出門訪學,去了蘇州,到范伯群先生家,請他為我們上課,講完課,付了五元錢的講課費。范先生一邊在收據上簽字,一邊説我跟你們先生是好朋友,為他的學生上課,還要這樣真是不好意思。然後,大約也是范先生的主意,勸我們乾脆坐船去杭州,覺得這樣更有詩意。那時候,老作家汪靜之先生與黃源先生還健在,我們計劃中要去拜訪他們。
於是就上了從蘇州去杭州的夜航船,因為年輕,也沒覺得這樣旅行,會有什麼樣的意義,好像是上了船就聊天喝酒,然後就睡覺,進入了黑甜之鄉。醒來時,已經到杭州境內。旭日初升,景色很美,想到船艙外去看看風景,可是剛走出去,便被臭烘烘的氣味熏了回來。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京杭大運河杭州段,被污染得不像樣子,河水黑乎乎的,漂浮著各種雜物,我們當時並沒感到詩意,感到的是詩意的消逝。
第二次在蘇州夜遊古運河,完全是另一種感受,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時間是新世紀,第一次過於簡陋,雖然臥鋪,又臟又亂又差,第二次過於豪華,有空調,有吃有喝,還有人唱崑曲。走出船艙,清風撲面,精神立刻為之一爽。兩岸風景如畫,燈光五顏六色,站在船頭上,與陸文夫先生通了一會手機,向他老人家問好。陸文夫是家父的摯友,那好像也是我最後一次與他聊天。
葉兆言,主要作品有八卷本《葉兆言中篇小説系列》,三卷本《葉兆言短篇小説編年》,長篇小説《一九三七年的愛情》、《花煞》、《別人的愛情》,《沒有玻璃的花房》、《我們的心多麼頑固》,《很久以來》,《刻骨銘心》,散文集《流浪之夜》、《舊影秦淮》、《葉兆言絕妙小品文》、《葉兆言散文》、《雜花生樹》、《陳年舊事》等。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