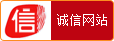一張水做的明信片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大運河
【編者按】中國大運河源於春秋,延續至今,是世界建造時間最早、使用最久、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被國際工業遺産保護委員會在《國際運河古跡名錄》中列為最具影響力的水道。
中國大運河是連通古代中國陸上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交匯點,其強大的航運交通功能帶來的巨大影響力,不僅在中國文化裏留下了印記,還輻射到了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眾多國家。
聊城大學運河研究院副教授胡夢飛認為,唐宋以來,大運河便引起了西方來華使節、旅行家、傳教士、商人的關注,他們沿運河遊歷或考察,在其著作中留下了眾多有關中國大運河的記載和描述。大運河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西方人觀察中國文明的重要窗口。大運河所包含的“開放、交流、繁榮”的概念,與“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不謀而合。
中國網大運河頻道特別刊發胡夢飛《西方人眼中大運河形象的歷史變遷》一文,從西方人的視角出發,與網友分享感觀不同的中國大運河。
推薦閱讀:
西方人眼中大運河形象的歷史變遷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古代運河,也是最古老的運河之一。與長城一樣,作為中華文明的標誌和象徵,唐宋以來,大運河也引起了西方來華使節、旅行家、傳教士、商人的關注。他們沿運河遊歷或考察,在其著作中留下了眾多有關中國大運河的記載和描述。這些著作傳到西方,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重要來源,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也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作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大運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西方人觀察中國文明的重要窗口。
一、元代以前西方人眼中的大運河
元代以前西方人涉及大運河的記載最早出現于晚唐時期西方著名商人蘇萊曼所著的《蘇萊曼東遊記》。《蘇萊曼東遊記》(一譯《中國印度見聞錄》)是中世紀阿拉伯人所著最早關於中國和印度的旅遊記,大致寫成于西元850年左右。該書早于《馬可·波羅遊記》四百多年,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有關中國的遊記。這部書後由法國人萊奴德復譯,並詳加考證,前部即《蘇烈曼遊記》,後部為西拉伕(Siraf)市人阿蒲·賽特·阿爾·哈桑(Abu Zaid Al Hassan)所述。根據學者的考證,蘇烈曼是否到過杭州,甚至見過大運河還不能確定。在《蘇萊曼東遊記》的後半部分記錄了當時一位名叫伊本·瓦哈卜的人曾從廣州北上京都長安。不管是從廣州還是從泉州出發,從海上入境的外國人前往洛陽或長安,基本上都要經過大運河。必經之路是從江南運河鎮江出長江,至瓜洲渡由瓜洲運河至揚州,然後走邗溝、通濟渠(汴渠)經開封、洛陽,轉入黃河,從洛水至洛陽,再由黃河水路至潼關,由渭河(關中漕渠)或陸路至長安。很有可能伊本·瓦哈卜走的也是這條線路,如果真的如此,這應當是西方人在大運河上最早的旅行。
另一項關於運河的重要記錄來自西元9世紀中後葉阿拉伯地理學家依賓庫達特拔(約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記》。依賓庫達特拔在哈裏發麥塔密德在位之時,曾經擔任笈巴爾省之郵務長官。依賓庫達特拔在其著作《省道記》中記載了其從越南佔城出發,到達廣州,經由泉州北上到達康圖(指揚州)的經過。書中寫到:“中國各港皆有一大河,可以航船。河受潮汐影響。康圖有鵝、鴨及他種野禽。由阿爾梅德至中國他端,最長海岸,有兩月航程。中國有三百名都大邑,皆人煙稠密,富厚莫加也。”
阿拉伯人馬蘇第是西元10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從小便開始遊歷各國,在其《黃金草原》一書中也提到了“揚州”。但局限于其當時的遊歷經歷,馬蘇迪竟認為揚州是一個“國家”,於是留下了這樣的記錄:“居住在揚州的該國第一位國王是奈斯泰爾塔斯(Nastartas)。在他在位的300多年期間,他將其居民分散在這些地區,挖掘運河、消滅猛獸、種植樹木和創造了園藝嫁接的習慣。”這也成為了西方人對於運河的重要記錄。
元朝以前西方對大運河的記錄僅見於此零星記錄,一方面,反映出當時西方來華的商旅對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感性的印象層面,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概念,否則也不會將一座都市誤認為是一個國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這一時期西方來華的人主要以外貿的商旅為主,且主要以與中國相近的阿拉伯人為主。與同時期日本、朝鮮來華的人物有著根本的區別,導致兩者留下的記錄存在天差地別。當時日本的圓仁法師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記》、僧人成尋著有《參天臺五台山記》,這些著作均對唐宋時期的大運河留下了非常詳細的記載。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地理距離和航行技術的限製成為阻擋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原因。
二、元代西方人對大運河的認識
蒙古鐵騎通過戰爭打通了東西方的重要路上交通,徹底疏通了西方來華的要道,歐洲人、阿拉伯人開始源源不斷進入中國,他們對京杭大運河開始有了非常準確的認識。這期間最為有名是的馬可波羅、鄂多立克、馬黎諾裏、伊本·白圖泰,他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著述,使得西方人對中國大運河的了解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馬可•波羅遊記》記載了主人公馬可•波羅在中國的一路行程,他曾從北京出發,沿著京杭大運河一路南下,經由山東到達江蘇揚州,還曾在杭州生活多年,甚至擔任官職。《馬可•波羅遊記》裏也記載了他遊歷大運河沿線淮安、寶應、揚州、鎮江、杭州等城市的故事,他寫寶應:“貨幣為紙幣……有絲甚饒,用織金錦絲絹,各類多而且美。”他寫高郵:“生活所需之物皆豐饒。産魚過度,野味中之鳥獸亦夥。”寫泰州:“自海至於此城,制鹽甚多,蓋其地有最良之鹽池也。”寫位於長江內的瓜洲:“此城屯聚有谷稻甚多,預備運往汗八里城(注:北京城)以作大汗朝廷之用。”對於杭州,他更是用了大量篇幅進行描述:“這座城方圓約有一百英里,它的街道和運河都十分寬敞。……城內除了陸上交通外,還有各種水上通道,可以到達城市各處。所有的運河與街道都很寬敞,所以運載居民必需品的船隻與車輛,都能方便地來往穿梭。”馬可•波羅認為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名貴的“天城”(或譯為天堂之城)——壯觀漂亮、燦爛高貴、繁華無盡,普天之下似乎無可比擬。正是這些記載才讓京杭大運河在當時的國際上享有了盛名。

鄂多立克眼中的“天堂之城”
馬可•波羅離開中國20多年後,又一位名叫鄂多立克的著名的義大利旅行家啟程前來中國。鄂多立克(Friar Odoric:1265-1331)生於義大利小公國弗尤裏的珀德農(Pordenone),少時即入聖方濟各會,在烏迪內(udine)教堂內修道。他是中世紀著名的旅行家,大約于1314年從威尼斯起航開始了其東方之旅。經君士坦丁堡、特拉比松、埃爾茲倫、大不裏士、孫丹尼牙、喀山、耶茲特、百世玻裏、設拉子、巴格達等國家,經廣州入中國,遊歷泉州、福州、明州、杭州、金陵、揚州、北京等地旅行,取道西藏回國。後在病榻上口述東遊經歷,由他人筆錄成書《鄂多立克東遊錄》。該書記載了鄂多立克從廣州經福建浙江到達大運河,後又到達北京的行程。在他的眼中,這個名字為“天堂之城”的城市,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它四週足有百英里,……城開十二座大門。此城位於靜水的礁石上,像威尼斯一樣有運河。它有一萬二千多座橋,每橋都駐有衛士,替大汗防守該城。”此外,鄂多立克還提到了一個名叫“Menzu”的城市,這也是《馬可·波羅遊記》中所沒有的。鄂多立克這樣寫道:“離開揚州,在‘Talay’的出口處,有個名為‘Menzu’的城市。此城中的船隻,恐怕比世上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要多。船的外面被涂成白色,潔白如雪。船上有廳堂和臥室,還有種種生活設施,都非常美觀整潔。此地船隻如此之多,不僅你耳聞之後不太會相信,即使你親眼目睹之後可能也會感到難以置信。”
繼鄂多立克之後,義大利修士馬黎諾裏(Marignolli)也曾來到過杭州。馬黎諾裏是元代末年來中國的羅馬教皇使者,他一行從阿維尼翁啟程,會齊元朝來使,先至欽察汗國都城薩萊(即拔都薩萊,在今俄羅斯阿斯特拉罕附近)謁見月即別汗。繼續沿商路東行,經察合臺汗國都城阿力麻裏,于至正二年(1342)七月抵達上都,謁見元順帝。他對中國的疆域廣大、人煙稠密驚嘆不已,説他途中所經過的城邑村莊難以數計,燦爛光榮之世界,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這有城市三萬,至於小鎮則無可計數。其中,最著名的當推行在(杭州),此城最美、最大、最富。……當人們講起城中的上萬座石橋時(橋上有種種雕刻以及許多手持武器的王子雕像),那些沒有到過此城的人,都認為簡直難以相信,還以為講述者是在説謊。”馬黎諾裏把這裡稱之為“現在存在的,或者也許曾經存在過的,最了不起的城市”。
當時的另一位大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遊記在西元1342年以印度使臣的身份出使中國,一路坎坷行進兩年多才到達了福建泉州。他接著從福建北上,經杭州通過大運河到達北京。伊本在中國也待了大約三年多,在1347年返回到了西方。在其著作《伊本·白圖泰遊記》中對來華後的經歷做了極為詳實的記錄,書中提到他在泉州等到了元帝國可汗的聖旨准許其北上進京,併為其提供了兩條路徑,伊本選擇了走水路。他首先乘船到達了江蘇鎮江,受到了極高規格的接待。“這是一座漂亮的城市,位於廣闊的平原中間。花園環繞,甚似大馬士革的‘姑塔’。”經過十七天的旅行,他又乘船到達杭州。他稱讚杭州城的規模之大,“在地球上我到過的城市中,這座城市是最大的。旅行者曉行夜宿要三天才能走完全城。”
三、明清時期西方人眼中的大運河
明朝末年,隨著地理大發現以後,歐洲人開始向亞洲擴張,西方傳教士紛紛踏上中國領土,其中最有名的當屬義大利人利瑪竇。他兩次乘船沿運河從南京到北京,沿途經過了許多運河城市,其中就包括揚州、淮安、徐州、濟寧、臨清等。利瑪竇對中國運河的總體印像是,大運河是皇家糧食和物資運輸的交通命脈,沿線繁忙而又混亂,經常會發生船隻擁擠、交通堵塞等現象。為了控制流量,政府不得不禁止從長江上來的私商的船隻進入運河,以保證運河漕糧的漕船能夠相對順暢通行。由於運河水量不足,過往船隻經常需要在水閘前面排隊等待。為了確保船隻前行,政府雇傭了大量的縴夫,在岸上牽拉河道裏的船隻前行。他還聽説,每年光是花費在維持運河通行上的費用,就達到了一百萬兩白銀。利瑪竇對此大惑不解:“所有這些對於歐洲人來説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們可以從地圖上判斷,人們可以採取一條既近而花費又少的從海上到北京的路線。這可能確實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擾海岸的海盜,在中國人的心裏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們認為從海路向朝廷運送供應品會更危險得多。”
清順治十二年(1655),約翰•尼霍夫隨以彼得•候葉爾和雅克布•凱賽爾為首的荷蘭使團來到中國。作為荷蘭第一個訪華使團的管事,他對沿途所經之地的風景、地貌作了細緻觀察,對各地的河川、城墻、寺廟、寶塔和奇特的建築物等都做了詳細的記載,寫下了《荷使初訪中國記》這本書。荷蘭使團于順治十三年(1656)五月二十一日從揚州開始沿運河北上,途經揚州、高郵、寶應、淮安、宿遷、濟寧、東昌、臨清、武城、故城、德州、東光、滄州、青縣、靜海、天津、河西務、通州等眾多運河城鎮,七月十二日在張家灣下船,然後由陸路到達北京。總的來説,約翰•尼霍夫的記載是相對客觀而公正的,真實地反映了清初運河沿岸地區的社會風貌,以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該書成為歐洲了解中國的重要知識來源。

馬戛爾尼勳爵訪華

使團覲見乾隆皇帝
喬治·馬戛爾尼使團是鴉片戰爭前到達中國的第一個英國外交使團,是中英關係史上的重大事件。記載此次出使經過的主要正使喬治·馬戛爾尼的《乾隆英使覲見記》《馬戛爾尼勳爵私人日誌》,使團主計官約翰·巴羅的《中國行記》,副使喬治·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隨員愛尼斯·安德遜的《隨使中國記》等。其中約翰·巴羅在其《中國行記》中寫道:“中國的大工程始終而且仍然要用大量勞動力完成,沒有機械之助,除非是個別非用機械力協助人工的地方。……在這些渠道裏航行的船隻,必須用豎立的絞盤把它從水面升高,沒有絞盤就幾乎不可能把裝載貨物的大船從一段運河送入另一段,同時用同樣的方法使船隻緩緩下降。這種笨拙的方法,或許並不意味著不知道使用閘門或別處使用的其他可行之法,而是政府不願革新,以免剝奪成千上萬人的微薄生計,他們現在靠照管這些絞盤為生。不管歐洲怎樣忽視這種觀念,無疑的是,為圖方便和減少勞力而把大批機械引入中國,在目前中國的條件下,將産生有害和可悲的結果。”
1816年,英國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團來華。由於在覲見嘉慶皇帝的禮儀問題上,雙方産生了分歧,最終清政府取消了阿美士德使團的覲見,但准許其沿大運河南下旅行至廣州,由澳門乘船返回國內。使團一行于1816年8月9日由天津塘沽進入北運河,至10月20日,由江蘇儀徵進入長江主航道,共在運河沿岸地區停留達70余天之久。在使團成員亨利•埃利斯和克拉克•阿裨爾二人所撰寫的旅行日誌中留下了眾多有關運河沿岸風土民情的記載和描述。使團成員在前往濟寧的途中,看到了運河水閘的工作方式。亨利•埃利斯對此評價道:“整個設計十分原始,操作時也很不安全,在固定豎立木柱時木樁有可能歪倒,支援它們的繩子也有可能被拉斷。”克拉克•阿裨爾在其所撰《中國旅行記》中記載:“這條溝通帝國兩大部分交通往來的著名水道,被認為是凝聚了辛苦的不朽之舉,在我看來,如果看作是人類勞作和人類技術巨大力量的典範,似乎有些評價過高了。”
晚清時期,由於運河的衰敗,運河沿岸的城鎮繁華不再,西方人筆下的大運河也呈現出一幅殘破、凋敝的景象。1868年12月1日,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從寧波乘船沿運河前往到鎮江,前後歷時15天,于12月15日抵達鎮江。後又于次年3月17日從鎮江出發,乘船沿運河北上,于3月24日抵達淮安王家營,在這裡雇車走陸路前往山東。在其旅行日記中留下了眾多有關晚清運河城鎮風光、名勝古跡和民眾生活的記載和描述。在他的筆下,昔日輝煌的大運河成了骯髒、落後、破敗的代名詞。他記載素有“人間天堂”之稱的蘇州:“這座以美麗著稱的城市,如今也是破敗不堪。”他在蘇州至無錫的途中記載:“接下來在運河上航行的100多裏毫無意趣。這段路程再也看不到比較大的村落,與優越的自然環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地人極度貧困的生活。……他們住在幾乎坍塌的屋子裏,和先時留下的那些宏偉建築物,比如橋梁等形成了刺眼的對比。”
四、結語
西方人對於中國的了解源遠流長,作為中國重要象徵的京杭大運河在西方人的眼中樣貌隨著時間而不斷變化。唐代以前,外國人對中國運河沒有什麼記載;唐代以後,相關的記載開始出現。唐宋時期,由於地理距離的限制,這一時期來華的西方人主要是來自阿拉伯的商人和旅行家。在他們的著作中,雖然對運河記載不多,但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眼中的中國神秘而又富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蒙古帝國向西攻入歐洲腹地,建立起了世界上幅員最廣的大一統王朝,中西方的交流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階段,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這一時期,出現了眾多著名的旅行家,包括馬可波羅、鄂多立克、伊本白圖泰等人。在他們的筆下,中國的運河更為形象和具體,成為體現中國繁華和富有的重要標誌。元朝以後,西方人來華後對大運河的認識開始發生了重大轉變,已經不再是蒙元以前的崇拜和讚譽,更多的是針對實際的客觀評價,既包括他們眼中大運河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也包括大運河在運作千年之久存在的問題。晚清時期,隨著運河的衰敗和時局的動蕩,運河沿岸地區破敗不堪。在這一時期的西方旅行家眼裏,大運河再也不是體現中華文明先進性的重要標誌,而是破敗、落後和貧窮的代名詞。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和中國人民勤勞智慧的象徵,大運河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見證中國近千年來文明發展和國際地位變遷的晴雨錶和風向標。
作者:胡夢飛,聊城大學運河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不代表中國網立場)
相關閱讀:《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近日出臺 相關工作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