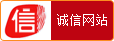古時大運河與通州“抗疫”

清末民初通州燃燈塔舊影
通州位於京杭大運河北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在歷史上有關瘟疫的記載也佔有一定的篇幅。比如《通州志》記:“萬曆十年(1582)春,通州大疫,比屋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連至親都不敢去探望,由此可見這次瘟疫的“慘烈”。
翻閱史書可以發現,大凡通州地方誌書所記載的瘟疫,北京志書中也有相關記錄,而北京志書中記載的內容,也往往會提到通州。比如《通州志》記載了一次瘟疫,“崇禎十六年(1643)七月大疫,名曰疙瘩病,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
這次名為“疙瘩病”的瘟疫,是明末史料中常見的瘟疫,而且危害非常大。根據研究,“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稱呼,患者的身體肢節間會突生一個“小瘰”,接著“飲食不進,目眩作熱”,只要一人被感染,全家都會被傳染。
在史料中,崇禎十三年、崇禎十四年都有疙瘩病的記載。每次出現這種烈性傳染病時,“人死十之八九”。當時李自成的起義軍裏也出現了“疙瘩病”,時人記載:“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
因為傳染性強,崇禎十六年通州所記的“疙瘩病”,不可避免地也出現在昌平、河間等地方誌書。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記載了一次瘟疫,“自春至夏,通州無雨,瘟疫大行”(康熙版《通州志》),而同樣是康熙十九年,《清史稿》記載了蘇州的一次瘟疫:“正月,蘇州大疫。”一個是北方的通州,一個是南方的蘇州,雖然相隔千里,卻在同一年發生了瘟疫。這次相隔千里的疫情或許存在某種關聯:大運河。
為何這麼説?翻開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在關於瘟疫的記錄中,瘟疫發生最多的地方,並不是人們想當然以為的自然條件惡劣的邊鄙煙瘴之地,反而是人口流動最多的繁華地界。
元、明以來有瘟疫歷史記錄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發生瘟疫最多的城市,多是在京杭大運河沿線城市,這些地方人員流動密集,人口規模巨大。
通州是京杭大運河的北端碼頭,各地供給京城的物資以及隨行人員、商賈等,幾乎都要在通州轉机,因此,如果一地發生瘟疫,傳到通州的可能性極大。比如康熙十九年的那場瘟疫,從時間上來看,蘇州是正月發生瘟疫,通州在春夏之交便發生了瘟疫,雖然並沒詳細的史料説明通州的瘟疫來自蘇州,但這兩處疫情的地點和時間,的確因為大運河有了某種關聯。
再有《民國通州志要》記載,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通州霍亂流行”,當時的《大公報》記這次霍亂“始發于塘沽”,可見這場瘟疫是由天津傳到通州的,雖然此時大運河的漕運已經幾乎廢棄,但因通州與天津的距離非常近,且通州仍是轉机之地,也因而被傳染。
那麼中國古代是怎樣防控瘟疫傳播的呢?古代稱瘟疫防控為“降疫”,所採取的手段居然和今天相差無幾:那就是隔離。針對疫情傳染的特性,阻斷反應幾乎是下意識的。《漢書·平帝紀》記載,漢朝對待瘟疫採取防控措施,便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也就是專門騰出空房來隔離,在相對空曠處臨時設置“癘人坊”,這是中國針對瘟疫採取“隔離”措施的最早記載,後世歷代沿襲。
採取隔離措施之後,就是對病患的救治和環境整治。比如《析津志》記載:金朝海陵王築金中都,因時逢夏季暑熱,人多勞苦生活條件又很差,最終導致瘟疫暴發。當時的海陵王是怎麼處置的呢?《金史·張浩傳》記:“詔發燕京五百里內醫者,使治療,官給藥物。全活多者與官,其次給賞,下者轉運司舉察以聞。”也就是説,發生瘟疫時徵調各地“醫戶”支援疫區,而且還根據救治效果給予賞賜。
古代的醫學沒有現代發達,但古人也直觀感知到了環境整治對“降疫”的作用,那時人們認為引發瘟疫的主要是“瘴氣”,而瘴氣的根源則在水源,以古代北京地區為例,每遇瘟疫流行,便對“井窩子”(賣水的水鋪)特別管制,對吃用水井加封井蓋,為防止老鼠及其“病瘤”(即病毒或病菌)落入,同時還要清理城中溝渠,及時排泄城中滯留的臟水。這些辦法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病毒或病菌的傳播。
作為京畿重地且人流密集的通州又是怎樣面對瘟疫的呢?在瘟疫的預防監測上也比其他地方更多程式,清朝刊行的《海錄》中規定,海外船隻進入中國港口要接受檢驗檢疫,“凡有海艘回國,及各國船到本國,必先遣人查看有無出痘瘡者,若有則不許入口,須待痘瘡平愈,方得進港內。”這還是海外船隻進入港口,再通過運河登岸通州,檢驗檢疫也會更加嚴格。
通州作為京杭大運河漕運北端碼頭,歷史上在對抗瘟疫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如今,通州迎來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新時代,通州地區的人口流動更多,城市規模也會越來越大,這將為通州帶來空前的發展機遇,但同時也帶來了某些風險,通州,準備好了麼?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