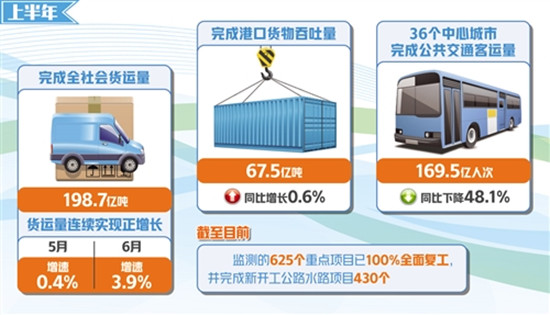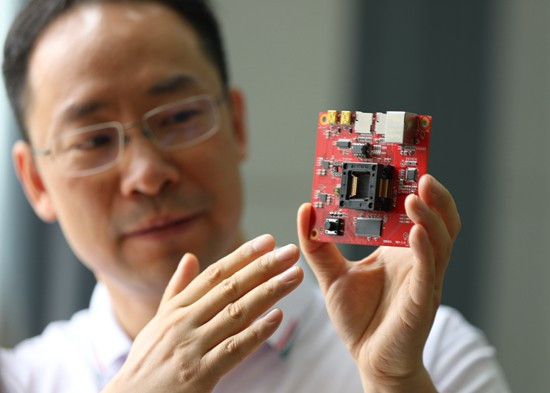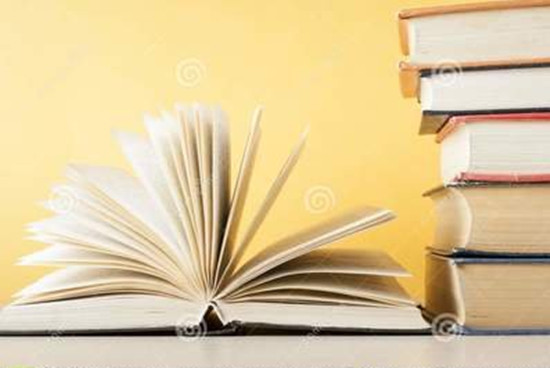種瓜得瓜 吃瓜得燈(豐子愷/繪)
夏天熱得要命,“寒暑表上的水銀好像一個勤勉學生的爭分數,只想弄到full mark,或竟超出其上”(豐子愷),“房間裏,是火爐;椅子,燙的,床上,燙的,墻壁、門、什麼地方,都是燙的:沒有地方可以安身,沒有地方可以鑽”(許傑)。“人張開兩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進來只是熱辣辣的一股悶”(茅盾),“在這樣的熱波裏浸著,便吐一口氣都覺得累贅”(鬱達夫)。在遲子建看來,夏天是她“最討厭的季節”,因為“在這個陽光稠密的時節,我的大腦一片混沌,持續奔流的熱汗將我良好的想像力洗劫得無影無蹤”,“這樣的日子你不會想起溫情的往事。它留給我的全部印象只是‘呼吸’——活著而不思想”。
酷熱讓一切變幹,“河裏連一滴水也沒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烏龜殼似的。田裏呢,早就像開了無數的小溝,——有兩尺多闊的,你能説不像溝嗎?那些蒼白色的泥土,幹硬得就跟水門汀差不多”(茅盾)。期盼已久的雷雨終於來了,“雷是鼓,雨落草地是沉溜的弦聲,雨落水面是急珠走盤聲,雨落柳上是疏鬱的琴聲,雨落水橋闌是擊草聲”,雨嘩嘩地下,一下子讓人“滿眼只是一體的雨色,滿耳只是一體的雨聲,滿身只是一體的雨感覺”(徐志摩),好不痛快!暴雨過後,整個世界為之涼爽,“眼前的一片汪洋,許多孩子所喜愛,他們跣著雙腳,撩起褲管,正涉著水往來嬉戲”(柯靈)。
當然,雨太大了,也會給準備收穫的農人增添無盡的煩惱。“關中幾十年不遇的一個濕夏”,“麥子被連綿不斷的霪雨浸泡得在麥穗上又發出綠芽來,稀泡泥濘的麥田裏,農人無法揮動鐮刀收割已經熟透已經發黴已經出芽的麥子。陰雨持續到夏末,滿川已是一片綠色的苞谷穀子和棉花,陰雨還在持續著,往常的百日大旱變成了百日陰雨,農家用石頭和土坯壘築的豬舍和茅廁十有八九都倒塌了,豬們便滿村滿地亂跑亂拱,人的鼻孔裏都長出黴點綠苔了”(陳忠實)。
蒸籠般的夏天的確是難耐與難忍的。但馮驥才卻摯愛夏天,“我充滿了夏之崇拜!我要一連跨過眼前的遼闊的秋,悠長的冬和遙遠的春,再一次邂逅你,我精神的無上境界——苦夏!”,“苦夏——它不是無盡頭的暑熱的折磨,而是我們頂著毒日頭默默又堅忍的苦鬥的本身”。
人怕夏天的熱,蟬卻一點也不怕。“爬爬兒是蟬的幼蟲,黃昏時從地裏鑽出來,爬到附近的樹上,或是籬笆上。第二天清晨,脫去一層黃色的皮”(孫犁),就蛻變成了蟬。有的人覺得蟬聲“聒噪得那樣地叫人心裏為之煩亂”,然而李廣田卻偏愛蟬鳴,“初夏雨霽,當最先聽到從綠蔭深處鳴來的幾句蟬聲時,是常有一種清新愉悅之感的,覺得這便是‘夏的氣息’了。而且那尚欠流暢的最初的鳴聲,像剛在練習著試調似的,聽來別有意趣。到了盛夏,當然是蟬的黃金時代了。愈是大雨之後,蟬愈多,愈是太陽灼熱的時候,它們也唱得愈狂”。在簡媜看來,蟬是夏之絕句,“蟬聲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絕句。絕句該吟該誦,或添幾個襯字歌唱一番,蟬是大自然的一隊合唱團,以優美的音色,明朗的節律,吟誦著一首絕句。這絕句不在唐詩選不在宋詩集,不是王維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蟬對季節的感觸,是它們對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寫成的一首抒情詩”。
捉蟬是孩子們夏天的保留節目,各地捕捉的方法不一:“北京的孩子捉蟬用粘竿,——竹竿頭上涂了粘膠。我們小時候則用蜘蛛網。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裏絡滿了蜘蛛網,很粘。瞅準了一隻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汪曾祺)。蟬是捉不盡的,“夏天並不因此而止,那些幼蛹,會從許多的地方生長起來,接踵地攀到樹梢,繼續地叫著,告訴我們:夏天是一個應當流汗的季候”(繆崇群)。即使我們捉得住蟬卻捉不住蟬聲,“整個夏季,蟬聲也沒少了中音或低音,依舊是完美無缺的和音”(簡媜)。
夏天除了蟬聲,還有荷香飄溢。朱自清1927年7月描繪的清華園的荷塘月色別有風味,“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有裊娜地開著的,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季羨林喜歡“靜靜地吸吮荷花和荷葉的清香”,“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綠肥、紅肥。倒影映入水中,風乍起,一片蓮瓣墮入水中,它從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卻是從下邊向上落,最後一接觸到水面,二者合二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裏”。
夏天的植物瘋長,“馬齒莧、狗尾巴草、益母草,都長得非常旺盛”(汪曾祺)。狗尾巴草,“莖纖細、堅挺,葉修長,它們散漫無序地長在夏秋兩季,毛茸茸的圓柱形花序活像狗尾”。有的女孩子喜歡“揪下這草穗,編結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搖晃著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草穗單拿草莖編戒指的,那扁細的戒指戴在手上雖不明顯,但心兒開始閃爍了”。也有女孩子喜歡用金黃的麥稈編,“麥稈在手上跳躍,手下花樣翻新:菱形花結的,卍字花結的,扭結而成的‘雕花’……編完,套上手指,把手伸出來,或互相誇獎,或互相貶低”(鐵凝)。
西瓜是消夏解暑的最佳果品。鬱達夫在1935年7月27日日記中寫道:“近日來,天氣連日熱,頭昏腦脹,什樣事情也不能做。唯剖食井底西瓜,與午睡二三小時的兩件事情,還強人意”。汪曾祺也説:“西瓜以繩絡懸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聲,涼氣四溢,連眼睛都是涼的”,“天下皆重‘黑籽紅壤’,吾鄉獨以‘三白為貴’: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東墩産者最佳”。去瓜園走一圈,別有風趣,“午後,趿著拖鞋,搭條毛巾,瓜地邊吆喝一聲,看瓜的老漢就笑嘻嘻銜著旱煙袋,捧著瓜從地裏鑽出,瓜棚是夏天最美妙的地方,坐在瓜棚裏,涼陰陰的,風從八面湧來。此時無煩無惱,只有風,有雲,有滿樹蟬聲,滿地的瓜香”(蔡翔)。
夏天的晚上,乘涼是必備的節目,“搬一張大竹床放在天井裏,橫七豎八一躺,渾身爽利,暑氣全消。看月華。月華五色晶瑩,變幻不定,非常好看”,“一直到露水下來,竹床子的欄杆都濕了,才回去,這時已經很睏了,才沾藤枕(我們那裏夏天都枕藤枕或漆枕),已入夢鄉”(汪曾祺)。
等到蟬聲消逝,荷花凋零,滾燙的酷暑也似乎一去不復返了。(作者:宮立,係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