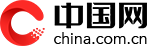這是馬長波在木納斯村的第543天。
2019年的尾聲即將到來。他站在村裏新修的停車場邊遙望遠山。山腳是泛著碎光的沃日河,河的另一邊,是像木納斯村所在一樣泛黃的大山。再遠一點,西南方向綿延著一群覆蓋著皚皚白雪的山頭,在遠處空曠的藍天下顯得尤為寂寥壯闊。
“我都看習慣了,沒感覺了。”馬長波發表對眼前景色的評論,神情平靜。他頭戴一頂藍色鴨舌帽,帽子上“弘揚憲法精神 建設法治中國”的標語在藍天下清晰可見。
一旁的第一書記笑起來,“他説他原來在春熙路看美女也看習慣,沒感覺了。”駐村第一書記名叫彭文清,是小金縣司法局的幹部。馬長波是她的隊員。三人小隊裏還有一名來自小金縣醫保局的何明友——從2018年6月開始,這支扶貧工作隊入駐阿壩州小金縣日爾鄉木納斯村,開啟了新一輪脫貧攻堅戰。
馬長波,是扶貧工作隊裏最年輕的那一個,也是其中唯一的漢族。

紮根木納斯
35歲的馬長波出生於簡陽農村,2007年大學畢業後曾幹過6年的商品管理,“天天都要朝春熙路跑”,直到2012年,他決定考公務員。
“一直在外面飄著,感覺沒做什麼事,不是個辦法。”馬長波給自己的過去做了個簡單定義,順手給身邊的何明友遞過去一塊劈開的木柴。村支書黃維忠家的客廳裏,雪白的墻壁上貼著國家領導人和天安門的畫像,靠近爐火的地方有輕微的煙熏痕跡。爐邊是一排鋁合金窗戶,望出去是深藍天空下似乎亙古不變的白雪山頭。
馬長波挨著他喊“何哥”的何明友坐在領導人像下方的矮沙發上,現在他身上已經完全沒有春熙路的痕跡了。他遞柴給正在生火的何哥,黝黑的面龐在若明若暗的火苗映照下略有些泛紅。
“長(zhang)波哥只要不説話,別人都會覺得他是小金的(人)。”楊學琴笑著告訴我們。楊學琴如今是小金縣稅務局第二分局副局長,此前她曾在木納斯村對面山頭的董馬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因為同在稅務系統的關係,她與馬長波熟識。兩村隔得近,常有工作交流,彭文清的三人小隊都習慣叫她“小楊妹”,而她開玩笑叫的“長(zhang)波哥”,也逐漸成為三人對馬長波特有的稱呼。
楊學琴還記得馬長波剛到木納斯的樣子。“人很白,跟現在完全不一樣。”木納斯村地處日爾鄉東北方高半山,海拔3200多米。全村61戶262人,99%是藏族,一個典型的嘉絨藏族聚居區。因地勢原因,村民的廁所都是旱廁,且建在屋外。“剛來的時候,我回縣裏,他還托我給他買棉拖鞋,還有房間裏用的小便桶,”楊學琴笑起來,“很快他就適應了,什麼都跟村民一樣,你看他現在像不像個老頭兒?”
馬長波早已習慣了隊友和小楊妹的打趣。他還年輕,自然不像老人家,只是在高原風吹日曬後變得黑紅的皮膚,頭上戴著的彭書記同款藍色鴨舌帽,撿起地上曬著的大黃(當地藥材)察看的姿勢,都讓人打心眼裏覺得,他是屬於腳下這片土地的。
“上級對我們駐村的要求,就是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馬長波領著我們走在雪後結了薄冰的山路上,一邊引導我們避開冰面和散落的牛糞。牛糞是寶貴的肥料,春天的時候他曾幫村民扛過,彭文清拿出當時的照片給我們看,照片裏馬長波扛著一大袋子牛糞,正一門心思地往牛圈跑。
村民對我們的到來極為熱情。路上偶遇上山拾牛糞回來的村民,馬長波跟他們打招呼,提醒他們注意安全,村民們向我們説完“扎西德勒”之後,往往會加上一句:“去(我家)喝杯茶吧?”馬長波笑著擺擺手,有時搭手扶一把年紀大的村民。山頭風聲獵獵,陽光碟機散著寒意,遠山靜默。馬長波回頭注視著背著背簍遠去的村民,“這裡的人們都很熱情好客,特別質樸。”
“要讓村民覺得你是自己人,你講的話才有説服力。”馬長波臉不紅氣不喘地走在山路上,如履平地。這些路他實在太熟悉,幾乎不用低頭看路。“我覺得我們像是被撒出來的釘子,扶貧比如一張藍圖,我們就是把這些藍圖釘下去,只有深深地紮根進泥土裏,扎到木納斯村的村民中間,才能釘得穩、釘得牢。”
馬長波的確沉穩地、不聲不響地扎進了木納斯村。楊學琴説自己剛開始駐村的時候,經常哭。“因為感覺什麼都不知道,”她雖然是小金本地人,面對貧困的農村也一度手足無措,“那時候就會跟長波哥討論,他會耐心地幫我想辦法。”楊學琴發現,即使很多事情馬長波從沒做過,也能很快摸清頭緒,做得有模有樣。長波的“長”,某種程度上變作了“兄長”的“長”。
講起扶貧工作和村裏的大小事宜,馬長波神情鬆弛,雙手偶爾在身前揮一揮。他在這裡,一切都融入了他的生活,從日出到日落,時間讓他與這座山氣息相連。採訪中大部分時間他都從容泰然,唯有在面對攝影師鏡頭的時候,他才像我們身邊的大部分男性一樣,突然變得緊張僵硬。
“你從這塊石頭上跳下來一下吧!”攝影師蹲在地上仰起相機。
“好。”他應了一聲,同手同腳從石頭上跳下來。
一旁的圍觀群眾發出一陣短暫的哄笑。他也跟著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