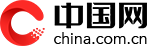平凡亦有可為
河灘上的冰雪漸漸融化。村長吳學周搬到了山腳下。
“那裏,看到沒有,那個電站邊上,我們現在就住在那兒。”他伸出右手,食指遙遙指向山腳下沃日河中一灣碧綠的水域。
彭文清在一旁又笑起來,“吳村長‘叛逃’了!”吳村長趕緊擺擺手笑起來,臉龐微紅:“沒有沒有!”彭文清又説,“我們黃書記(村支書)一家也已經在山下買了地了。”這幾天黃書記的愛人住了院,他正在醫院陪護,並不知道自己要搬家的消息即將傳到一百五十公里外。
經濟條件稍微好一些、年紀尚輕的村民們陸續搬到山腳下或是日爾鄉鎮上,這裡有更好的教育、醫療資源,以及更適宜的居住環境。馬長波也是這樣跟村民們分析的,隨著年齡增長,對便利的醫療條件的需求也將日益增長,而儘管新修了山路,但下山路開車仍然需要30到40分鐘。有時候這幾十分鐘,就是生死攸關。
“但是故土難離嘛,”馬長波的手在膝頭輕輕叩了叩,“老人對自己的村落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肯定要充分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隊友何哥是縣裏醫保局的,他跟何哥對疾病有過深入的討論,希望能最大限度地預防高半山區域村民們的多發疾病。
“這裡心肺問題比較突出,”馬長波又開始分析,“你看,因為首先這裡海拔比較高,其次大家又比較喜歡喝酒,上了年紀心肺出問題的概率就比較大。”工作隊對此進行調查討論後,將相關民情上報了相關部門,很快就有了相關健康知識宣傳和定期檢查。
馬長波對比了簡陽老家和藏區農民的醫保報銷情況,發現如今醫保政策已經儘量向邊遠貧困地區傾斜。這個數據最直觀地來自他的父親。2018年,他的父親因車禍受傷入院,母親不識字無法照顧,焦急輾轉之下,上級部門多方協調,給了他二十天假回家陪護父親。“那是最難的時候,”馬長波衣兜鼓起來,他的手揣在裏面,“我爸年紀很大了才生的我,現在年齡大了,我又不能隨時在身邊照顧。”等了一會兒,他鬆開手,看向爐火,神色復歸平靜。
“等回去了,我會好好陪他們的。”他把雙手在身前交叉起來。“他們”,還包括母親、妻子和兩歲的兒子。村民朱菊香家的小兒子往他懷裏鑽的時候,他的手臂略有些僵硬。“我那個兒子啊……”他眼神亮了亮,沒有再繼續,轉而低頭對懷裏的小傢夥笑起來。
“回去後再好好彌補,好好陪他。”他寄望于小朋友兩歲前的記憶都是模糊的,等他回去後再陪伴還來得及。“等他長大了,我就帶他回這裡,告訴他這裡有爸爸的‘戰友’,這是爸爸曾經流過汗水的地方。”陽光穿透稀薄的空氣照在我們身上,山坡上挖大黃的村民三三兩兩散開,有鷹在墨藍的空中盤旋,時間緩慢近乎凝固。停了好一會兒,馬長波突然開口:“我想跟他説,你看,人生從來不輕鬆,大家都是平凡人,只有腳踏實地幹過一些事,才算過好了這一生。”
高中時期的馬長波從當時僅有的200塊生活費裏拿出15塊,買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看了很多遍”。這本書和童年時的農村經歷一起,共同構築了他人生選擇的基礎。農村生活對人的磨礪是全方位的,驕陽黃土下的汗流浹背、狂風暴雨前的慌張收曬,幹起來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插秧、收割、脫粒、堆垛……都在輕輕的一句“苦大的”裏帶過。這段經歷練就了他極強的適應力,吃苦於他,駕輕就熟,“這裡比小時候的條件好多了。”
“為什麼來這裡呢?”我問他,“王局長説只有你一個人主動申請。”
“其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申請,”他鬆開交叉的雙手,“只是另一個同事家裏確實走不開,我們局又剛好需要人過來,我又是黨員,那我就過來吧。”
“事情總要有人做,對不對?”他抬起頭看著爐火。妻子和家人對他的理解支援讓他感到十分滿足,“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有一個幸福和睦的家庭。”
大概是想到了妻子,他的語氣柔和起來。他説等回去後,要把這一段經歷好好寫下來,“時不時拿出來看看,免得老了忘記。”
“那是不是也把我們寫進去呢?”何哥指指坐在對面的彭文清和小楊妹,又指指自己。
“肯定啊,”馬長波哈哈大笑,伸出手比劃了一下,“起碼要寫好幾大章哦!”
何哥和彭文清、小楊妹笑成一團。他們是他的戰友,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馬長波就是這麼介紹的。精準扶貧,的確是一場需要精力和耐心的戰役,要與之抗衡的,不止是惡劣的自然條件、未知的災害風險,還有內心的孤獨、徬徨與迷茫。有戰友,一切都不會太壞。
次日就要準備迎接國檢抽查了。來自長安大學的大學生志願者將走進被抽中的貧困村,了解扶貧工作開展情況,確定各項指標,為各駐村工作隊2019年的工作打分。
“我們還是比較有信心的,”馬長波望向自己的隊友,“大家的生活的確在變好。”然後,他小聲但篤定地説道,“我們還是做了一些事的,大家都看得見。”
採訪結束,告別的時候到了。他和他的戰友們在村頭與我們揮手告別。稍後他們還將為明天的國檢進行簡單的討論與準備。“要把我們長波哥寫好一點哦!”何哥對我們喊。“重點是要宣傳一下我們木納斯村!”彭文清笑著加了一句,“我們這裡七八月特別涼快、特別美!”
敞亮的太陽光下,他們的笑容真摯又熱烈,和他們身後的木屋與柴火堆一起,從車窗中漸漸遠去。
車過日爾鄉,有一段路上密集飛揚的塵土掩住了車窗外的遠山。塵土漸消之時,雪山又再浮現。我想起馬長波和吳村長在村裏的對話。
“你曉得‘木納斯’在藏語裏是啥子意思不?”馬長波問吳村長。吳村長揪了揪衣袖,呵呵笑起來。
馬長波看著他,嘿嘿一笑,頗有些得意,“我專門問了,是水稻。”
是水稻。
這個村落所期盼的豐收富足,如今再不用寄託在對魚米之鄉的想像上。(羅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