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我六七歲的時候,我們全校的小朋友都在泥濘的村子主路上,跳著舞、搖著花環、喊著口號,敲鑼打鼓熱鬧非凡地送一批解放軍叔叔上前線。他們胸前戴著大紅花,雄赳赳地列隊前行,遠遠走出了村口用松枝搭起的高高凱旋門,我們的口號聲還此起彼伏,一陣一陣成了每個班級的拉練。
後來才聽老人説他們是去前線的支前民兵,那時認為穿上綠軍裝就是無比崇敬的解放軍了,雖然沒有紅五星和紅領章,沒有我一個遠房表叔穿綠軍裝的照片英武帥氣。他在照片裏一身綠軍裝紅五星腰間別著手槍,一手掐腰,目光堅毅,一手佩戴著上海手錶在指著軍用地圖。那張照片,簡直佔據了我小時候的憧憬和夢想,每天都要盯著相框看,每次都想像著照片之外是如何的炮聲隆隆、槍聲陣陣、震天動地。
那幾年最盼望著這個表叔回來探親,他一回來整個院壩裏都圍攏了鄉親父老,聽他講故事,傳著看他的立功證書和獎章。我們小孩子最幸福的事,就是分到一小塊壓縮餅乾,窩在墻角裏舔著那種甜甜鹹鹹的味道,無限的甜蜜洋溢在小小院壩中。
再後來表叔光榮地從部隊退伍回來了,他人長得高大英俊腦子又靈泛,在鎮子裏第一家開起了照相館。過年過節我們都相約著去照相,穿上最想穿的衣服,坐在硬紙板做的雅馬哈小摩托上,不斷地更換著天安門、長城、大海、藍天的背景,咔嚓咔嚓地留下了一張張開心的笑臉。儘管是手繪的背景、黑白的底色,但在暗房裏沖洗後,根本看不出任何笑靨背後的皺褶。緊接著表叔又搗鼓起鐘錶修理,把那支黑黑的炮筒眼鏡塞在雙眼皮中,他可以在各種齒輪螺絲中坐一天到晚。我最感興趣的是那一排排挂在玻璃罩罩下面的電子手錶,各式各樣,花花綠綠。去他店裏多少次,就看了多少眼。不敢要那些鐵錶帶的廣州貨,心想哪怕是能有一塊塑膠錶帶的,也總比我畫在手上的抖草。
表叔時不時地找我爸款嘴嘮家常,他一進屋,我就貓出去悄悄地跨上他的28永久單車,雙手扶龍頭,屁股半坐在三角架上,雙腳只能半圈半圈地踩。腿太短,稍微一不小心,半個屁股一條褲子上就沾滿了泥巴或鏈條上的油污,甚至連人帶車摔倒,被刮破皮撕爛褲子也是常有的事。從村頭到村尾,掐算著時間差不多了,再偷偷地把他的座駕還回去。很多時候,是媽媽在大聲叫喚,也有些時候是表叔和老爸在屋檐下抽著老煙筒,笑瞇瞇地等著我回去。
有一次不小心又撒遠了,等我大汗淋漓急急忙忙地趕回去,表叔有事已經先回去了,這時候免不了一頓批鬥。不過還好,還沒等我委屈的眼淚掉在地上,媽媽笑呵呵地拿出了一樣小禮物。呀!是表叔送我的一隻電子錶。我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一塊表,人生第一塊手錶!至少,我可以自己看著時間去上學;至少,我可以晚上睡覺時按一下,它的表盤就發出淡淡的優雅的綠光;至少,我在這麼多的小夥伴中是第一個戴手錶的人!
時間在滴滴噠噠中行走,季節在冷暖變化中交替。正月的大地千枝萬樹竟相發芽,田間地頭的迎春花、羊耳朵花、苦刺花、棠梨花在風中搖曳,路頭村尾的桃花姹紫嫣紅、梅花紅白相間,仿佛是一夜之間就全部綻放開來。二大爺家院子裏的山茶樹虬勁若雲,年前就盛開的花朵端莊依舊、粉粧玉砌。田野裏綠浪翻滾,一片片綠油油的青蠶豆、一條條金燦燦的油菜花、一個個亮晶晶的泛舟湖,春意濃濃的高原壩子萬物復蘇,生機盎然,遇見的每個人都在春風拂面中互致一年的問候。剛過的元宵節裏互相“偷青”,象徵性地在別人家地裏摘幾個青蠶豆、拔一顆青菜,也希望別人多到自己的菜地裏踩青,才預示著一年的好運連連。春天的氣息瀰漫在每個人的心田,我們每天在菜花地裏逐蝶攆蜂,玩累了就大把大把地吃著鮮嫩甜脆的蠶豆,捧一口甘甜的池塘水解渴,然後在豆田花海裏美美地睡上一覺。冬春的池塘裏水位下降,在露出的臺地上,大人們辛勤地理出一壟壟整齊的水稻育秧地,那裏的小苗正齊刷刷地排隊出操。這個季節,我們要按照父母的安排,每天扛著一根竹篙穿著一個塑膠瓢去給秧苗墑溝澆水,回來的時候還要在田埂上割一籃子青草喂兔子。
我每天都看著時間去澆水,生怕那些嬌嫩的小苗渴著餓著,擔心照顧不好會耽誤了插秧時間。雖然我還沒有竹篙的一半高,儘管我使出吃奶的力氣還舀不滿一瓢水,但還是要看著表在天黑前把墑溝裏澆滿水、背籃裏割滿草。波光粼粼的白水湖是我們家鄉的寶,方圓十幾個村子依湖而生、傍湖而建,炊煙嫋嫋、楊柳婀娜、魚米飄香,半池出水芙蓉,一湖蓮菱珍饈。整個的夏天,我和小夥伴們都泡在白水湖中,每次回家都要被媽媽在背上刮下一層層指印,她可以從指甲尖裏的水氣和印跡推斷出那天遊了幾次澡。記得有一次農忙時媽媽叫我回家拿一個背簍,我直接套在頭上裝盔甲,結果一不小心掉在轉角的池塘裏,好在白水湖裏練就的基本功成就了我,慌亂中,亂撲亂抓地遊到了岸邊,總算是撿回了一條狗命。
這些小溝小壩塘都不在話下,我們“扛過槍”、遊過泳、翻過船、“打過仗”。記得有一天去澆水非常急躁,只想急著早點回去看電視,那段時間剛播完《霍元甲》又正在放《西遊記》,小夥伴們都要來看,回去晚了,耽誤了上房轉天線,電視機一齣雪花點那就把臉丟大了。反正是匆匆地澆水,隨意地割了幾把草,就小跑著趕回家。
第二天起床,才發現手錶的時間不對了,沒了燈光,沒了跳動,是電池幹了嗎?還是按鈕壞了?——天!我心愛的手錶竟然只剩表殼和錶帶還在手上,電子錶的表芯居然不見了!哦,是掉在哪了呢?這手錶,品質也太不靠譜了。急得我翻箱倒櫃地到處找、到處回想,我好不容易的一塊電子錶呀,它到底去哪了呢?害得我順著昨天澆水割草的線路一點點搜索偵察、一點點掃蕩回憶。這麼個小孩,老天你為什麼要叫他的表掉了呢?
秧苗長出了新芽,個頭越竄越高,炎熱的五月一到,它們就要被移栽到大田裏繼續安家。三四月間收完蠶豆,我們就跟著大隊上的履帶拖拉機去犁田翻地,我用紙畫了一張表盤,緊緊地粘在我的手錶表盤內,不時抬頭看表,一手扶門一手指揮,同時想像著坐坦克指揮打仗的場景。
落實政策後,退伍回鄉一年多的表叔去了有名的供銷社,過幾年他的坐騎換成了拉風摩托,戴著墨鏡穿著喇叭褲行走在村社鄉間,我的羨慕視野隨之轉移到他管的大倉庫裏,那裏有高聳的物資、成垛的糖果和堆成小山的連環畫,曾經我為了一輛小單車睡在百貨公司的地板上滾來滾去,現在好歹可以飽飽眼福,有時候一整天就坐在他的辦公桌前如饑似渴地看那些連環畫。大約是我上高中的那幾年,隨著企業改製表叔離開了供銷社,幹了一輩子,離開後他也想再創業,開過小廠、做過買賣、盤過餐廳、跑過保險,無奈總是諸事不順。我工作後,聽説表叔還是好喝酒,改不了酒多就話多事多的老毛病,還經常住院。去醫院看他,他日漸消瘦,一見到我就訴説過去的辛酸,話少語輕,但俊朗的五官中仍有那麼一些堅毅和硬挺。
和我祈盼的相反,他終是沒有熬過那個冬天,在沒滿花甲的年歲惜別了他的戰場。時間像是和我的表盤一樣,掉在了白浪滔滔的白水湖中,看似停滯,但兜兜轉轉,它終究還是在另一個世界永生著。(燕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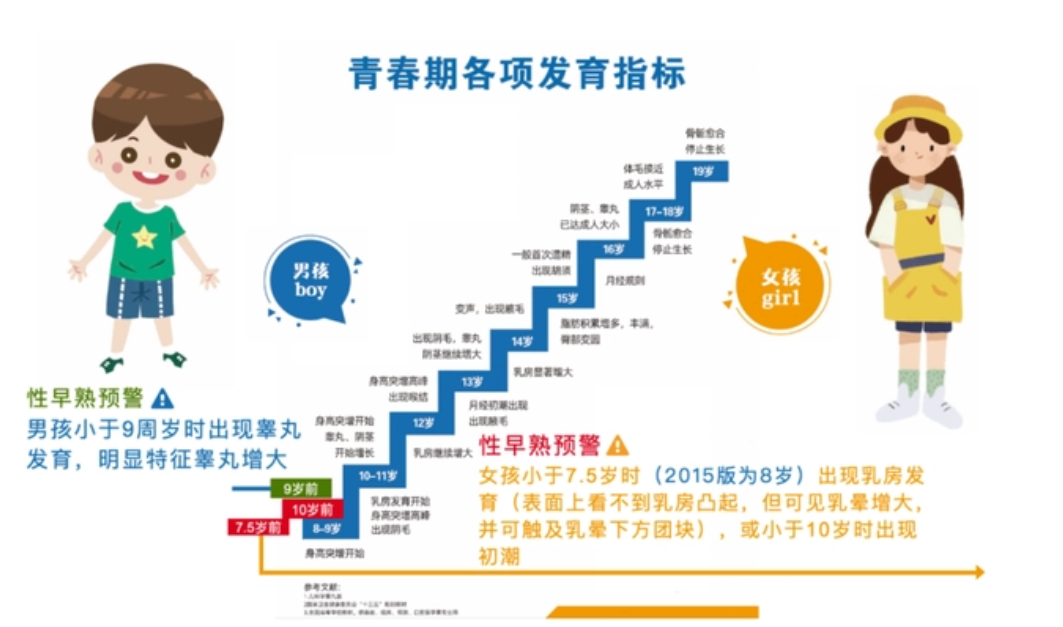
050b0da7-1806-43b5-a7a3-c7961f54d58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