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春華秋實,二十青蔥,四十不惑、六十從容、八十如典。歲月把馬大正先生帶到八秩之年,回望數度春秋,他六十年治學研史,勤奮執著,孜孜以求,以赤子之心、學人擔當譜寫人生華章。
民族史的探索
大正先生1938年9月出生在上海,1956年至1964年,他在山東大學歷史系完成本科和碩士研究生的學業,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不承想,大好時光竟被十年“文革”耽誤了。直至1975年,在著名學者翁獨健先生的指導下,他才參與了《準噶爾史略》一書的寫作工作,並走上了民族史探索的道路。

資料圖片
準噶爾原是我國清代衛拉特蒙古族的一部,明末清初,準噶爾崛起于西北,統轄衛拉特諸部,其後裔至今生活在我國新疆、青海、甘肅、內蒙古一帶。《準噶爾史略》在尊重史料的基礎上,肯定了準噶爾的歷史作用,在漫長的歷史征途上,準噶爾部躍馬揮戈,馳騁疆場,外禦強敵,內勤牧耕,為開拓和保衛我國西北邊疆作出貢獻。
《準噶爾史略》是研究衛拉特蒙古部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在這部書的撰寫過程中,老一輩學者的治學精神給大正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至今不忘翁獨健先生的諄諄告誡:“一定要詳盡地掌握原始資料和國內外研究動態,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齊,編好目錄,仔細閱讀,在前人的基礎上,把這本書寫成有較高科學性的民族史學專著,不要成為應時之作。”
帶著前輩的囑託,大正先生走上了這條艱辛的學術之路,而且一走就是幾十年。20世紀80年代初,他參加對新疆地區蒙古族的考察,多次深入土爾扈特部落探訪,後來將一幕幕生動感人的場面記載下來,寫成《天山問穹廬》。“我讀著這本透著滿紙煙雲與蒼涼的書籍,合書掩卷常思以往的歷史,慨嘆著曾經失去過的那一片片遼闊富饒的土地,還有蒙古民族那富有英雄傳奇般色彩的歷史故事,我滿腹悵惘,一臉清淚。”一位讀者曾發出這樣的感嘆。
1982年始,大正先生與清史專家馬汝珩先生合作,完成了多篇論文,如《顧實汗生平事略》《厄魯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達評述》《土爾扈特蒙古係譜考述》《試論渥巴錫》《渥巴錫承德之行與清政府的民族統治政策》等。對土爾扈特部的這些研究極具功力,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
大正先生與馬汝珩先生合作完成的《飄落異域的民族——17至18世紀的土爾扈特蒙古》一書至今為學界樂道。這部書歷經十載,四易其稿。在土爾扈特蒙古部的部落源流與王公係譜、土爾扈特蒙古與清朝政府的關係、土爾扈特蒙古與俄國的關係、土爾扈特歷史人物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中,顯示了獨特的學術眼光與見解。書中關於土爾扈特蒙古部東歸的細節描寫尤其讓人動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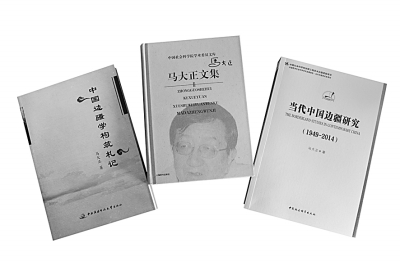
資料圖片
伏爾加河1月初的氣候,正是隆冬季節,寒風凜冽,就在這時,成千上萬的土爾扈特婦孺老人乘上早已準備就緒的馬車、駱駝和雪橇,在躍馬橫刀的騎士保護下,一隊接著一隊陸續出發,徹底離開了他們寄居將近一個半世紀的異鄉。他們衝破俄國的雅依克防線,渡過雅依克河,冒著隆冬的嚴寒,迅速進入哈薩克大草原,向恩巴河挺進。歷時八月有餘、行程近萬里的東返征程,終於以土爾扈特人的勝利返歸祖國而結束。
隋唐民族關係史是大正先生民族史研究的另一個重點。1984年,他參加了翁獨健先生主持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中有關隋唐民族關係史的撰寫。從《準噶爾史略》到《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通過對衛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關係史的研究,他對中國歷史上最有特色的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疆域、民族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與認識。
在對隋唐時期少數民族關係的研究中,大正先生通過深入考察,廓清了這一時期民族關係與邊疆的一些重大問題。他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隋朝統治時間雖短,但結束了近400年割據分裂、軍閥混戰的局面,由割據重新走向統一。唐朝推行“以武撥亂”的方針,開疆拓土,抗擊突厥,聯合回紇,廣開北疆,統一西陲,經營東北,對吐蕃與南詔和戰並舉。盛唐時期的疆域,超過了西漢鼎盛時期的版圖,成為當時世界上版圖最大、勢力最強的封建帝國。
大正先生認為,隋唐時期的邊疆政策接受了數百年來的經驗與教訓,是歷史發展的産物。唐高祖對前代的教訓有清醒的認識,因此他要“追革前弊”,制定更加符合當時社會狀況的邊疆政策,這個政策的主旨是“就申和睦,靜亂息民”,“懷柔遠人,義在羈縻”。這是一個卓有見識的戰略方針,為唐代確立比較開明的邊疆政策打下了基礎,到唐太宗時期這一方針有所發展,如“懷之以文德”就成為唐太宗治理邊疆的基本政策。
大量史料的掌握,不僅讓大正先生的民族史研究紮實可信,也為他日後研究道路的拓寬打下牢固的基礎。他不僅在浩瀚的史料裏爬梳整理,而且在漫長的邊境線上奔走前行,考證史料記載,收集鮮活資料,讓自己的學術底氣更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他行走邊疆,研究邊疆,足跡所至竟達70多萬公里。
邊疆學的研究
從20世紀70年代研究準噶爾歷史開始,大正先生的學術生涯與邊疆就再也沒有分開過。此後幾十年間,他的數十部著述都是圍繞邊疆展開的。“從古代到當代多個層面追溯邊疆歷史、從宏觀和微觀多個角度解析邊疆歷史,致力於從邊疆歷史演進中探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發展規律,從紛繁複雜的邊疆歷史嬗變中探尋邊疆治理的癥結和路徑。”他的同事李國強研究員如是評價。
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日子裏,大正先生一如既往地從閱讀文獻典籍做起,以更多地佔有史料。同時,他注重邊疆歷史與現實的結合,在觀察、分析的基礎上,形成了邊疆歷史研究的新思維、新方法、新格局。1994年,他擔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擘畫統籌,身先士卒,傾注了大量心血。
為改變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冷寂的局面,大正先生提出開展中國疆域史、中國近代邊界沿革史、中國邊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構想,並提出一系列有利於研究深化且行之有效的舉措。20世紀90年代,他主持並參與了當代中國邊疆系列調研。在他和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具有優良傳統與百年積累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得到長足發展,實現了新的飛躍。
這一時期,中國邊疆史研究的發展脈絡,尤其是對中國古代治邊政策研究更加清晰。大正先生通過分析做出這樣的判斷:中國古代治邊政策自秦漢至清朝逐步完善,秦漢時期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治邊政策,經隋、唐、元、明的充實,到清朝已經比較完善,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清朝治邊政策可謂集封建王朝治邊政策之大成,是中國國情的特定産物,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地域的廣闊性、內涵的多樣性、影響的深遠性等特點。形成這些特點的重要原因則是中國古代治邊政策與治邊思想,它們在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統一,協調了民族關係,推動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發展,加強了邊疆地區的經濟建設,推進了邊疆與內地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2013年8月4日,時隔20年,馬大正二訪紅其拉甫邊防7號界碑(資料圖片)
總結過往,是為了今天與未來。借助對中國古代邊疆治理的深入研究與對疆域的考察,大正先生發前人之未發,提出許多極富價值的見解。他認為,中國邊疆地區的戰略地位可以從歷史與現實兩方面審視。從歷史上看,當代中國邊疆是兩大歷史遺産的平臺,這兩大歷史遺産一是幅員遼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二是人口眾多、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這兩大遺産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如果沒有邊疆這個因素,就不成其為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國邊疆地區存在,那麼生活在這個地區的各民族可能也進入不了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範圍裏。
“回顧我在邊疆中心工作的歲月,大體上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為開展三大研究系列的研究出謀獻策;二是為當代中國邊疆調查與研究的展開身體力行;三是為中國邊疆學的構築盡心盡力。”大正先生躬身力行的這三件大事,其潛在的作用、價值與意義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凸顯出來。
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除了總體上的協調組織,大正先生的個人研究與調研絲毫沒有鬆懈,完成了從民族史研究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跨越。他的研究領域從民族史拓展到中國疆域史,特別是在中國歷代邊疆政策和中國疆域發展的綜合研究、清代新疆地方史研究、中亞史和新疆周邊地區史研究、東北邊疆史尤其是古代中國高句麗歷史研究、當代中國邊疆穩定特別是新疆穩定與發展戰略研究等方面,用力尤甚,用功最多,他的研究,彰顯了恢宏的學術視野與崇高的時代擔當,由他主編或撰寫的相關著述多達15種。其中,他主編的《中國邊疆經略史》《中國古代邊疆政策研究》,他參與主編或撰寫的《清代邊疆政策》《清代邊疆開發研究》《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等著述獲得學界好評,多次獲得圖書大獎。
新疆既是大正先生研究的起點,又是他研究與考察的重點。20世紀90年代,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完成了12個調研報告,而新疆就佔了一半。30多年間,他60余次來到新疆,走遍了新疆絕大多數邊境線、新疆周邊的鄰國,穿越了塔克拉瑪幹沙漠,考察了土爾扈特部的“東歸”和察哈爾的“西進”。他通過嚴謹的論證,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在當代新疆研究上取得常人難以企及並富有價值的成果。
新學科的構築
隨著研究的深入、視野的開闊、史料的充實、理論的支撐,一個更為宏大的目標在大正先生心中日漸清晰:中國邊疆學的構築。他認為,面對新形勢的需要,應通過維護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的研究,總結歷史上的邊疆治理經驗,考察當代中國邊疆穩定和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制定相關的邊疆穩定與發展戰略。顯然,這樣宏偉的任務僅僅依靠一門或幾門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是不能完成的,唯有憑藉中國邊疆學方可達到。中國邊疆研究不但追尋歷史的發展軌跡,還應探求中國邊疆發展的未來;中國邊疆研究不僅擁有豐富的歷史遺産,還要開拓未來的發展道路。
正是這樣的學術胸襟,推動大正先生的研究邁上了新臺階,瞄準了新目標,達到了新境界。同時,他也非常清楚,中國邊疆學是一門新興邊緣學科。新興,意味著創業;邊緣,意味著艱辛。早在20世紀末,這個目標就在他的心中萌動、升騰。1997年以來的20年間,他寫的幾十篇論文都是圍繞這個命題展開的。大正先生深知,中國邊疆研究面臨的任務、中國邊疆研究的深化離不開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地理學、宗教學、哲學、文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口學、心理學、生態學等多學科學者的參與。因此,中國邊疆研究實現向構築中國邊疆學的飛躍,既是學科發展的必然,又是時代的要求。中國邊疆研究具有相對明確的研究對象,具有眾多學科研究方法的支援,具有特殊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完全可以併入正在發展為具有獨立學科地位的中國邊疆學。將中國邊疆問題置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與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作用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國邊疆學的特殊價值首先體現于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認識,其次體現于對中國邊疆及其各個局部的認識,最後體現于對邊疆這一抽象的人類社會歷史産物的認識,這一特殊性是任何一門學科無法替代的。
如果説上面所述是一種理想的話,那麼從理想到現實還需要許多鋪墊與轉化,大正先生將其視為“過三關”。第一關,從繼承到創新。中國邊疆研究已有較長時間、較大規模,尚需創出新路。第二關,從分工到合作。要在各學科領域對中國邊疆研究進行分工,要有各方面的合作。第三關,從自然到自覺。要逐步將以自然應變為主的研究轉變為以自覺為主的研究。與這“三關”相對應的是處理好“三個關係”。一是研究中國邊疆與中國邊疆學研究的關係。二是研究服務於社會需求與中國邊疆學學科發展的關係。三是把握好中國邊疆學研究的客體與國際社會接軌的關係。
對於學界關心的中國邊疆學的內涵,大正先生也給出了初步框架。他提出,中國邊疆學的內涵可以分為兩個領域:基礎研究領域、應用研究領域。基礎研究領域包括中國邊疆理論、中國歷代疆域、歷代治邊政策、邊疆經濟、邊疆人口、邊疆社會、邊疆立法、邊疆民族、邊疆文化、邊疆考古、邊疆地理、邊疆國際關係、邊疆軍事、邊界變遷、邊疆人物等諸多方面。應用研究領域是對當今及未來中國邊疆發展與穩定的戰略性、預測性的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研究,涉及的方面與基礎研究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是有更強的現實性。這些全局性、戰略性見解體現在大正先生的《當代中國邊疆研究(1949—2014)》《中國邊疆學構築札記》等多部著述中。
《清史》的纂修
2002年12月12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戴逸先生出任編委會主任,全面負責清史纂修的學術組織工作。清史纂修工程由此正式啟動。對於新編清史,更是提出了明確要求:“編纂的清史品質要高,必須是精品,要注重科學性和可讀性,確保編纂出一部能夠反映當代中國學術水準的高品質、高標準的清史巨著,使之成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
作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的大正先生,又站在了一個嶄新的起跑線之上。這一年,他已經64歲了。
盛世修史,責任重大。當宏願即將實現時,大正先生感到肩上擔子從未有過的沉重。在戴逸先生的帶領下,他與同仁傾其全力,投入了這一宏大浩繁的世紀文化工程中,配合戴逸先生,做了大量協調、組織與撰寫工作,許多工作都是親力親為,狠抓落實。
16年來,大正先生參與新修《清史》的設計、立項、撰寫、審改、定稿五個階段的學術組織工作,並先後分工負責典志組、史表組、篇目組、編審組、文獻組、出版組、秘書組的學術聯絡工作。他認為,新修《清史》應力求寫成一部反映當代中國清史研究水準、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史學著作。而能否實現這一目標,有待參與這一工程的專家們的不懈努力,最終能否達到此目標,則要由學術界同行和所有關注此工程的人士來評議。
在大正先生看來,在《清史》的纂修實踐中,有四個重要因素為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可能。一是資料的利用面大大擴展,為超越和創新提供了紮實基礎。二是體裁體例的佈局和內容的拓展,為超越與創新提供了可能。三是科研組織和管理上的有益嘗試,為超越和創新準備了條件。四是樹立了從世界視野來創構編纂清史的新體系。這是新修《清史》的創新之處。
2018年10月,新修《清史》送審稿完成,計106卷,104冊,另附錄6冊,隨之進入《清史》送審稿送審、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結項與《清史》出版流程。16年的心血,16年的努力,大正先生的學術人生有了特別的意義,新修《清史》即將完成,他80歲的生日也因此平添了喜悅與欣慰。
回顧新修《清史》的學術經歷,大正先生十分感慨:“這次纂修清史應該成為清史研究進程中的一個坐標,它既是20世紀清史研究成果的繼承和發展,又是21世紀清史研究的一個嶄新起點。”
“在史學領域裏,我還是做了些許工作,簡言之,一是習史,二是研史。研究工作優劣成敗,應由社會評説,我只是做了應做的工作,在所在的崗位上盡了責、出了力,沒有虛度年華。”
“中國邊疆研究涉及內容豐富多彩。上下五千年、東西南北中,似蒼穹,似大海。而自己幾十年研究所涉獵內容雖大都當在其中,但似星辰、似浪花。”回顧自己的治學歷程,大正先生在《我的治學之途》中這樣説。從黃浦江畔走入齊魯大地、走進大漠荒煙、走向茫茫海疆,從青蔥到耄耋,他把自己交付給了學術研究。他不曾動搖,不曾停歇;他心存高遠,腳踏實地;他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在他人生的行囊裏,裝滿了歷史與邊疆,裝滿了使命與擔當,裝滿了艱辛與榮光。
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説,在歷史的長河中,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用一生踐行這個理念,為中國思想文化寶庫增添異彩,受到人們景仰。大正先生的學術精神與學術探索,讓人們看到了薪火相傳的光芒。他踏著先賢的足跡前行,守正出新,唱響了匯入中國學術洪鍾大呂的“三部曲”。對祖國的摯愛、對歷史的敬畏、對治學的崇尚、對人生的追求,這正是大正先生學術自覺、學術格局的力量源泉。
八秩之年,大正先生的邊疆情懷依舊,邊疆激情依然。“我最大的心願是:熱望中國邊疆研究的大發展;呼喊中國邊疆學的誕生!”這是一位一生研究邊疆、行走邊疆、情係邊疆、奉獻邊疆的學者最大的期盼與願景。他期待著中國邊疆學這個“寧馨兒”早日降生,他要在這片熱土上繼續耕耘,春種秋收。在大正先生八十華誕之際,以上文字若對年輕學子有借鑒意義、對邊疆研究有啟迪作用,斯願足矣。
學人小傳
馬大正,1938年9月生於上海,山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生畢業。1964年任職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7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歷任副主任、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2002年始兼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長期致力於中國邊疆歷史與現狀,唐代、清代邊疆史研究。當前主要從事中國邊疆治理、中國邊疆研究史以及中國邊疆學理論框架構築領域研究。1978年以來,獨著、合著、主編、合編學術著作、論集、資料集7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300余篇,策劃、主編叢書及學術專欄20項,在國內外學術演講300余次,獨撰或合撰調研報告200余篇,主持或承擔國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省部級研究項目30余項,培養博士生6人。
(作者馬寶珠係光明日報高級編輯,原標題:馬大正:默默治史一甲子 唱響學術三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