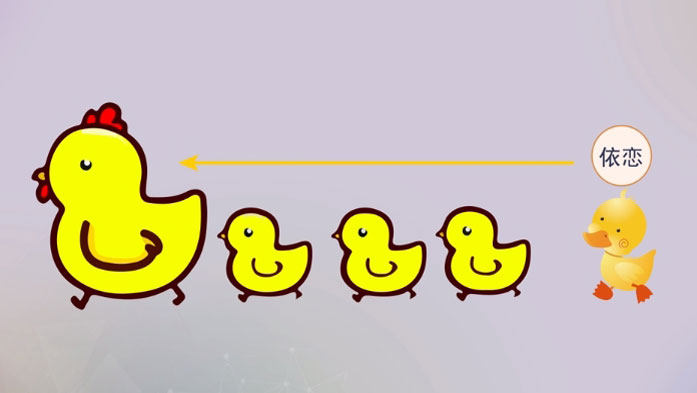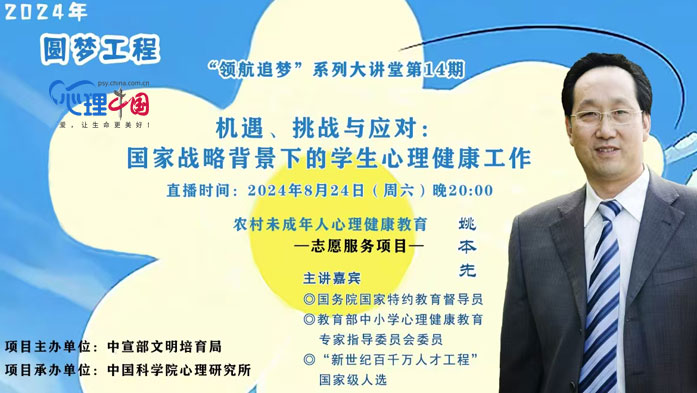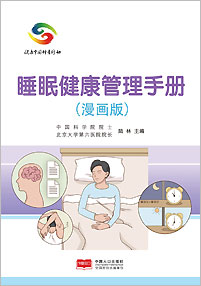開學在即,看抑鬱症的家庭又多了|走近抑鬱的少年
發佈時間:2024-08-29 11:25:11 | 來源:中國網心理中國 | 作者:莊勝春醫生:“你最近怎麼樣?”
女孩(12歲):“我越來越討厭我的父母和老師。”
女孩(初二):“好多了,因為做了兩次家庭心理治療。”
女孩(初一):“復診第三次,9月份去學校。”
醫生:“開學之前再來一次吧。”
8月下旬,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門診,人又多起來。

來自全國各地的家長,把困惑塞滿這間七平米的診室:
“升了初中後,學習壓力大,不想上學,寫字拖拉,跟大人發脾氣,老愛看手機。”
“一説話,他就急,看見我就像仇人一樣。”
“他最近半年一直在家,現在這種情況,上學有沒有問題?”
“這樣是不是要終生吃藥?將來還會回到正常的生活嗎?”
“我的孩子,到底怎麼了?”家長們不知道,早在來門診前,抑鬱的隱患可能已經埋下兩三年,甚至更長時間。
快開學了,央視新聞《相對論》記者莊勝春蹲點青少年抑鬱,走進十幾個被困住的家庭,一起求解——
青春期情緒風暴
“一上學,就這兒不舒服,那兒不舒服。”何凡是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主任,二十幾年的從業經歷,讓她看見青少年心理疾病背後,未能及時更新觀念的龐大家長群體,“家長們常和孩子説的就是,你老説你心情不好,我又沒少你吃沒少你穿,我平時也沒少給你花錢,你還心情不好,你憑什麼呀?你別矯情了。”
她帶著我們,來到兒童精神科住院部,80個床位,常年滿床,收治16歲以下的患者,最小的只有6歲。
不少孩子的小臂上,有著深淺不一的劃痕,“我每次就敢拿菜刀割一個地方,把別的地方割了,爸媽又罵我”。
一個初二女生寫下了給父母的14條建議,其中3條都是——“吵架時別帶上我”。因為,“父母鬧離婚時總會説,要不是為了你,我就怎麼怎麼樣”。

這些建議,是為家庭心理治療準備的——這是近年來醫院的新嘗試,醫生發現,只治療孩子,效果有限,得讓家長參與進來。
經過允許,我們加入了其中一場家庭心理治療。談話剛開始,父女倆就因為女兒要“養蛇、養蜘蛛”産生分歧。
爸爸無法理解,“家裏小,不適合養這種東西”。看著快哭的女兒,心理諮詢師羅愛宇問:“我在想,你這麼難受,爬行動物對你來説,意味著什麼?你願意説説嗎?”

圖: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病房,正在進行單個家庭心理治療。
女兒抹了一把眼淚:“家長經常不在家裏,我不能一整天都看手機,就跟它們玩兒,爬寵沒有動靜。”
停頓了一會兒,爸爸回應:“我平時很少在家,今年跟她媽媽離了婚,對她心理打擊比較大。”
原來,女兒最近升入初中,新環境壓力大,回到家又是支離破碎,“爬寵代替了一部分的陪伴。”羅愛宇告訴記者,每個家庭都有一個固定的相處模式,家庭心理治療所做的,就是打破這種模式,當問題呈現出來,對話開始流動,變化也隨著産生。
女兒:“每週多回來幾天,帶我出去玩,打個羽毛球也行。”
爸爸:“剛才説打球、散步,未來我會盡可能從後方支援,愛越來越多。”
女兒:“希望是真的。”
爸爸:“假不了,你得重新認識爸爸。”
2021年,由北京安定醫院牽頭的中國首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發佈。調查選取了北京、遼寧、江蘇、湖南、四川五個省(市)的約74000名兒童青少年作為樣本。結果顯示:在6~16歲在校學生中,精神障礙總患病率為17.5%,其中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佔6.4%、焦慮障礙佔4.7%,對立違抗障礙佔3.6%、抑鬱障礙3.0%。
相對這一比例,公眾對於青少年心理問題的認知,還相當有限。

圖: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病房,心理治療師施道明正在帶領家長團體活動。
“青春期是一個充滿動蕩的階段,就像暴風雨來臨時。青少年階段,邊緣系統的腦區發展,成熟會更快一點,但是在前額葉皮層部分的發展會比較慢,所以我們經常説孩子的情緒會很突出,但是控制能力又很弱,這是有生理的基礎原因。”
除了家庭心理治療,北京安定醫院中級心理治療師施道明還給患者家長們開設了家長團體講座,教授一些相關心理知識——如何理解和應對青春期孩子的情緒等,也給家長之間提供相互支援和溝通的機會。
他反覆傳遞的資訊是——在情緒的背後,是一些沒有被滿足的需求。“孩子希望被理解、被尊重、被看見、被愛,而不是指責和評判。”
這些家長參與的活動,已經成為安定醫院當下重要的治療手段之一。在何凡看來,青少年心理障礙的高風險因素包括遺傳、社會環境、家庭關係、應激事件等,之所以這麼強調“家庭”,就是因為,家長的改變,是治愈孩子最可及,也最關鍵的一環。
掉隊的羊
18歲的許皓然,本應該參加今年的高考。但四年前,初三的他確診重度抑鬱。休學後,沒能再重返學校。
他是少有的,願意直面鏡頭講述自己故事的青少年抑鬱症患者。

在皓然的印象中,上小學前,家裏充滿著包容和愛。
但後來,“一定要考一個好的高中,好的大學,然後讀研、讀博,找一個好的工作……”似乎成了父母和自己愛的連接。
成績不好,會被爸爸打,關在家門外,哭著求媽媽幫忙,“她卻只是靠墻看著我,轉身離開,她不敢幫我”。
12歲,是青春期的分水嶺。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皓然父母離婚,他們對彼此不滿的情緒,疊加著皓然青春期的波動,如疾風驟雨——家,變得愈發“不安全”。
這些情緒壓力,需要一個出口。有些少年會進入一個病態追求成績的狀態,想通過成績好獲得愛和關注;有些少年則選擇自暴自棄,“熬夜、玩手機、打遊戲”,和父母對著幹,表示“抗爭”。
疫情期間,皓然滑向後者。當他再次回到學校,已是初三,緊迫感和無力感包裹著他,“我當時是沒法呼吸的,像把我團成一個團,鎖在一個箱子裏面,一點一點把箱子裏的空氣抽出去。心臟不停地跳,不停地跳,窒息。”他哭著打電話給媽媽,“每天在學校,快崩潰了”。
接下來,皓然走向了和其他抑鬱嚴重的孩子相似的經歷:請一天假,請一週假,到長時間不去學校,最後休學、複學、再休學……四年裏,他沒能再上學。
藏在漫長成長時間裏的裂縫,徹底崩塌。
確診那天,爸爸對皓然説“你不上學,待在家裏,你的人生就廢掉了,你這輩子就完了。”
在皓然父母這一代的成長經驗裏,烙著那個時代的最樸素認知,“只有上學,才有未來。”
“我是不是個廢物?我的人生是不是完蛋了?”皓然開始自我懷疑,自我攻擊,“當時我每天沒有活下去的動力,就在想我明天為什麼要活著?”

圖:2020年剛生病的皓然
父母分開後,皓然和媽媽同住。母子倆的爭吵和衝突,持續了一年多。
“我沒法控制我的情緒,以及我對未來的恐懼”。每次聽媽媽提到“回學校”三個字,都像點燃了皓然情緒的炸藥,“我是有動手打她的,好幾次,甚至我掐著她脖子把她按到墻角”,“她也很絕望,説你就掐死我吧,我也不想活了。”
每次動完手,他會後悔,“我為什麼要動手,我怎麼控制不住自己,我是不是就是一個混蛋,一個瘋子,一個十惡不赦的人”,但他不曾把愧疚告訴媽媽,只是埋在心裏。
最糟糕的情況,是衝動自殺。
皓然輕生前的導火索,是一件他現在想來再平常不過的小事,他因為外人的一句話和媽媽起了爭執,沒能得到理解,這讓他想起了在學校被老師誤會時,也沒有得到媽媽的支援。
“我覺得站在了世界的對立面,是被世界拋棄的人”。皓然在床和紗窗之間,來回走了三次,每次都希望有人過來敲敲門,“後來我就跳了下去”。
萬幸的是,家裏樓層不高,皓然只是腰部骨折。但這次衝動也給他留下了後遺症,不能久坐。
讓人意外的是,皓然回憶起這段經歷,“如果再來一次,當時的我還是會自殺。因為那時我孤立無援,學校的不認可,父母的不認可,身邊沒有任何一個人認可。但是現在的我不會。”
“孤立無援”,是許多受訪的患者都提到過的一個詞,但“孤立無援”的,不只孩子。

皓然媽媽,是我們這次遇到的,唯一一位同意面對鏡頭的家長。
家裏的墻上,挂滿皓然5歲時的畫,書架上擺著生病前母子倆的合照,拐角處的白墻有筆印標記著不同年月皓然的身高……
“他整天關在自己的屋裏,一直在睡覺,不説話,不吃飯,連遊戲都不打”,回憶起兒子生病期間的狀態,皓然媽媽覺得“天塌了,我的孩子怎麼説躺下就躺下了。”
“我們那一代是通過上學出來的,你會讓他去複製那條路,他上學不好,你覺得他的一生就完了。”曾經的期許,被皓然媽媽比喻成“一個羊群”——大家都在往前跑,前面就是好學校、好工作、好未來。本來還能在中間跑,跑著跑著,突然間徹底骨折了,就是絕望,“這孩子,你怎麼就不能起來了,你怎麼就病了?”
“那時,我都是淩晨遛狗,因為我也睡不著,我就看房頂,哪個頂樓上……”坐在她的面前,很難想像,過去四年她經歷的生活崩塌。
如果孩子和父母,都如此痛苦,問題出在哪?
“快點快點”
8月,我們跟著皓然,來到青島,參加了一個由近50個抑鬱症患者家庭組成的夏令營。
第一天的課堂上,家長們做了一個“遊戲”。心理諮詢師呂軍生,請十幾位家長按順序説出——“在這個年齡段裏面經常跟你孩子説的一句話”。
快點快點。一代家長的焦慮,在一兩分鐘裏,變得具體。
“大家有沒有發現,從上幼兒園開始,後面沒有一個家長,向這個孩子傳遞感情。”呂軍生從事心理健康教育20多年,目前專注於心理困境青少年家庭的陪伴與支援,在他看來,家長身上被投射的社會壓力,日復一日地傳遞到孩子身上,這種壓抑,與成長中的被忽視、被誤解疊加,孩子承受不住,情緒就會崩塌。
就在上課期間,一對父母焦急離開。
他們的孩子突然離開營地,獨自跑到河邊,朋友説“80%不回來了。”父母擔心孩子輕生,焦急打車去尋找。在河邊發現孩子時,爸爸卻推著記者莊勝春上前,“你去你去,我不敢去”。
他們的兒子,今年19歲,初中時自殺過,有時,跟爸爸的關係像仇人。“我的性格比較急,從來不去傾聽孩子的聲音”。初中時,有一次孩子作業沒做齊,老師把作業本撕了,砸到他臉上,還有幾個同學搶他零食。孩子跟媽媽表達想休息一段時間,但是爸爸不同意,打了孩子一巴掌。
“你不上學,你不上學你幹什麼?”在做心理諮詢時回憶起當時的衝動,爸爸抬手擦淚,有些哽咽:“我很內疚……也很慚愧”。
夏令營裏,每一個家庭,都有相似的故事。
有幾位少年,主動找到我們,分享了自己被困住、又走出來的故事——

正在上大一的浪浪,患病3年,念高二時,整夜整夜睡不著,腦子不停轉,全是消極的念頭,“我很失敗”“我做得不好”“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牢籠裏面,不知道出路在哪”。對自我的負性評價,是抑鬱症患者典型的症狀。浪浪從小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少,“我一直病態的去追求成績,想要得到他們的認可。”

今年剛參加完高考的生椰西瓜,患病5年,“像我父母這一代,我爸就很焦慮。他小時候相當於是全家的希望。他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事,回家就會找我的茬”,“一言不合,突然抽個拖鞋飛過來,他就打我。”

KK是渡過青島線下營的輔導員,回憶起患病4年,父親的缺位,母親的焦慮,21歲的她忍不住一直流淚,“情況嚴重到我哥説,你實在不行,你別堅持讀書了,先離開這,但我不可能丟掉學業”。
患病5年,曾是營員的李翔宇,現在也成為了營裏的輔導員。他8歲開始缺失父母陪伴,在充滿不確定的人生中,“學習好是唯一我能抓住的東西。文言文默寫的時候,標點我都不希望它錯,錯了,我罰自己10遍,100遍去改。”他在高二齣現了軀體化症狀,看過各類科室找原因,“最頻繁的表現是一天我要上10次廁所以上,腹瀉,拉肚子,嚴重影響了我的上學,休學又複學,反反覆復,最後放棄了高考。”
但是,日常生活中,當孩子出現厭學情緒,父母很難辨別,是“矯情”“犯懶”,還是生病了?

“起碼你要了解孩子他是怎麼想的”,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主任何凡回應,青少年本身就是動蕩不安的年齡,我們要理解孩子本身是脆弱的,需要包容、接納、理解和幫助,“一般的心理問題積極處理後,可能就不是問題。如果心理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早期識別和干預,日積月累就成心理障礙甚至精神疾病了。”
無論是醫院,還是社會機構,如今都在試圖搭建一個過渡帶,讓患病的孩子重新走入人群,讓家長重新認知自己,認知孩子。
如何重啟人生
改變的信號,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
浪浪回憶起自己生病後,“我爸抱了一大堆書回來,有些很離譜,什麼‘10天治愈抑鬱症’。挺想笑的那一刻,我跟他説,咱們要相信科學”。但也是那一刻,他覺得自己被理解了,起碼父母開始和他站在同一條戰線。
後來,他的父母甚至主動幫他卸下了學業上的負擔:“我爸説,你放心去考,考到本科供本科,考到專科供專科,沒考上也沒關係,咱們讀職高”。
浪浪的家庭支援系統,建立了起來。放心往前衝,後邊有人給你兜底。
對生椰西瓜來説,有幾件“特別重要”的小事——媽媽撿起了她看不下去的CBT(認知行為治療)書,想學完幫助女兒;總是讓她緊張的爸爸,陪她一起救了一位吞藥自殺的同學,“我爸意見跟我一致,衝到她家裏,把她從一堆嘔吐物中抓起來,送到ICU”。
生椰西瓜有些害羞,“現在爸爸媽媽在我睡覺前,都會過來抱抱我,親親我,他們會懊悔説,要是在那個時候有這方面的宣傳,就不會耽誤我那麼多年”。
主要照顧翔宇的,是姥姥姥爺。多次休學又複學的經歷裏,姥姥姥爺做到的是,在他又跌下來的時候,穩穩地接住他,不推他去上學、去運動……而是默默照顧,每天給他備好飯菜。對翔宇來説,這是一個“微弱的確定性,但很重要”。後來接觸許多病友,他才發現,“能給到這樣支援的,很少”。
“回過頭來看,當他從小學習遇到問題時,需要別人的幫助。但我們只是在對他的成績表達情緒,給他要求,而不是真正的幫助。”對成績的焦慮讓皓然媽媽忽略了孩子的情緒和感受。
孩子不能上學,“我看到的是我多麼痛苦,孩子生病了,跑不到前面去了,怎麼辦?”在皓然生病很長時間後,她才學會,什麼叫共情。

一天,她在房間崩潰大哭,皓然聽見後,走進來坐在床邊,用手撫摸著她的後背,“我知道你難受,沒事,我在”。那一刻她意識到,原來,“共情,是你能感受到我,不是告訴我這件事用ABC三種方式。”
不用抵抗媽媽的焦慮,皓然也開始有力氣建立自我,“在她不理解我之前,我花80%力氣在跟她抗爭,你憑什麼不允許我,你為什麼不允許我,但她允許我的時候,我可能就花20%,其他的力量在積蓄我自己的能量。”
“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學生成長環境不斷變化,疊加新冠疫情影響,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更加凸顯”,2023年4月,教育部等十七個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堅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完善全面培養的教育體系,推進教育評價改革”,“貫穿學校、家庭、社會各方面,培育學生熱愛生活、珍視生命、自尊自信、理性平和、樂觀向上的心理品質”。

圖:許皓然在千島湖拍攝的滑翔傘,“雨過天晴,彩虹出來,就像我現在的狀態”。
休學後很長時間害怕出門的皓然,如今,可以走出家門,他愛上了攝影,會在朋友圈分享拍攝的照片。他也像媽媽一樣,開始學習心理學,準備參加自考。
“我想把孩子重新埋到土裏去,他身上有很多創傷點,那我就重新養育他一遍,風大了就給他遮遮風,雨大了給他打把傘,我在旁邊就看著,陪伴,讓他用自己的力量重新再活一遍。”
關於“掉隊的羊”,皓然媽媽也不再害怕,“升學,不是人生唯一的一條路。人生是一種體驗,每個人的速度、幅度是不一樣的,你把自己放到一個更長的時間段,會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也在其他患病的孩子身上生長出來。
9月,KK即將前往匈牙利上大三,她選擇了心理學專業。
生椰西瓜的大學生活也即將開始,她選擇了醫學。

圖:2024年6月,翔宇完成心理諮詢專業學習,順利畢業,與老師合影。
而當年沒能參加高考的翔宇,後來上了一所大專,讀心理諮詢,今年6月以專業成績第一畢業,走向社會:“哪怕未來,再次陷入低谷,我還是有信心,慢慢來,去撐過這段苦日子。”
2018年,翔宇曾在一條視頻下留言:“19歲的我重度焦慮抑鬱,希望能夠在未來站出來,讓大家消除病恥感”。
經歷了青春期的“情緒風暴”,一次次跌落又爬起的少年,關於“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或許找到了一些新的答案。
(文中浪浪、生椰西瓜、KK均為化名)
寫在最後
如果此刻你正在經歷抑鬱的低谷,
周圍暫時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希望你再給自己和世界一個機會,
試著撥打一個電話,
和電話那頭的陌生人説説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