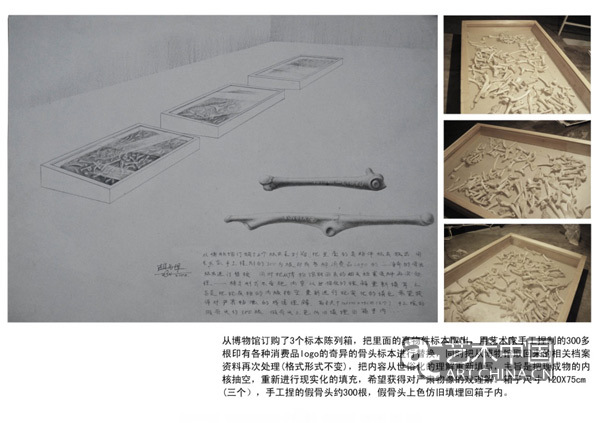和麗斌:現在的社會不需要極端,社會需要什麼,産生什麼。
陳長偉:那天我跟蘭慶星聊起何雲昌的作品,我説我還是蠻喜歡的,他就説他不喜歡,因為何雲昌走的很極端,這種極端會引起很多問題。比如席特勒,他就很極端,這種極端就很可怕。他説藝術越成功,它鼓勵的極端方式就越多。比如行為藝術中,把自己困在水泥中24小時,出來的時候身上被劃上了2000多個口子,這種極端如果被鼓勵,就會走入偏激。我忽然覺得蘭慶星的想法確實很好。藝術家其實就是在精神藝術引導下往前走,應該在現實之外獲得一種更飽滿的引領情緒。如果像那樣的極端,必然會干擾一部分人對生命的理解。我覺得他這種思考讓我很感動的。
薛濤:極端要分兩説。從創作語言上來説,沒有極端,不可能發現一種新的方式。而新的方式是可以給我們産生某些借鑒性。都中庸的話,藝術語言上是匱乏的。
向衛星:這就是藝術的包容性。它成為了一種藝術家的分類方式,有的藝術家極端,有的好中庸。這和你喜歡那種藝術家的畫一樣。這樣藝術才好耍。
陳長偉:我更喜歡中國傳統書法的那種在前人基礎上,一點點往前走的感覺。
和麗斌:其實具體到個人,是藝術家個人的選擇問題。也有這種,生活裏很中庸,作品裏很極端。或者是生活上很極端,作品裏很平庸。這在藝術上是可分的。
陳長偉:可能因為他在生活裏是平庸或者包容的,所以在創作時,表現出一種極端。也可能就是因為他生活裏太極端了,所以作品裏做的比較平庸。太多種了,每個人的選擇不同。有些人結合的比較好,有些人結合的不太好。大部分人選擇藝術更重要的選擇這種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沒有誰最初做藝術的時候目的就是打算賺錢的。更多的人是身心投入進去之後,被社會選擇、被市場選擇、被時尚選擇。
我深深地發現,他們都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在職業特色之外,他們同樣有著對生活的熱愛,有著自己看待世界的眼光,或感性,或理性,但和我們都一樣,帶著問題,在這個或煩瑣,或嘈雜的世界裏,找尋著自己內心的世外桃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