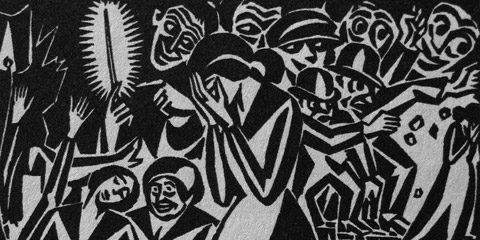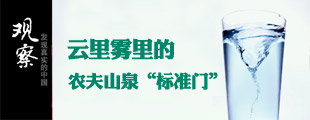聚焦
由於《富春山居圖》中“雷點”太多,開啟了自微網志等“自媒體”興起後幾乎最大規模的全民歡樂吐槽。自該片上映以來,吐槽這部電影簡直成了今年端午節的全民活動,不少影迷相互打招呼時紛紛選擇用“今天你發影評吐槽‘富春’了嗎?”許多影迷抱著十分好奇的心態去影院“膜拜”這一爛片,而後則紛紛表示想掐死自己的好奇心。
通常只需要有個靶子,具體是誰不重要

就算沒有《富春山居圖》,還會有別的“圖”來滿足大眾的惡趣味。網路上從來就缺少不了被千夫所指的“紅人”,借著這股罵名的東風,只要有足夠的心理素質和大無畏的不要臉精神,“紅人”們都可以過的順風順水、臭名遠揚。
當然並不是所有在網路上遭致吐槽的東西都跟“富春”一樣一無是處,每年的春晚就是一個屹立不衰的中國好靶子。春晚的文化水準可以説是當代中國的代表,從節目的內容形式到硬體聲光電的整體配備,很難找到比它更高水準的晚會製作。同樣是隨著微網志的興起,拉動了全民在三十晚上吐槽春晚的歡樂事,吐槽春晚似乎比看春晚更有趣、也更重要。
前有春晚,後有“富春”,在品質對比下,可見吐槽並非完全因為作品的“爛”,它既有可能由於全民發泄的心理需要,也可能由於那些所謂的文化工作者對觀眾底線的不斷挑戰。關鍵是社會應該如何看待這些現象,在現象背後,我們是否能看到吐糟的真正隱喻。
我們可以因國産電影的竟然能如此之爛痛心疾首,當然也可不必緊張地説我們還有能拿奧斯卡的李安。[詳細]
娛樂節目從捧星時代到虐星季

《星跳水立方》和《中國星跳躍》等一系列的明星跳水節目致傷致死的新聞不斷,這讓香港電影明星黃秋生憤慨地説,讓明星去跳樓,收視率更高。跨界明星秀跳水,觀眾如何看?答案在節目未開播之時已經揭曉:觀眾看明星跳水,一定會以娛樂心態來看。以娛樂心態看明星跳水,其實已與競技跳水毫不相干,而明星跳水的種種窘態只能被無休止地放大、被不厭其煩地“消費”。
以跳水之名做秀,中國跳水收穫的是什麼?有人説,跨界明星秀跳水,人們看的終究是明星,而不是跳水;也有人説,以自我娛樂精神推廣已經越來越小眾的中國跳水,未嘗不是一種選擇。客觀地説,跳水界能夠擺脫金牌思維定式,放低身段尋找推廣路徑,已是一種進步。但問題是,將一個項目的推廣更多維繫在一檔從國外照搬過來的綜藝節目上,似乎並不高明,更不是長久之計。
跨界明星秀跳水,主辦方和明星要的是什麼?對於主辦方來説,選中跳水打造跳水真人秀,要的或許就是專業跳水與跨界明星因為不相容而産生的巨大反差,這種反差可以以勵志為名製造話題、可以以明星出糗博取眼球。而跨界明星為何明知出糗還要迎接“挑戰”?令人信服的答案可能不像節目自我標榜的公益那樣崇高,借助標新立異的綜藝節目提升曝光度或許是更為現實的選擇。[詳細]
巧妙的檔期選擇和湖南衛視的平臺優勢,是《我是歌手》成功的“天時”和“地利”因素,而其“人和”因素,則是節目組對參賽者的遴選。
在過去幾年的草根音樂選秀熱潮中,那些五音不全的草根“唱將”以及靠各種雷人造型博眼球的參賽者,早已讓人們“審美”疲勞——這也正是中國選秀節目陷入“七年之癢”的關鍵原因。而《我是歌手》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精英化與專業化相結合的道路——參賽者無一不是經過節目組精挑細選的出道多年的專業歌手。[詳細]
這些節目的構成並非中國原創,清一色地是從國外購買的版權。可見在外國虐星時代已經開啟了不短時間,以購買美國《The Voice》版權而一炮而紅的《中國好聲音》,成功包裝了了一個明星與學員之間互相選擇的節目形式,而從南韓購買了版權的《我是歌手》,成為今年湖南衛視的最吸金節目,它以一個嚴酷的考核淘汰,成為了虐星季的一個溫和開始,而《星跳水立方》和《中國星跳躍》以傷殘甚至死亡將娛樂節目的虐星指數飆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在這種主動權的反轉下,明星在走下了神壇,但又矯枉過正地走向了深淵,觀眾們終於停住了幾十年的追逐腳步,當了一回上帝。無論是誰對誰的追逐,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地位的差異。當今的娛樂節目正是利用這種反差作為噱頭來擠壓收視率,而我們要看到的是,同為一個個人的明星與觀眾本無差別,作為文化的輸出者和文化的消費者,二者本應站在一個同樣高度的平臺,而非誰來仰望誰。[詳細]
至死不休的娛樂形式謀殺了文化內容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讓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就是把文化變成一場娛樂至死的舞臺。這一觀點來自尼爾•波茲曼的著作《娛樂至死》。
讓文化成為一座監獄,用我們熟悉的話叫做“文字獄”。當“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成為一個足以殺頭的罪名時,文化精神就已經在殫精竭慮中被謀殺了。
而讓文化全權成為一種娛樂手段,文化精神的枯萎則是在悄然中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這個過程不易察覺又充滿了刺激與快感,像一場鴉片戰爭,等人們恍然醒悟的時候,太多東西就已經腐朽得無可救藥了。
與《娛樂至死》寫作的背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美國社會——不同,如今的地球村式的文化聯姻氛圍中,具體的內容已經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無論是政治、宗教、經濟、體育還是文化,我們早就已經熟絡了將一切“正事”娛樂化的手段,諳熟了如何挑逗讀者與觀眾,讓一切看起來都那麼“有趣”。當波茲曼提出“娛樂至死”後幾十年,我們發現娛樂至死仍然不休。[詳細]
碎片化時代需要文化認同感

當一切以娛樂的方式滲透,文化的存在形式也讓在變化中讓人匪夷所思。微網志帶來了娛樂新時代。為什麼明星的微網志就算是水文不斷也有成千上萬的粉絲轉發?為什麼明星就算不回復粉絲也有動輒百千的留言?
這與我們如今時代的文化呈現方式密切相關。網際網路的發達帶來知識的躍進與革命,同樣帶來了時代的個人主義和碎片化。從話語權的完全控制到如今自媒體的蓬勃發展,權力的分散勢必帶來了碎片化一切的文化現象。幾年前香港就已經率先發現,人們開始進入讀圖時代,許多小學生如果沒有圖畫的幫助無法理解簡單應懂的字面意思。個人部落格興起幾年後,被微網志擊了個粉碎,人們逐漸發現140字其實也有點多,喪失了閱讀能力的不僅僅是小孩,成年人們同樣已經不會使用長文。有時候幾個表情,一些網路用語就是日常生活的全部了。
這一切都可以算作是人類文明的進化,但是以人文精神的標準來衡量,我們失去的文化內容卻不是一星半點。
一種新文化的出現並不代表我們要拋棄舊的。可如今誰會踏踏實實每天讀幾頁書,安安靜靜地逛一逛博物館或者畫廊書店?實體書店的逐漸死亡除了電商的衝擊之外,更多的是人們對與文化認同的消逝。[詳細]
僅有3億人口的美國,竟有11.6萬座圖書館,每人平均佔有率世界第一。特別是在1.64萬座市立圖書館中,尚包括9000個中心圖書館和7400個分支圖書館,大眾化閱讀越來越成為美國公共政策的方向和基石。與圖書館相比,美國的博物館、音樂會、文化節和劇院之多、之“活”,在世界上可謂首屈一指。僅紐約就有400多座陳設內容各不相同的博物館。而在全國的大學中,也廣泛分佈著700多個博物館、3500多個圖書館和2300多個劇院。
華盛頓是美國的政治中心,這裡展覽館和博物館林立,特別是對中國歷代文化、文物和藝術製品的收集與展出,更是精品頻現。[詳細]
發達的科技和富裕的生活不應該成為擠壓文化生存空間的理由,相反,我們更注重對此領域的保護。當人們能夠認識到唯有文明的文化才是民族精神的內核時,不竭的精神源泉才能滋潤國家的成長和繁榮。
(編輯:楊公振)

《我是歌手》的實力依舊是有目共睹的。但或許連導演組也沒想明白,這檔節目究竟靠什麼留住觀眾。《我是歌手》的南韓原版在第一季也曾引發轟動,但從第二季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透過跳水真人秀,可以清晰透視體育界與娛樂界的尷尬混搭、綜藝節目與受眾群體的畸形互動。混亂格局是現實生態的真實反映,只是簡單評判對錯難以切實解決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電視綜藝節目如此熱衷“拿來主義”?什麼時候我們也能夠做出擁有自主版權的原創綜藝節目?長期以來,文化産業原創力不足的困擾,如今也傳染給了電視綜藝節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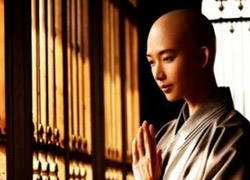
“逆行銷”成了這段時間內地影市的關鍵詞。在渠道甚多的環境中,一部電影的口碑好壞很快會傳播給大眾,可“富春”碰到的情況是:罵得越狠,票房越漲,只用了兩天就過了億元大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