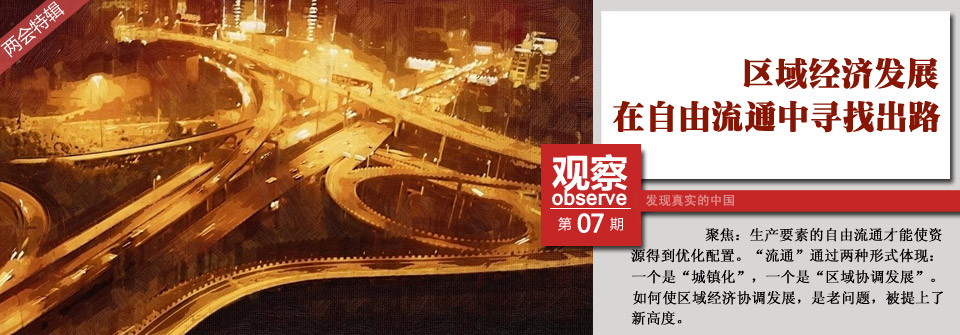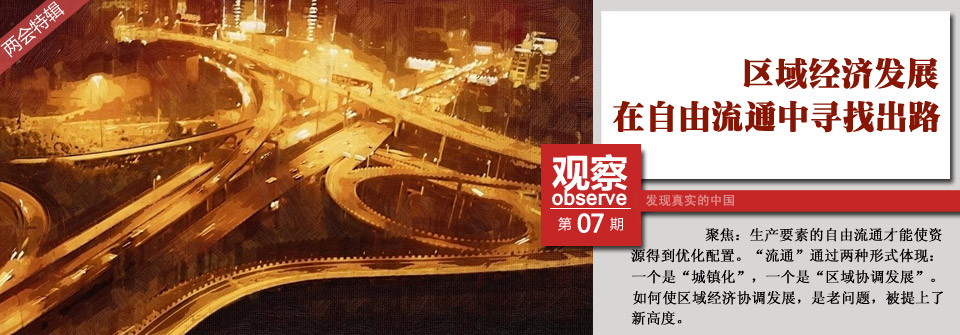| 不平衡是遺留問題,“特區不特”是新問題 |
在中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是一個歷史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儘管各地區經濟都在發展,但是有些省經濟的發展快於另外一些省,因此,地區之問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地區經濟不平街問題變得突出起來。究其原因,既有政府行為,也有經濟因素,既有歷史原因,也有地緣關係、自然條件等方面的差異。
而隨著全國性制度的不斷完善,各地的制度和政策在內容和水準上已經基本實現了“水準化”。特區原來享受的政策優惠、制度優勢(尤其是較少的舊體制負擔)被大大消解了,現在必須和其他地區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所謂“特區不特”表達的正是對這種現實的感慨。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空間形態上已經從局部的地點轉向了更大範圍的“區域”,單個城市要保持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必須依託周圍的地區,形成要素相互支援的發展區域。如果説第一個挑戰説明瞭特區在整個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定位發生了調整的話,那麼第二個挑戰則體現了特區與周圍城市之間關係的變化。特區頭上的光環正在消退,其功能也需要重新的定位。[詳細] |
| 最遙遠的GDP距離不是總量,而是“每人平均” |
為了落實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近些年來國家比較密集地出臺了一些區域性的規劃和指導文件,目的是使區域發展的指向更加明確,戰略格局更加清晰,支援的政策能夠更加完善,從實踐來看是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在不斷趕超,但是每人平均GDP方面,最低的省份貴州的每人平均GDP只相當於最高省份天津每人平均GDP的五分之一。
經濟發展差距必然導致收入水準的差距,並最終形成生活水準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兩者具有趨同性。但是,由於各地區經濟發展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及人口流動程度不同,兩者又不完全同步。發改委副主任杜鷹表示:區域差距不是指的GDP總量,指的是每人平均GDP,只要分子GDP往西邊去了,分母人往東邊去了,自然差距就會縮小。[詳細] |
| 突破口在於找準各地的“比較優勢” |
李承鵬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裏提到:在美國,如果想從政你可以去華盛頓,搞金融可以去紐約,演電影可去洛杉磯,做工業就去底特律,如果你什麼事情都不想做可以去新奧爾良聽民間音樂。連我們不太看得起的義大利,也分時尚之都米蘭,工業之都都靈,或者去羅馬當個考古學家……
而在中國,人們尋找夢想和機遇,全都涌進北上廣。究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的區域特色沒有發展起來。東部地區不僅資源集中,機會、教育、交通等都優於西部,人們會自然向發達地區流動。如何把區域的特色優勢發揮出來是統籌區域經濟發展的突破口。
事實上,今年以來國家批准的各地區域規劃都在爭相主打“比較優勢”牌。特色經濟的發展對地方經濟發展貢獻較大,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尤其在我國老少邊窮地區的脫貧致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國不少老少邊窮地區往往是特色資源相對密集地區,在經濟發展大潮中,這些地區為了加快脫貧致富的步伐,依託各地資源特點和自身優勢,發展了一批市場強勁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産業,發展了本地經濟。[詳細] |
| 更要實現“人”和“資源”的自由流動 |
每年的春運,就是中國人的最大規模遷徙,這樣的遷徙意味著人和資源在區域間的流轉。區域之間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使中西部之間的要素能夠流動,東部的産業可以向西部轉移,西部的勞動力可以到東部去打工。
長期以來,我國流動人口主要聚集在東部沿海一些大城市、加工製造業産業聚集區,珠三角地區尤為密集。近兩年,流動人口在全國流向呈現三個趨勢,一是開始由東部沿海向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分散;二是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始由珠三角向長三角,再向京津等北方地區流動;三是在一些省區內,流動人口開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
在我國,要素流通的“壁壘”表現為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下的行政分化所導致的市場分化和市場封鎖。今年的兩會第一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到‘自由遷徙’這個詞。讓人員和資源能夠以市場為背景自由的流動,只有在流動中才能實現比較優勢的轉換,也才能縮小區域差距,才能使資源得到優化。[詳細] |
| 政府角色:調節規劃為主,提供服務為輔 |
中央政府和政策制定的具體部門,在分解和細化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切忌只靠紅頭文件層層下壓。政府頂層設計應該找好位置,還原市場的主導地位,從制度設計上為生産要素的自由流轉掃除障礙。同時還應該注意,對欠發達地區,政府應該提供與發達地區平等的基礎服務。
在市場經濟過程中,地方政府有一個角色轉換的問題,因為過去在計劃經濟過程中,經濟發展是靠政府來組織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也承擔了組織經濟發展的角色。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地方政府的角色也適時的轉換,首先地方政府應該把社會事業發展放在一定的地位。比如投資環境的改善。因為我們經濟發展主要是以企業為主體,投資環境如果改善的話,僅僅靠優惠政策,短期內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從長期來看,投資者可能不滿意,也不願意來,所以政府工作應該轉到如何改善投資環境。
投資環境分為“軟環境”和“硬環境”。所謂“硬環境”包括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建設,還有一些生態環境。“軟環境”,是政府對企業的服務問題,另外就是法制建設問題。政府的角色要轉到公共服務上。比如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基本福利、社會保障,對弱勢群體的援助,還有文化道德的建設,體育事業的發展。這些方面,一方面使地方的文化和社會風氣有更大的改善,第二方面也有助於投資環境的改善。[詳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