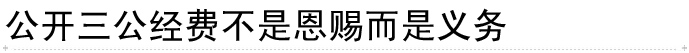
凡使用公款者,必須公開三公經費
2006年,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學習時報》發表文章,針對政府公務開支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數據:三公消費9000億,公車消費4000億左右,公費出國是3000億左右,公款吃喝2000億左右。雖然不斷有人對9000億提出質疑和修正,但它依然是關於政府“三公消費”被轉載得最為廣泛的數據。如此過度的公款消費很容易引起群眾不滿,影響和傷害政府威信。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吳丕接認為:“只要花的是國家的公款,就都應該公開支出,接受百姓監督。”除了國家規定的不公開的一些涉密部門,從原則上來講,只要是花公款的單位,無論是中央或地方,都應公開。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認為,《政府資訊公開條例》第九條規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需要社會公眾廣泛知曉或者參與的,行政機關應當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三公”經費的根本源頭來自於納稅人的稅收,這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政府部門機關當然有義務向社會公開。
法治藍皮書《中國政府透明度年度報告(2011)》的主筆人、社科院法學所的呂艷濱坦言,目前很多行政部門包括國務院某些部委機關,都把“依申請公開”和“主動公開”的範圍完全割裂開來,但行政機關不能以政府資訊屬於“主動公開”的內容,來拒絕公民的“依申請公開”請求。
怠慢公開三公經費者,必須問責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稱,當前中央各部門在公佈“三公”經費時存在的不足,反映出我國許多政府部門普遍存在的一種問題——“權老大”的意識還很強,排斥社會監督,特別是一些部門一把手的法律意識仍比較淡漠,有時甚至完全無視法律的明文規定。
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也曾指出,國務院只是要求中央部門于6月底公開“三公”經費,而沒有相應的約束懲罰機制,在各部門不願公佈的情況下,必然使得這條政令變成“稻草人”。所以,從維護政令權威的角度,國務院應將沒有按照要求按時公開“三公”經費的部門名單對外公示,對其譴責,並適時啟動問責。
對拒不公開的問責至少包括三個層面,一是行政問責,二是司法問責,三是民主問責。這其中,關鍵又在司法問責與民主問責。此次國務院自上而下推動“三公”經費公開,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以拒不公開或消極公開應對,實則既惡化了官民關係,又損害了中央政府權威。為保障政令暢通,行政問責必不可少。否則,“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成為既定現實,勢必帶來權力割據。
公佈三公經費別玩弄技巧
“週末情結”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新聞關注度避峰就谷現象,政府部門公佈“三公”也不例外,大家給勞累的心放一個假,自然不再去關注新聞,不再去憤世嫉俗了。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公佈三公靠所謂的“技巧”諱疾忌醫,恐非明智之舉。
公開“三公經費”,無疑是向老百姓公開。但是,老百姓到底能在哪看到這些公開的資訊呢?有些部門公佈的“三公經費”資訊很難直接在其官方網站找到。甚至借助搜索引擎也無法查詢到相關資訊。

保證數據真實可靠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呂艷濱副研究員將公眾的迷惑歸因于目前“三公”公開的標準、內容、範圍、方式方法等沒有統一和規範。他認為,這樣的公開還不能讓公眾清晰、明瞭地判定該部門經費支出的詳細核算標準、開展有關活動與本部門履行職責的關聯度、必要性和實際取得的成效,因此也就很難判定這些經費的支出究竟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真的取得了應有的績效。知情的目的沒實現,勢必遭到公眾的質疑。
光靠當事部門做“王婆賣瓜”似的解説,顯然不足以釋疑解惑,因此不妨借98個中央部門公開“三公”經費這個東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請國家審計署大張旗鼓地進行專項審計,既能懲戒和防範在此事上敷衍了事、做花賬的行為,又有助於把公開“三公”作為規範政府部門行為、梳理管理職能、轉變工作作風的一個有效輔助手段發揮更大作用。
公開口徑應當統一
國務院要求中央部門公佈的“三公”經費只限于財政撥款的部分,而在各部委的相關支出中,財政撥款僅是其中一部分,其餘事業收入、預算外收入等非財政撥款中,往往隱含著更大的三公支出空間。特別是在很多實權部門,財政撥款之外的行政收費、尤其是各單位不納入財政預算的“小金庫”往往是“三公”消費的重要來源。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質疑,在這樣一個狹小而模糊的“三公”標準之下,中央機關發揮聰明才智,自己去理解“三公”的標準,於是出現了畸高畸低的數字。比如,什麼是“公務用車購置及運作費”。此前北京公開了公車數量,但採取的是最小口徑: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黨政機關、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公務用車實有數為62026輛。這個數字立刻引起公眾的質疑。而廣東有關方面曾指出,公務車是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國有股佔50%以上國有企業、中央直屬和外省駐粵單位購買的公用小汽車,類型包括旅行車、小轎車、吉普車和微型廂式車等。那麼,這次中央機關公佈的公車經費,是按什麼口徑統計的呢?
公開數據更加細化
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後李長安分析認為:
一是各單位在職人數,這是個最基本的數據,沒有它三公支出數據根本沒什麼意義。
二是三公支出佔行政支出的比重和佔整個財政撥款支出的比重,從這個比率才能看出三公支出是高還是低。
三是要按照支出功能分類編制三公支出預決算表,這樣才能反映政府各項職能活動中三公支出的多少。
四是除公佈預算數據外,還應公佈三公支出的編制原則和控制標準,這樣才能分辨預算編制本身是否合理。
五是要對三公支出的各項做明細説明,比如因公出國有多少次組團,多少人次,主要是參加什麼活動;公務車購置和運作費中購置費是多少,運作費是多少,有多少臺車,均價是多少;接待費中接待來訪花費多少,業務工作花費多少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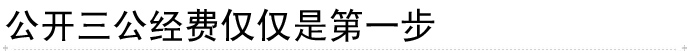
三公經費公開得讓民眾看得懂
多數部門公開的三公數字通通是所有的費用總額,叫人讀起來好比天書,看不出其中的名堂。殊不知各部門所公佈的並不是“三公經費”核算的唯一賬本,有選擇性的公佈賬本也是降低風險的最好方式。積極推進經濟民主的吳君亮此前提到,政府目前編制預算是同時採用兩種方法編制兩個賬本,一個賬本是按功能支出編制的,也叫功能支出賬本,大致就是目前各中央部門所公開的。另一本帳則是經濟支出賬本,按經濟支出分類來編制,包括具體的支出明細,比如汽車、房租、培訓等納稅人最需要了解的項目一覽無余,這個成熟的賬本編制,財政部了解,各部門自己了解,可是納稅人卻沒有機會了解。
那麼,預算帳單究竟如何才能讓人看得懂?雲南省財政廳廳長陳秋生認為,“三公經費”公開的關鍵,是所公佈的科目要細化。我國預算科目設“類、款、項、目”四個級別,此前公佈的預算報告多數公佈到“類”和“款”,具體的各種行政開支從中看不出來,應當公開到“項”甚至“目”,並做出相應的解釋説明,讓公眾一目了然。
全面構建多種監督途徑
“三公經費”並不是單純的公示問題。公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讓政府支出更節儉、更合理、更透明,實現從源頭上對預算進行制度性壓縮,節省行政經費開支,減輕納稅人的負擔。
改進預算編制的辦法和程式、健全監督體系、建立問責制度等,都是“三公經費”的制度“籠頭”。通過對比“三公經費”的多少及其效果,也可以同步考察政府部門是不是管了不該管的事,是不是應當讓渡某些職能,從理順職能方面促進“三公經費”的公平公正。只有不留死角的公開,才能實現有效的監督,真正衡量出行政成本的高低及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