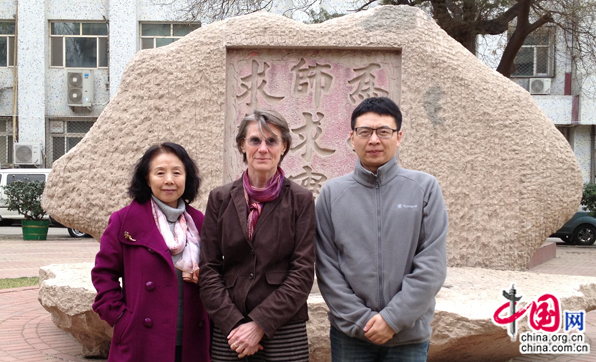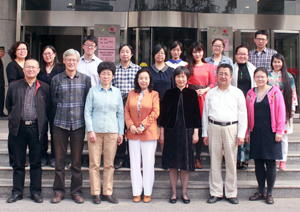實錄

王紅旗
中德兩國“女性和職業生涯”的現狀
王紅旗:尊敬的謝妮教授好!非常歡迎您來我校,來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了解中國女性與職業生涯的現實情況。我們的研究中心成立於2000年,在國內也是唯一的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2010年成為中國女性文化研究基地。我們的研究中心主辦兩種媒體,一份傳統紙媒,為《中國女性文化》學刊,一個與中國網(國務院新聞辦外宣網站)聯辦的新媒體,為“中國女性文化論壇”。主要內容包括女性社會文化學、女性教育學、女性文學藝術等理論與實踐方面的考察研究。無論學刊還是論壇,對各界職業女性的生存發展狀況,均從社會制度與文化觀念層面對女性職業生涯的不同影響,做過諸多專題的研究。主要是從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制度建設,以及愛情、婚姻與家庭的價值觀,男權傳統文化的刻板印象,社會對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來探索對女性職業生涯發展的不同影響。經過考察女性職業發展的實踐經驗,發現其精神思想方面的成長訴求。 2003年,在與美國全美女總裁協會舉辦的《一場中美女性生存命運現狀的討論》座談會上,我首次提出職業女性“無國界的性別玻璃頂”問題,當時的全美婦女組織董事會主席瑪莎•伯克教授,美國文化革新中心主任朱迪斯•L•懷爾特,美國婦女政策研究所主任海迪•哈德曼,還有秘書張林西,國際女性發展促進會會長劉誕麗女士等等,都認為女性的事業和愛情、婚姻與家庭角色三重困惑,是全世界女性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我認為,對“女性與職業生涯” 項目研究,具有全球性和現實性,以及未來性意義,很願意和您共謀建立中國與德國“女性與職業生涯”的比較研究項目策劃,從法律、政治、社會、心理、文化等方面,對中德兩國女性生存與發展的經驗,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歷時性對比梳理,探求在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明模式裏,相異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同的女性解放路徑,卻有著相同的精神訴求,從而揭示女性生存發展研究的人類性價值。尤其是,在當今全人類遭遇精神生態、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多重不同程度的危機與挑戰之時,我們兩國知識女性、高校女性研究學者如何攜起手來,以考察研究中德“女性與職業生涯”課題為起點,以兩國女性精神生命的思想重建,為國際女性的生存發展政治經濟體制完善提供有價值的政策參照,而參與到完善人類心性、建構新文明的進程中去,從而推動人類心性的健康完善與世界和平事業。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女性的社會良知與責任擔當,女性意識與人類意識的合二為一。
謝 妮:完全同意。“女性與職業生涯”在德國是一個非常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問題。一方面預計在不久的將來會面臨高品質員工缺乏的現狀,而多元化能夠促進企業的成功,此項目希望在促進社會性別問題上能夠更加平等。另一方面,事實表明,對於年輕的媽媽們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希望通過制度改革來提高女性/母親的就業機會。在項目開始,我們想在中國考察這一情況,並在法律、政治、社會、心理幾個方面與德國對比。這將成為不來梅科技大學一個專題研究的主題,這一專題研討會將成為中德雙方在此問題上的起點。王紅旗:非常感謝。以具體的課題項目為起點,組織多方面的研究資源,就會更具有強大的力量。我們曾經策劃過幾次這方面的項目。比如2003年出版了女性社會焦點問題系列叢書:《中國女性在演説》《中國女性在對話》《中國女性在行動》《中國女性在追夢》,講述的就是女性生存發展的三困惑,我把它叫做女性生存發展的三大困惑:事業與愛情、婚姻、家庭之間的矛盾衝突。也就是你説的“女性與職業生涯”之間的矛盾對女性事業發展的影響。我尤其關注女性和職業生涯方面問題,曾經與中國中央電視臺的《半邊天》節目、北京廣播電臺的《星空下的女人》節目、人民網的《情感時空》欄目合作,,現在正與中國網聯合主辦《中國女性文化論壇》欄目,關心下崗女職工的再就業,女博士的事業與愛情婚姻家庭困惑。還曾舉辦中美女性發展經驗高峰論壇,中國與美國30位女企業家相互分享她們家庭幸福、事業成功的經驗故事,赴蒙古國在總統府與其女法官協會舉辦國際女性文化論壇,還對中國的女奧運冠軍這個特殊群體的職業生涯做了研究,出版了研究報告《巔峰之道》。 謝 妮:你們做過的研究非常特殊。是非常有意義的,你有好多好的想法,而且很有規劃性的,很完整。王紅旗:向您介紹了我們的情況之後,很想請您談一談現在德國職業女性的情況。因中國政府力倡男女平等政策,中國的女性解放是“自上而下”的,而德國女性解放卻是“自下而上”的,那麼,德國知識女性的職業生涯面臨什麼樣的具體問題?請談談您的看法。
謝 妮:這個可以説。我覺得女性解放或者這不是我的專業,我也搞社會調查類型的東西,而且你説那個“自下而上”,我們有學生運動,我70年代上大學的時候也參加這些女性的組織,所以這是一個個人的興趣。後來就沒有具體的搞女性研究,還搞了一個小調查,在中國搞的調查,中國女性企業家,但是是外國女性企業家在中國,這是原來搞過。我就先説個人的好嗎?
我怎麼想到這個項目,我現在年紀大一點,還要工作,在大學可能還有5年時間。但是現在開始想,離休以後還可以繼續做一些對社會貢獻的事。我還有一個朋友,她在企業家裏面工作,她跟我一樣大,我們就想看看你們學校有什麼興趣,所以我就到這來了。其實,這是我們兩個人的興趣。她在企業家裏面、公司裏面知道好多人,我就在大學裏面知道好多人,我們雖然在不一樣的地方,但我們選擇的這個“女性和職業生涯”項目,是可以共同研究的。説起女性解放的歷史,德國的女性解放是早就開始了,20世紀初就有女性可以在政治方面有參政權。但是沒有很大的改革。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如果女性想在外面工作,應該爭得丈夫的同意才可以的。
王紅旗:有這樣的法律條文?
謝 妮:對,如果丈夫説你在家看孩子吧,那女性就不能出去參加工作。70年代還存在這樣的情況,這是後來才知道的。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女性因為丈夫在外面打仗,自己在家要看孩子,又要在工廠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的獨立性提高很快,大部分的女性都是有自己收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她們的丈夫回來了,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丈夫需要有工作位置,所以國家讓女人回家。另外經濟發展很快, 所以家庭一個人在外面工作, 收入經常足夠, 沒有必要女的在外面做工。可能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發展,跟中國的改革以後發展可以相比。
我是在50年代出生的,我長大的那個時候好像以後越來越好,這是我們這一代的感覺。那後來50年代很多女性在家看孩子,我的母親也在家,大部分女性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夠生活的話,都呆在家裏。
王紅旗:你説的是上世紀70年代?
謝 妮:這是50和60 年代的情況。現在女性應該出去工作,得去掙工資。
王紅旗:政府呢,政府對婦女的就業有沒有優惠政策,或者説,就是參加工作之後,是不是有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
謝 妮:有這樣的政策,這樣的政策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不太清楚。法律上一樣的工作得有一樣的工資,但是,有很多研究證明,女性與男性一樣的工作,女性的待遇比男性的差21%。這個數字很大。但是也有另外的情況,如果真正的高層也不一樣。因為,女性的工作跟男性不一樣,比如説女性更多的是搞託兒所的,護理類型的工作,那些工作的工資不高,所以有差異。但是,你如果真是一樣的位置,一樣的任務,女性還是比男性少7%。這不是按照法律,是不同公司自己定的。按照法律應該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王紅旗:明白。從國家制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四十八條第一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第一章第二條第二段:“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國家採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各項制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正式在這些制度的實施,女性職業發展情況呈不斷上升趨勢。但從實際的工資結構上比例上看,還是男性工資高。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不同體制的企業,有公有制的國家企業,集體制企業,也有個體企業。就像您説的,很多公司都是自己制定的,男女工資並不一樣多。但我不清楚具體的比例。在高等院校教授的工資是男女同酬的。但是,大學女教授的數量比男教授少,有研究者對我國1000多所普通高等學校女教師正副教授職稱從1984年至2000年所佔的百分比做了調研統計。1984年,我國高校女性教師人數比例只佔教師總數的26.19%,正高職稱僅佔5.75%。而在2000年,女性高校教師人數比例已經佔到45.96%,副高職稱有15.80%的差距,正高職稱差距最大,為48.64%。雖然,我國高校女教授正高職稱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當與男性相比仍然較低。但新世紀以來女性高級職稱、特別是女性正高級職稱的百分比增長還是比較快的。儘管如此,在女性職業生涯中的“滲漏性”是很嚴重的。比如,在對北京高校女教師的調查中發現,從女教師的職稱結構來看,金字塔特徵表現得十分突出,女教師所佔比例與職稱成反比,就是説,職稱越高的女性所佔的比例越低,職稱越低的女性所佔的比例越高,教授職稱中男女的比例更是相差懸殊。這就是如您所説的“女性與職業生涯”在德國是一個非常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問題。可見,在很現代的德國也存在這樣的性別不平等情況?
謝 妮:德國也存在這個情況。
王紅旗:具體表現是什麼?
謝 妮:最高的層次,特別在公司裏面的最高層,大部分都是男的。但是現在國家有一個政策,也是一個經歷了很長時間很大的討論。但政策剛剛決定,在大公司的不是董事會,是跟董事會類似的一個重要組織,我們叫管制會(Aufsichtsrat), 參加這個管制會的應該有30%的婦女。因為是新的法律規定,各個公司應該執行。現在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怎麼找到很多婦女能參加這個管制會?因為她們應該有經濟經驗,應該有管理經驗,應該知道公司企業的發展。我們一直在提出這些問題,德國職業女性也同樣有一個“玻璃頂”。王紅旗:其實,“玻璃頂”是由文化偏見與不合理制度構成的,它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自我意識的。實際上是一種隱性的性別歧視,就是讓女性沒有辦法走上去。實際上,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轉型的中國,顯性的性別歧視正在逐漸減弱,就是這種隱性歧視給女性發展帶來心理挑戰。
謝 妮:對,是大量隱性的,看不到的,説不清的理由。王紅旗:這種説不清、道不明的理由,無形的、微妙的屏障,就足以阻擋女性向上發展。韓 梅:是的,在中國,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高校,都普遍存在高層領導層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現象。有一次我陪同校長參加一個校領導座談會,發現整個圓桌上落座的二三十名高校校領導中,只有一位女性。相反,我在歐洲,尤其是北歐訪問時,接待我們的大學校長、副校長,很多都是女性。所以,我個人的印像是,北歐女性更為獨立、強勢,享有更寬容的性別環境。但是,在我們學校的層幹部中,女性還是佔相當大的比例的,而且,多年來我們學校的第一把手也是女性。

謝妮
中德兩國“女性與職業生涯”的現狀
王紅旗:中國女性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市場消費資訊時代,政府賦予的“鐵飯碗”被打碎、重新創業的職業生涯“大地震”,面臨新機遇與新挑戰的個體靈魂成長的艱難歷程之後,無論面對順境,遭遇逆境、困境、絕境,大多都具有笑談苦難悲歡、突破重重困境的能力。她們挑戰傳統女性角色定位,克服女性性別弱點,發揮自身聰明才智,創造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質財富,積累了豐富的職業生涯與家庭生活經驗。並且堅信在全球化的知識經濟資訊時代,比智力,女性很有機會出類拔萃,當那些有形與無形的“玻璃頂”被打破,女性創造的潛能就會脫穎而出。這些鮮活的、具體的實踐經驗,是我們聯手考察研究的國際女性生存學、女性成功學的源頭活水。對中的女性發展而言,是非常有價值的。您談到的,在德國對於年輕的媽媽們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中國女性同樣遭遇這樣的事業與家庭角色兼顧的兩難困惑。實際上是一個女性生活方式重建的困難。有些不僅僅是為生存,而是為發展自我社會價值,或者説是社會自我與家庭自我,職業與妻子、母親等角色的協調發展,從而達到女性的全方位的發展。通過制度改革來,建立相應的機制平臺,提高女性/母親的就業機會就顯得非常重要。我想聽聽您談談德國女性的生活現狀。
謝 妮:德國女性也有這個困難,因為有了孩子以後還是大部分的家務是婦女去做,或者大部分的負擔是家庭負擔。我們這一代有了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也是從下到上,也提高到男女平等,從那個時候開始女性也要求男人一樣的參加家務勞動,一樣的參加子女教育的工作,這是一個初步開始,我們這一代只有個別的人可能是比較平等的,男人也參加過家裏的工作,可能知識分子就比較多,看孩子還是大部分有女的來承擔,但是男的也會照顧孩子。或者在知識分子當中,你們周圍也有這個情況,也不一定你的工作很穩定,可能你有3、4年工作,後來可能有一年沒有工作,就拿到你的失業金,我們有社會保障,我的那一代我知道不少人就是這樣,有的時候男的工作,有的時候女的工作,或者兩個都工作,或者少工作,一般的是一個星期40個小時工作,或者20個小時或者30個小時。孩子小的時候,有一些比如説大學,公共方面的國家提議一些條件,讓父母少工作,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你可以説孩子到6歲的時候,你可以選擇少工作,可能十年前有一個新政策,就是父母有了孩子以後可以一年不工作,或者是妻子或者是丈夫,可以一年不工作,可以選擇。
王紅旗:選擇不工作的話,還有工資嗎?
謝 妮:有,國家給一年的80%左右。
王紅旗:那很好,夫妻雙方可以一心一意地照顧孩子。也學是因為經濟的原因,中國的政策是,只生一個孩子的話,女性可以享受6個月的産假,發給工資。僅指國家體制之內的女性,其他公司企業的制度都不一樣。這些女性尤其面臨生孩子後的再就業問題的困難。從這一點上講,德國的制度比較完善,小孩小的時候,無論是妻子或者丈夫,可以有一個人出去工作,另外一個人就在家裏待一年伺候孩子,無論男女都有工資。
謝 妮:對。這是因為從下到上,就是那些年輕人向政府要求,取得的權利。
韓 梅:跟人口比較少有沒有關係?
謝 妮:也有。所以也都應該看經濟的情況,社會一般的情況。還有一個特別的政策,一般就給一年的,如果男的不參加就給一年12個月,如果男的參加可以有14個月。
王紅旗:鼓勵讓男性做家務。
謝 妮:是。因為這樣,還是有不少男性很願意要這兩個月的工資。
韓 梅:在歐洲城市的大街上,時常能看到逛街的一家人中,丈夫抱著、背著孩子,推著嬰兒車,一派模範奶爸的形象,妻子則坦然受用,神清氣閒。王紅旗:也許因為,中國從數千年封建的傳統社會發展而來,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外女內的社會分工等級制度,至今還根深蒂固存在人們的意識觀念裏,有很多男性知識技能是現代化的、高科技的,但是骨子裏卻是大男子主義,能夠接受賢妻良母,女人無才便是德。就是不能接受女性比男性聰明能幹,尤其對高才華的女性有所恐懼。因此,有一些高職女性,比如女教授、女博士、女高管,女領導的婚姻家庭經常會遭遇不幸,事業特別成功,不是獨身就是離異,在事業與家庭方面很難找到平衡。還有一些年輕女性,為了追求事業成功而選擇獨身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為了事業而延遲走進婚姻家庭被稱為“剩女”。但是,一些有獨立經濟能力,社會身份的女性,認為一夫一妻制婚姻本身就是男權主義的,不結婚表示對男權主義的抗議,自我選擇獨身生活。 還有一些是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對象結婚就先獨自生活。尤其是底層的職業女性,離異後的單親家庭,造成女性生存經濟的貧困,也是一個影響女性職場發展的原因
謝 妮:實際上,德國也存在這種情況。很多男女不願意結婚,或者成家。在這方面,我們兩個國家的情況很類似。現在城市裏面是自己獨家的人越來越多,年輕人結婚也有不少沒有孩子的人,也有不少女性自己就一個人帶孩子。她們也有社會保障,退休之後就享受國家的養老金。一般是單親母親的家庭,很少是父親。離婚率也比較高。
王紅旗:您研究經濟方面專家的,在德國是不是經濟上比較富裕的女性,選擇獨身生活方式的比較多?
謝 妮:是的。年輕人一般都想找到合適的對象,堅持愛情理想年輕人還是多數。有些人是找獨自生活,找一個合適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話,可能是幾年跟這個,幾年跟那個。同居性的,不結婚很普遍的。
王紅旗:這種現象在中國的存在相對少數。也可稱其為前衛的生活方式吧。這可能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先哲孟子就有“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的訓教。就是説,像愛自己的老人一樣去愛別人的老人,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別人的孩子,以這樣的關愛倫理秩序治理家庭,家庭就會和諧。用這樣關愛倫理秩序治理國家,國家就會和諧。因此,中國人一向重視家族血緣,家國同構。當然要摒棄其中的封建等級與男權思想。
謝 妮:德國也正在想建立這樣一個和諧社會,怎樣才能有一個和諧的社會,這也是一個國際上討論的大問題。或者説什麼樣的社會是人類理想的社會。
王紅旗:你覺得理想的社會是什麼樣的?
謝 妮:我認為,我還是懷疑的,我不知道男女怎麼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家庭,這個很難很難。而且是很大的工作去做,尤其是你對自己做工作。王紅旗:對,您説的自己做很多工作,實際我們叫情感投入。婚姻家庭是要投入真愛情感的工作,不能把什麼都算得斤斤計較。您認為婚姻家庭需要女性自己做很多工作,對其職業生涯發展的太有影響了?謝 妮:有了對象會促成你的生活內容, 同時也要求你投入感情和關照。王紅旗:我們又回到了的原點上,就是説理想的家庭夫婦、子女之間應該是平等與關愛的倫理關係。僅僅只有平等是不夠的,凝聚一個家庭的情感核心是愛。就是您説的要投入很多具體的情感、愛心去經營家庭生活。中國的女博士,即便就像德國現在最時尚的方式,找一個人一起同居,兩個人生活一段離開了,也是在平等和諧的互相關愛當中才會獲得幸福的。
謝 妮:但是,第一個是想得到理想的職業目的,哪有合適的、喜歡的工作,第二個是你有機會遇到心愛的人,大部分都希望這樣。
王紅旗:是的,首先得有這樣的訴求。在德國只是同居,沒有婚姻契約,不領結婚證的佔多大比例?
謝 妮:我估計,在城市獨身可能是30%,結婚40%、50%,同居20%、30%。因此,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情況,而且都是很自然的。
王紅旗:都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謝 妮:是這樣的,沒有社會壓力,沒有文化風俗的壓力。現在從父母方面也沒有什麼壓力,但在20世紀70年代還是有壓力的。可是,有了自由也有了責任。因為就沒有這個依賴了,所以責任就很大。
王紅旗:對婚姻沒有依賴的時候,可能就不存在我們所説的婚外情了。請問你們對婚外情如何理解,不限制吧?
謝 妮:很少,因為你或者結婚,或者跟你愛的人在一起同居,或者你不跟一個人在一起都可以,社會方面都認可。經驗是,男的經常希望還有別的女的,特別是女性受不了。
王紅旗:那還是結婚比較穩定些。
謝 妮:是,那當然,但這得做大量的工作。我覺得,如果對職業或者對感情都會去努力,工作和家庭方面都不會做的很好,因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韓 梅:所以很難兼顧兩個都特別好。
謝 妮:是的,這是全世界的婦女面臨的同一個問題。
王紅旗:有沒有家庭暴力存在?
謝 妮:個別的有。王紅旗:剛才在談到女性與職業生涯時,你談到一個心理層面的問題,根據我們的經驗,如果一個知識女性當了女主管甚至當了女總裁,她會用她經營家庭的親和去經營她的企業,親和力比較強,是一種溫柔的力量。目前看來,這樣的方式要比男領導以威懾力經營企業的效果比較好。韓 梅:俗話説“男女搭配,幹活不累”,一方面説明男女心理上的需求,另一方面説明男女性格的互補有利於提高工作成效,完善工作效果。女性春風化雨般的風格和耐心細緻的特點在職場上能夠起到男性無法替代的效果。
謝 妮:是,有一個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研究結果就是這樣的。當然是多樣性的,如果一個公司男女都在當領導,一個小組裏面有男有女,效果才是最好的,有這麼一個研究。王紅旗:在中國企業界出現這麼一種情況,跟德國也有所相似,總裁大多是男性,副總裁大多是女性。這種搭配叫剛柔相濟。從領導層的頂層設計方面,女性參與領導權越來越多了,更承認女性領導的價值了。這是近來30年來真正的女性文化非常大的收穫。男性大男子主義意識也在逐漸改變,而且承認女性智慧的力量。我認為,女性擅長以平等友善、親和對話,以分享代替統治,以互利取代附依,以“不同而和”代替戰爭的處事之道,會逐步受到世界的崇尚與青睞,對人類和平很有價值。謝 妮:是的。
王紅旗:所以,我們研究女性與職業生涯非常有意義,如有機會能夠合作,共同發起關於性別平等的關愛文化建構,尋找人類和平的新文明關愛文化,也是我們作為50後的知識女性應該有的一份責任。實際上這是一個女性意識和人類意識的合二為一,個體社會責任和人類責任的合二為一。就是這種動力經常支援我,就做的很有心勁並樂在其中,因為你能感覺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謝 妮:這也是我也想搞當代社會女性與職業生涯研究的目的。
王紅旗:對,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共同的理想。請問同性戀問題在德國的現狀如何?男同性戀和女性戀家庭模式都是存在的?
謝 妮:德國是比較普遍的。而且還在增加。
王紅旗:在歐洲同性戀法律已經全部覆蓋嗎?
謝 妮:不是全部的。在德國是合法的,他們也可以結婚,他們也可以有孩子,只要他們願意向別人要孩子,如果他們沒有自己的孩子有一點困難,但是我朋友當中有不少的。
王紅旗:領養孩子?
謝 妮:不,他們兩個人,但是沒有孩子。但是想要孩子的越來越多。
王紅旗:德國只結婚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多不多?
謝 妮:多。
王紅旗:德國現在面臨不面臨社會老齡化的問題?謝 妮:有。為什麼就這麼支援生孩子,這個和中國不一樣的。
王紅旗:養老問題在德國的養老方面的政策方法是不是比較完善?
謝 妮:是比較完善,一直在改革,因為原來的方式是我們用現在工作的人去付的那筆錢,用到已經退休的人去生活,就有一個計算説這樣這個錢不夠,因為工作的人越來越少,退休的人越來越多,所以現在也開始有一個私人保險,原來全部都是社會保險,現在讓人自己保險的越來越多了。
王紅旗:剛才談到年輕人只是結婚不生孩子的問題,現在德國現狀如何?
謝 妮:好像有一點波動,比如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當中,有不少人沒有孩子,以後更多的沒有孩子,好像現在年輕人開始又想要孩子了。這不光是考慮到社會保障的問題,也考慮到你單獨住或者沒有孩子,可能也不一定是很幸福的生活,缺一點。
王紅旗:這種觀念也和中國挺相似的。
謝 妮:我的看法是每一個人不一樣,我有密切的朋友,有兒子,現在也有孫子,但是我沒有丈夫,但是我有很親密的朋友,而且我經常跟朋友們在一起。
王紅旗:對。其實還是一個情感上、生活上的伴侶,這樣不孤獨。如果説經濟上養老像您的待遇,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但有一個特別親密朋友經常可以説心裏話,是情感上不能缺少的。在有一定經濟基礎的情況下,最重要的幸福感,是來自於情感而不來是自於金錢,可以這樣理解嗎?
謝 妮:理解,完全對的。經濟方面應該有一個基礎。
王紅旗:也就是説,在很多方面我們的生活觀念、精神訴求是一樣的。這就是我們兩國能夠在女性文化方面,對女性與職業生涯進行對比研究的基礎。因為,其本身就有一種同構性,有的是相同的,也有相異的。兩國女性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解放歷程,不同的職業生涯中,遇到了相同困惑問題,積累了多種解決的辦法,使我們的研究在同中求異、異中求同或求同存異,而達到精神訴的統一性,這對於世界女性更深層的精神解放、人格成長完善,是一種非常好的方式。
謝 妮:對,我們的想法也是從兩國女性生活與生存,職業發展的比較開始。王紅旗:是您的想法啟發了我,很感謝您,謝謝韓梅院長。我們曾做過關於中國女性的職場生涯解讀節目,主題為“遭遇職場就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女性誰更無奈”。您看咱倆是50年代生人,韓梅院長是60年代,我的助理是80年代,在職場上表現出很不一樣的特點。 50年代生的人,像我們是“無我”的,或者説是先有“大我”,後有“小我”,先有“集體”,後有“個人”。
謝 妮:不考慮自己。
王紅旗:很對。因為,那時國家倡導集體主義,我們是一顆集體主義的螺絲釘。60年代的出生的人,是辛苦的。我國60年代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人人挨餓。70年代出生的人,是尷尬的。他們就覺得自己啥也不是,哪兒也摸不著,沒有60、50年代生人的那種位置,他在找前找後找不到位置。80年代生人更是充滿無奈。
韓 梅:這就是中國社會轉型,然後價值觀變化特別大,人生目標、理想好像都找不著北了。是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轉型,所以夾在縫裏。王紅旗:80後因為是獨生子女,大多為幾代人都關心著他,是比較自我中心的。在職業生涯方面,因時代不同所以存在的問題也不同。現在解釋一下女性在職場的無奈,50年代生的女性在無奈職場于政治,60年代的女性在職場的無奈是計劃經濟,70年代的女性在職場的無奈是文憑,80年代出生女性無奈職場壓力。
謝 妮:這樣解釋中國的。
王紅旗:也就是説,50年代的女性性別幾乎被所有人忽略,包括自己也忽略了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誰,就是這樣的無我。60年代的女性在職場打拼,直言威脅來自70年代生人,因為70後在他們後面,後來居上。70年代生的人説前有60年代坐鎮,後有80年代追趕,這兩方面就覺得很緊張。80年代女性可以説是新新人類,她們的尷尬狀態是,對60年代信服但疏遠,對70年代崇拜的偶像從此誕生,這都是調查裏面得來的一些想法。
在談如何去解決職場失敗的問題時,50年代生的女性應該調整心態魔方,你不應該什麼時候都是為別人,應該有自我主體意識。60年代生的女性要相信自己獨特的魅力,不要怕前怕後的。70年代的女性,要放心追逐自己最想要的生活。80年代的女性要不怕摔跤和失誤,勇敢往前走。
謝 妮:你們經常做類似職場調研或節目嗎?
王紅旗:現在主要在中國網做。有很多女性職場方面的故事,您能不能講講德國女性職場的故事?
謝 妮:剛才説了,50年代德國的經濟越來越發展,發展的很快,女性都在家看孩子,德國也有一個“特別的”沒有工作。有一個流行的叫法“烏鴉母親”,就是説,在外面工作的,不在家看孩子母親,就叫烏鴉母親。這是很不好的意思,50年代就開始有這種説法。所以,女性的一個理想就是在家裏照顧孩子。王紅旗:明白了,德國50年代是鼓勵女性在家,你如果在外面工作就是“烏鴉母親”。因此,女性就想做在家裏的全職太太,不願意做在外面工作的“烏鴉母親”。謝 妮:而且烏鴉母親的概念一直到現在起作用,起不好的作用。其實是從希特勒那一代,他就非常重視家庭母親,特別重視女人有孩子。因為,我們對希特勒特別重視家庭,對束縛女性有特別反感的感情。所以對家庭也反感。70年代女性解放的時候,靠70年代或者60年代繼續去做女性解放,政府也一直在做關於女性解放、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工作,但是很慢很慢。現在可能有些又回到家庭是理想的,很模糊,沒有一個很理想的模式,都在探索。
王紅旗:目前,在全球化語境下人類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正在重組,如何以對話解決衝突,推進世界和平事業發展。國際女性之間生存發展經驗交流,互相認識與提升很重要。尤其是,中德文化交流友誼從十三世紀至今,源遠流長。兩國的哲學、文學與藝術先賢知識分子,把中德文化碰撞喻為“徹底的精神體驗”。我們對女性職業生涯的對角度研究,也是從兩性關係、女性生存現狀與和平的關係出發,共同構築性別和諧與世界和平的新希望問題。自我獨立意識,性別平等意識,是女性自我內心強大的內在力量。由於中國毛澤東時代就開始力倡男女平等,是自上而下的婦女解放模式,德國是自下而上的婦女解放模式。但是,就這兩種婦女解放模式而言,是有各自的經驗可以總結的,也有多方面經驗可以比較的。如果把這兩個國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典型女性解放經驗進行研究,對影響女性職業生涯的文化、社會、自我的因素做一個理性的分析,客觀去審視女性以前走過的路,女性的職業成功和困惑在哪,去尋找社會的原因,制度的原因,文化的原因,自我的原因,是非常有歷史、現實與未來意義的。就像您説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非常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問題。
本期資訊
主持人:王紅旗
時 間:2015年4月1日
地 點:首都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大廈
第七會議室
嘉 賓:謝妮 韓梅 周顯波
嘉賓介紹
|
|
精彩片段
活動預告及報名
活動報名:請將姓名+職業+聯繫方式發送至female@china.org.cn
報名成功會有郵件回復
聯繫方式
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中國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王紅旗
助理 周顯波
責任編輯 蔡曉娟 王琳
聯繫電話:88828051
電子郵箱:female@china.org.cn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聯合出品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 聯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