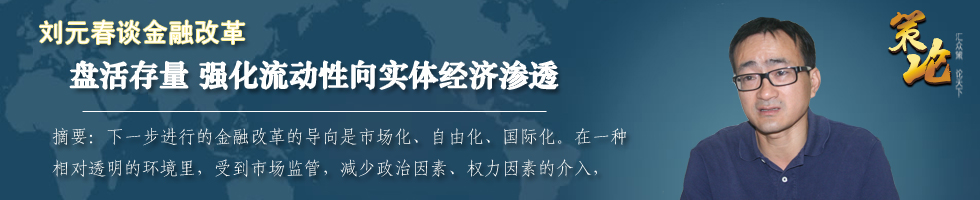輿論坐標
以論對策
金融“空轉”背後潛伏著深層次矛盾
銀行的前期資産擴展太快,導致短期資本金和撥付在結構上出現問題。而這背後則是整個金融體制的扭曲、資金的錯配以及商業銀行行為模式的變異到了一個新水準,從而導致我們在某個時點上出現體系運轉不良。 [詳細]
讓信貸存量流向實體經濟
要調整商業銀行扭曲的、沒有實體經濟基礎的逐利行為,要改變大量資金向表外流動,要打破金融體系內的這種迴圈,其實都是監管當局在加強監管,是對商業銀行的違規失范行為做出全面調整,同時貨幣當局要對貨幣政策進行全面的綜合指導和道義勸説。 [詳細]
根除監管套利的制度性根源
除了加強流動性的向實體經濟的回歸之外,對於存量不良的資産,該處理的要處理,該暴露的要暴露,這也是盤活的一個重點。利率市場化要陸續推開,使資金供求面能夠在更靈活的市場環境下進行匹配,根除監管套利的制度性根源。 [詳細]
金融改革重點在打破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
要在糾正資金錯配、金融空轉,調整金融過渡風險化行為過程中實現軟著落,在技術層面,這就考驗中央銀行怎麼來駕馭這些問題,也就是説,改革的秩序節奏就是關鍵;在制度層面,要對於一些利益集團做出明確調整,打破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也是很重要的。 [詳細]
文字直播
6月的一場金融風波讓整個市場都捏了一把汗。6月本來就是年年的“錢荒”月,但今年對銀行系統和融資市場來説是資金和貸款額度相對緊張的情況更加明顯。
李克強總理一個多月時間三次提到“存量資金”問題。近期包括央行、監管層的舉措都是為了糾正經濟結構性問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一屆政府對短期經濟增長下行、對短期副作用的容忍度正在提高。
今年銀行系統的資金相對短缺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盤活貨幣存量”對於金融改革的意義何在?金融改革的難點又是什麼?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在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時都做出了深入分析和解讀。
中國網:內地銀行業的所謂的“錢荒”近期掀起金融領域的一次風波,這個風波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劉元春:這一次“錢荒”從表像來看好像是資金流出過大,好像是由於季節性因素,由於財政入庫準備金的收繳和監管調整等因素引發的,但是實質上暴露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現:
第一,就是銀行的前期資産擴展太快,導致短期資本金和撥付在結構上出現問題。而這背後則是整個金融體制的扭曲,資金的錯配,以及商業銀行行為模式的變異到了一個新水準,從而導致我們在某個時點上出現體系運轉不良。主要表現為在某些時點上央行進行的一些非預期性的調整,導致很多銀行在流動性管理上出現問題。
第二,商業銀行逐利行為過度,這與我們穩健的風險管理和內控是相違背的。很多商業銀行急需通過短期資金的發放來吸取資金同時又來進行較長時間的放款,逐漸演化的最惡劣的狀況就是把一些拆借資金,通過這種市場的週轉進行款項發還,就導致很多的資金出現錯配。
第三,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前期的高收益率的理財産品和表外業務的擴展,導致一些商業銀行在資金結構、行銷模式上發生了一些變異,就導致它必須要維持套取新的一些流動性,從而導致銀行前期的監管套利行為,再加上前期部分行業融資難導致的利率上漲,要維持發行表外業務,理財産品又導致進一步的發放相應的一些資産。因此就形成了金融圈的“空轉”,在某種程度上是脫離實體經濟發展的,沒有這種利潤收益基礎的一種金融迴圈,帶來的後果是比較嚴重的。
這三大深層次的原因,實際上就會集中體現在幾大指標的衝突上:
第一,M2,貨幣供應量,信貸總量,社會融資總量,雖然存量很高,增長速度也很快,但是拆借市場的利率和實際利率、貸款利率都沒有下降,反而逆勢上揚。那麼這兩個指標的衝突就是説明我們整個的資金錯配問題是比較嚴重的。
第二,存量資金很多,像備付金1.5萬億,很多指標都很多,但是拆借市場上的資金很緊張,並且5月份就已經出現了,維持在5%以上的這樣一個水準,從而導致利率出現短期和中期的利率倒挂現象。
第三,金融整體的資産存量和增量都很快,但是實體經濟沒有錢,這也是一個矛盾。
這三大矛盾實際上是由於上面這三個深層次問題引發的,從而導致我們在某些時點上,由於某些偶然性因素來促發這些問題暴露,因此我們看到的比如像光大銀行的違約,中國銀行的問題,雖然我們看到的都是個案,但背後有一連串的這樣的個案事件,而這一連串的個案事件背後又潛伏著這些深層次的三大矛盾,三大核心根源。
中國網:有觀點認為,在當前的格局下,中國經濟尤其是信貸資金的最終去向,央行已經沒有能力把握了,只有靠中國政府出面制衡。你怎麼看這個觀點?
劉元春:那倒不至於。
第一,銀行和貨幣當局,對於整個資金的控制依然是很強烈的。從這一次“錢荒”爆發的導火索,實際上就是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都希望縱容商業銀行進行瘋狂放款,然後進行空試點,從而倒逼央行來進行釋放流動性,是要改變這種格局做出調整,這説明央行的調整還是比較強的。
第二,我們的貨幣當局和監管當局,實際上對這些問題已經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從2010年開始,銀監會已經對於投融資平臺的債務問題進行全面清理,同時也對於銀行表外資産進行了全面管理和監管,同時近期對於非標準性資産進行表內化的做出很多調整。在去年年底的工作會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央行這些貨幣政策,包括反覆強調的“控風險”是今年的工作重點。
在某種程度説,這一次所謂的“錢荒”是監管當局和貨幣當局進行的主動調整,反映出貨幣當局和監管當局已經在對這些問題進行制約,只是央行在這個金融秩序的調整,金融風險的控制過程中,在流動性問題上應當更審慎。
要調整商業銀行這種扭曲的、沒有實體經濟基礎的逐利行為,要改變大量資金向表外流動,要打破金融體系內的這種迴圈,這些其實都是監管當局在加強監管,對商業銀行的違規失范的行為要做出全面調整,同時貨幣當局要對貨幣政策要進行全面的綜合指導和道義勸説。
所以説,國家要想真正改變這種格局,應當是進一步加強監管,同時對於商業銀行的一些過度的非穩健行為要進行一定的處罰,特別是最近幾大行出現的拆借違約的問題,不僅要教育這些商業銀行,更重要是要進行問責制。
中國網:怎樣的問責和懲罰是最有效的?
劉元春:這次的“錢荒”也暴露出商業銀行在管理上存在的問題。目前在表外資産膨脹,在資金錯配過程中,它的經營行為已經失去了監管當局所要求的穩健性的原則。
在我們目前金融秩序整頓,這個風險泡沫化解過程中間,還出現這種問題,應當説商業銀行內部管理的失范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如果國家要想真正進行治理,一方面在流動性上面應該更為審慎,另一方面,在監管上應該進一步強化,我認為,相關部門的主管應該解職,大銀行裏面至少是主管該流動性管理業務的副行長應該進行受到處罰,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網:近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李克強總理對於“盤活貨幣存量”的提法,公開至少有三四次,“盤活貨幣存量”對於金融領域的改革來説意味著什麼?
劉元春:我們確實有大量的貨幣存量,首先,M2很高,但是流到實體經濟的資金相對較少。因此所謂的存量概念主要是指,目前我們所看到企業的存款很高,但是大量的企業存款是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在的,同時很多的企業資金都是進行金融債投資,投資意願相對較弱,這種情況對於整體國民經濟的良性運作是存在很大的問題。所以,盤活存量就是要切實讓以往的信貸存量向實體經濟流轉,這是很重要的。
中國網:在資金流轉過程中,存量資金使用效率低,使用方向錯配問題的核心原因是什麼?
劉元春:金融領域的一些短期産品和表外業務的産品收益率是大於實體經濟的正常收益率的。因此,實體經濟的收益率在下降,金融領域的收益率還在上揚,這種背離使整個金融出現“搏殺”行為,甚至在局部出現了一些長期理財行為,就是為了維持他前期的資金週轉,不斷地發新債、還舊債,並且利率越發越高。
因此要加強流動性對實體經濟的回歸,盤活存量,就要認識到,表面是金融資産收益率和實體經濟收益率的背離,但是實質上是在經濟回落的過程中金融本身出現了變異。
中國網:如何治理金融本身的這種變異?
劉元春:必須叫停資金空轉,叫停這種為追逐非理性的較高金融收益率的投機行為,打破這種惡性迴圈,甚至是局部長期理財的這種迴圈。
所以説,對於一些短期的理財産品,某些風險較高的部門集合貸款,以及一些來源不明、使用方向不明的委託貸款等等,要進行查處和清理;另外,要增強監管,對於非理性的逐利行為加強管制,使銀行業的資金成本逐步回歸,銀行可以進行指導性的,對一些資金價格信號有所調整,因此在同業拆借市場上,在糾正商業銀行的行為上,應該交于監管層面;同時,貨幣政策應該把同業拆借利率的緩和作為重點,要進行分工,商業銀行要調整它的行為。
不僅如此,目前控風險、糾扭曲、去泡沫的過程中,可以強化一些信貸的定向流放,但並不是簡單的大規模的放給資金量還比較充裕的,存款量很高的國有企業,而是要向一些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進行適度傾斜。
就盤活存量本身來講,除了加強流動性的向實體經濟的回歸之外,對於存量不良的資産,比如一些理財産品可能會陸續存在的違約現象,該處理的要處理,像投融資平臺的一些問題,該暴露的要暴露,這也是盤活的一個重點。
最後,就是利率市場化要進行陸續推開,使資金供求面能夠在更靈活的市場環境下進行匹配,根除監管套利存在制度性的根源。
中國網:金融領域的一些違法違規行為,可能跟腐敗是不能完全分開的,你認為這個金融領域的腐敗對金融改革作用有多大?
劉元春: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如果我們存在一些過度管制,就會存在套利空間,就會存在一些銀行的主管部門利用管制價格和市場潛在價格之間的差價謀取收益。
理想的情況是,在一種相對自由的環境裏面,管制因素相對較小,出現金融腐敗,甚至一些金融犯罪的現象可能就會減少。
我們下一步進行的金融改革的導向是市場化、自由化、國際化。其中,市場化、國際化過程中,就會使監管的套利空間、權力腐敗的空間大幅度縮小,在一種相對透明的環境裏,受到市場監管,減少政治因素、權力因素的介入,當然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中國網:除了從金融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其實這次所謂的“錢荒”在群眾中還是引起了一些恐慌的,甚至有些民營企業也受到了影響。那麼金融市場的動蕩對老百姓以及一些中小企業來説,存在著哪些短期和長期的影響?
劉元春:第一,在某個時間出現這種流動性的問題,肯定會帶來系統性的振蕩,這個振蕩就是恐慌。當然需要明確的是,目前的流動性“錢荒”的出現是在可控的環境,因此不會出現銀行的存款支付問題,這是肯定的,因此老百姓大可不必太恐慌。
第二,中國採用的是存款保險制度,即使在過去一些局部的商業機構出現一些問題,國家都是負責還款的。我們目前並不存在支付性的危機,只是出現流動性管理上的一些大的磨擦,出現一些個案事件,並且個案事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各個方面因素綜合的短期的産物。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國銀行業本身總體的資産負債狀況是處於良性的。資産負債率,資本充足率都在10%以上,同時不良率只有1.03%,撥付總額很充分,只是在局部環節出現問題,而這個環節出現問題是因為商業銀行的某些行為變異,而政府希望調整它所出現的問題。
因此對於老百姓來講,應該不必要在這上面有恐慌情緒,當然這也説明,央行在處理這個事情時,的確需要更審慎,不要因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事情,産生系統性的恐慌。
對於中小企業來講,目前所看到的國家穩健貨幣政策的方向,同時對於資金空轉要進行全面整頓,下一步要盤活存量,強化流動性向實體經濟的滲透,這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小企業是有一定利好的,但是應當看到在經濟相對疲軟的情況下,金融秩序整頓的過程中,雖然我們可能會加強一些定期投放,但是中小企業本身依然要過緊張日子,不可能過上太寬鬆的日子,這肯定是一個常態。
所以,一方面監管當局應該加強監管,另一方面,中小企業也不應該太樂觀,也不用太悲觀,應該要很審慎處理這個事情。
中國網:您認為金融改革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劉元春:在技術層面,要在糾正資金錯配、金融空轉,調整整個金融過渡風險化行為過程中實現軟著落,是一個富有很多技巧和藝術的管理,這就考驗中央銀行怎麼來駕馭這些問題,也就是説,改革的秩序節奏就是關鍵;
在制度層面,要對於一些利益集團做出明確調整,打破商業銀行的盈利模式,也是很重要的。
金融改革的重點,就是人民幣資本項目的開放,這依然會對相應的一些傳統套利渠道産生很大衝擊,那麼也要考慮利益集團的問題以及宏觀的、穩定的問題,這兩方面都是難點。
如何在改革過程中,保持宏觀的穩定和金融的穩定,這是底線。很多金融風險往往是在調整中、改革中出現一些鬆動崩潰的現象,所以,要加強這方面的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