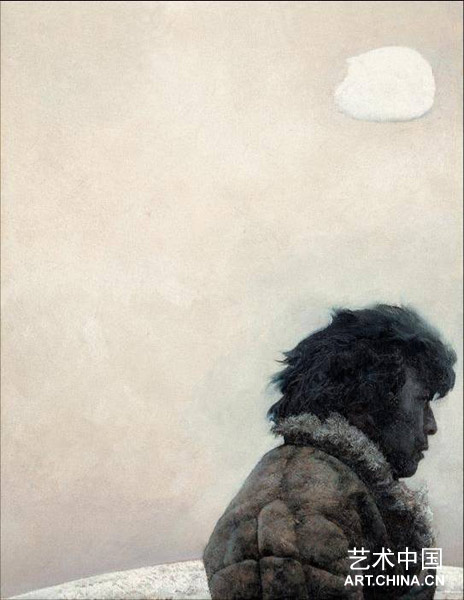
八十年代的中國畫壇並不缺少西方大師的風潮,當時引進的歐美畫展與畫冊直接或間接地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日後國內畫壇炙手可熱的畫家。這種成功經驗甚至在九十年代被總結為某種模式,即選定某位歐美畫家的技法風格,尋找可以直接借鑒的具體的表現語言,以西方大師的畫風來表現本土題材。十年前我在瀋陽魯迅美院讀本科的時候,流傳過這樣一個真實的笑話,某學生到魯美北門外的畫冊地攤上俯身尋覓良久後,問書販聽説有一個北歐的寫實畫家,油畫係人手一本的……,話音未落那書販便説啊,奧德!有有有!三百一本五百兩本。連書販都熟諳一個小圈子的局部流行風尚,可見追逐風潮其實並不是困難的事情。巴爾蒂斯、弗洛伊德、斯梵塞、盧奧……如果願意,統計一下三十年來影響過中國油畫創作的這些西人大師及其所對應的中國畫家的名字,是一件輕鬆而快樂的差事,而這些名字,當然也與中國當代油畫的接受史與審美價值更疊史密切相關。
在八十年代畫壇的種種風潮之中,與上述的“大師風”不同,“懷斯風”影響最眾持續最久也最為特別,特別到它已經超越了一場風潮,因為一種風尚是會過時的,而懷斯直至近日仍然是很多畫家心中的標桿。雖然懷斯的中文版畫冊直到1988年才在中國大陸正式引入,但在此之前,中國畫壇鄉土寫實主義的圖式與精神已然充盈著懷斯的味道。據艾軒最近的回憶,早在70年代,陳逸飛就推薦他去看軍博展覽中的懷斯作品,而在80年代初期,艾軒和何多苓已經坐在四川美院的圖書館裏翻看原版的懷斯畫冊了。一種風格樣式的移植與風行,很大程度上在於其對當下現實語境的適應程度,及其所能碰合出共鳴的可能性。正是懷斯畫風中的寂靜憂傷,與七十年代末期的“傷痕”美術的情緒相碰合,當這些畫家們意識到:個體命運的苦難與憂患,連同家庭的悲劇,可以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和情境抒泄出來,把內心深處的痛苦和對於命運的不可知的恐懼,轉換為某種恬靜而悲傷的畫面的時候,一種風格的移植與再創造才成為可能。當然這種可能的背後潛藏著必然,懷斯之於八十年代的中國畫家,不是為了尋找寄託而盲目皈依,而更像是鄉間偶遇並一見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