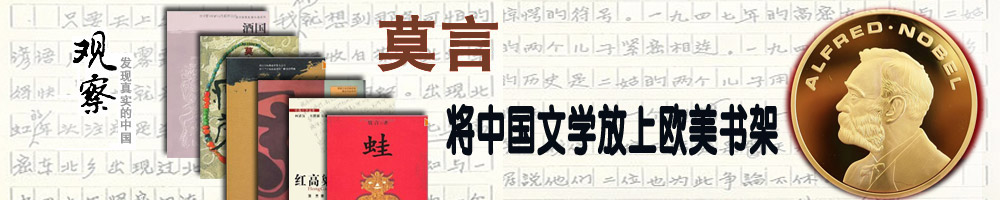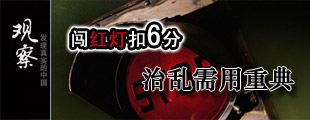|
中國人的諾獎情結不是虛榮心
中國人的“諾獎情結”可謂源遠流長。上世紀初諾獎初創,獲獎對於貧弱的中國來説還很遙遠。直到1913年,印度詩人泰戈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第一位亞洲人獲此殊榮。囿于當時的客觀條件,中國無力競爭自然科學方面的獎項,自然就特別關注與科學水準沒有直接關係的文學獎。很多人認為,作為一個飽受欺淩、內憂外患的“詩歌國度”,如果能夠贏得一項國際榮譽,無疑是贏得尊敬和證實自我的捷徑。鄰邦印度既然能夠獲獎,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於是,中國人的心頭就開始有了“結”。
在1927年,拒絕文學獎提名的魯迅這樣説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們。倘因為黃色臉皮的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 然而,無論是拒絕參選的魯迅,還是此後因過早辭世而與諾獎失之交臂的老舍、沈從文,都沒能夠讓這個在期待和挫折中一再鬱結的“諾獎情結”消散。
歷數諾獎109年曆史,獲獎者逾八百名。而已有8名華裔人士獲得自然科學方面獎項的事實足以證明,智力上,我們不輸于任何人。在文學獎上面,近百年的文學沉澱和歲月洗禮,中國人的諾獎情結絕對不再是“虛榮心”。中國的大國地位已然確立,但是在文化層面卻始終得不到世界的肯定。文化走出去了,文化軟實力提升了,但是中國數代作家的努力卻沒有將中國國文學擺上歐美書架。因此,中國人的迫切實在情有可原。
莫言的“當代一流”撐得住諾獎稱號
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的文學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及“愁鄉”的複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現實影響,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2011年8月,莫言創作的長篇小説《蛙》,獲第八屆矛盾文學獎。其作品在國內外有廣發的影響,被譽為中國當代最好的小説家之一。
莫言是最有資格(和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其一,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尖銳的筆觸書寫了當今的社會矛盾和當代歷史的創傷經驗;其二,勇敢的先鋒主義美學態度,在文體實驗和形式開拓上以各種形態突破了傳統寫實主義的機械手段;其三,鮮明的本土色彩,蘊含著大量中國鄉村文化和民間文藝的元素;其四,很不幸,諾貝爾獎的評委除了一人之外都不懂漢語,而在當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裏,被翻譯介紹到西方文字最多的,是莫言的作品。[詳細]
翻譯們成就了“諾貝爾•莫言”
“沒有安娜,就沒有莫言今天的成功。”昨日,莫言獲獎消息震動全國的同時,將莫言作品帶到瑞典的翻譯家陳安娜也成為網友關注的焦點。
陳安娜究竟是誰?8月27日,莫言曾在微網志上表示,他在瑞典出版了三本書:《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勞》,三本書的譯者均是在瑞典從事翻譯現代中文作品的陳安娜。除了陳安娜,美國翻譯家葛浩文也是助推莫言走向世界的有力推手。作為翻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國際級大師,數十年來,他已將莫言的十多部作品介紹給英語國家讀者。葛浩文表示:“我真心喜歡莫言的所有小説,並對翻譯它們樂在其中。我喜歡它們的原因各式各樣,比如《酒國》可能是我讀過的中國小説中在創作手法方面最有想像力、最為豐富複雜的作品;《生死疲勞》堪稱才華橫溢的長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極富音樂之美。我現在正在翻譯《蛙》,接下來還應該會去翻譯一些此前未能觸及的他較為早期的作品。”[詳細]
別説無所謂,但我們需要平常心
諾貝爾文學獎,不應該是我們得不到卻説“葡萄很酸”的獎,也不應該是我們得到了就要給國産作家扣上西化和媚外大帽子的獎。諾貝爾獎尤其是諾貝爾文學獎,需要用平常心來解讀,需要用長遠的眼光來看待。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最應該拋棄的就是當下的種種語境,而應該用更長遠的眼光來評價此事。再退一步講,媚外的作品未必能得到真正的大獎。正如莫言所説“文學沒有配方”,不是哪一位作家放好醬油、醋和鹽就能做出一份諾貝爾文學大餐來的簡單之事。
任何一個獎,之於偉大、寬泛的文學創作而言,都是膚淺的,即便它是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文學作品和作家,卻必須要用獲獎的形式獲得鼓勵和認可。作為普通讀者,至少我非常希望能有一位國産作家拿下此獎。國産作家獲得諾獎,至少不是一件壞事。正如中國電影界之望奧斯卡最佳外國語片獎,許多導演為之努力過奮鬥過,拿不到這個獎必然存在價值觀不同的問題,但如《臥虎藏龍》者拿了這個獎,至少證明這絕不是一部爛片。莫言的文字,縱然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但也並非犬儒之輩,不是嗎?[詳細]
國人最近對金牌的渴望空前高漲。但是文學真的沒有搞金牌主義的必要,還是不比、不鬧、不折騰為好。作家們該寫作寫作,該發呆發呆,該下生活下生活。只要故事寫得好,只要自己的故事真的寫了自己的心,對得起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讀者呢,買到了好書,讀得開心感動就行了。讓那些願意沒事找事的政客、文化焦慮症患者還有文化生意人自己去折騰吧,看客越少,犯傻的人就越少。
莫言一直很低調、很淡定,不是強調“我,沒、看、法”,就是説“千萬別提這事兒了”,而前幾年莫言就説過,老是對諾貝爾文學獎唸唸不忘只是自尋煩惱。也許,關注諾獎,關注文學不是壞事,起碼在純文學日漸邊緣的當下,這種聚焦提醒了人們對文學現狀的凝望與省視。
中國很高興,中國人更該好好看本書
很多支援莫言的人,或許只看過張藝謀導演的電影《紅高粱》,而未必看過原著,如果,連基本的閱讀面都不能達到,不管褒貶,都是缺乏誠意的。”
圍觀者中有罵中國作家得不到諾獎,有説諾貝爾文學獎如何褒賞性靈,好像前364天的存在就是為了看一部諾獎作品——但他們從不為中國作家埋單,但他們卻敢於將感覺視為精準的遊標卡尺,丈量諾獎與本土作品之間的距離。説白了,不過是一種情結,就像奧斯卡之於中國電影,奧運金牌之於中國競技體育。換言之,如果莫言真的得獎,又能改變什麼呢?撐死了算是為商業文化來一次正版意義的“開光加冕”,如同包裝上的3C認證、諾獎也會燙金在一幹作品的腰封上,供有此情結者買回家裝點客廳或書房。事實就是如此——往屆很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品引進中國後,卻少有人問津,譬如維•蘇•奈保爾、凱爾泰斯•伊姆雷、哈羅德•品特、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幾人讀過、幾人愛讀?它們頂多,在得獎的當年火在文學版上,或若干年後,在文學史上被我們順帶一筆。
一個崇尚文學的地方,諾獎自然不會如此情重意濃;就像一個群眾體育蓬勃的地方,比賽就斷不會成為悲情的狂歡。卡夫卡、列夫•托爾斯泰沒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薩特甚至拒領了諾獎,但這依然無損其大師級的榮耀。[詳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