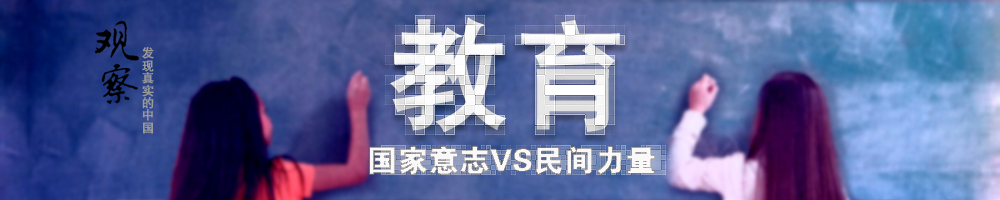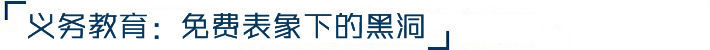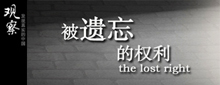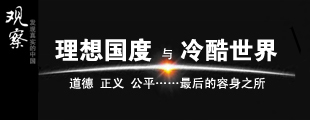|
在我國發展教育的過程中,一直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教育整體投入嚴重不足,財政性教育投入佔GDP比例4%的目標仍是目標;二是教育投入的領域與政府應當承擔的教育責任錯位,長期以來義務教育只是名義的“義務”;三是基礎教育主要依靠縣鄉財政,存在極大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校際差異。這些問題決定了基礎教育,尤其是鄉村基礎教育,應當是教育投入的重點。[詳細]
根據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到2012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投入佔GDP的比例將達到4%,以GDP40萬億計算,每年將在目前的投入基礎上新增1600億元。這1600億該怎麼投、怎麼花?盤點基層教育的各個領域,可以窺視國家教育投入的成效以及民間力量的地位。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我國將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積極扶持民辦幼兒園。
長期以來,我國的幼教經費一直只佔整個教育經費支出的1.3%左右,而發達國家學前教育經費佔總教育經費支出一般達到3%以上。許多地方政府更樂於將公共財政投入到很容易體現教育發展水準的高中和高等教育領域,而對學前教育投入甚少,在管理人員編制、辦學標準制定、監管等方面也都存在缺位。對此,國務院2010年提出了“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十二五”期間,中央財政將安排500億元,重點支援中西部地區和東部困難地區發展農村學前教育。並且還會安排“扶持民辦幼兒園發展獎補資金”,支援發展普惠性、低收費民辦幼兒園。
但是現狀是,一方面,各地政府在發展公辦園上的確很“大力”,學前教育經費向為數不多的公辦幼兒園傾斜,稀缺的優秀師資也不成問題,但入讀門檻相對很高,完全變成一種稀缺資源,對於廣大的非本地戶籍人員來説,只是看上去很美。
另一方面,民辦園的準入門檻提高,辦理許可證困難重重,而待遇地位跟不上導致教師流動太頻繁,貴族園與大量不符合辦學標準的黑幼兒園承擔起了對城市務工人員子女和農村留守兒童進行學前教育的重任,儘管民辦幼兒園的收費只需備案不必審核,但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基礎教育研究院成剛表示,40%的民辦幼兒園處於虧損狀態。在投入不足的情況下,這些民辦幼兒園自然成為事故多發地,從搜索引擎結果中可以看出,民辦幼兒園傷亡事故遠高於公辦幼兒園。但教育部門通常表示將進一步加大對民辦幼兒園的監管力度,卻很少提及加大投入,只依靠行政監管,要真正改善民辦幼兒園的辦學條件無異於緣木求魚。
截至2009年,全國民辦幼兒園的總數已達到8.34萬所,佔全國幼兒園總所數的62.2%,學前教育依然處於民辦教育為主的狀態。在公辦幼兒園不能包攬所有兒童的學前教育的情況下,給予民間資本扶持,並不是一句空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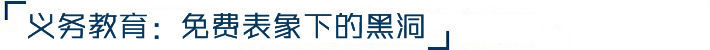
《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免試入學。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
擇校費來自教育資源配置上的嚴重失衡。名校成了“超級航母”,可以肆無忌憚地橫衝直撞,致使擇校大戰硝煙瀰漫。擇校費再多,依然有家長願意為孩子買單,正如一位家長説的那樣,“在名校裏哭泣花錢多總比在普通學校裏哭泣沒去名校要幸福。”事實上,擇校費是所有家長為教育不公買單,而結果卻又離期望的公平越來越遠。教育專家楊東平認為,擇校費出現有制度性原因:地方政府在高考政績指揮棒下,仍以培養精英的思維發展義務教育,加上“擇校經濟”給政府帶來的利益,導致優惠政策和資源向名校傾斜,兩極分化嚴重。義務教育是面向全體學生的保障性、基礎性教育,而不是選拔性的培養尖子的教育。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依法辦學,實現公辦義務教育學校的均衡發展。至於市民對於教育的多樣性、選擇性、豐富性需求,應該由民辦學校來提供。
由於城鄉義務教育資源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工作環境、福利待遇等與城鎮學校有較大差距,部分農村學校教師不能安心紮根在農村學校長期任教,而是通過調往城鎮學校等途徑離開農村,導致相對邊遠地區的一些農村學校教師數量不足。所以儘管早在1985年,教育部就取消了民辦教師,但因農村條件艱苦,招攬正式教師難度大,如今,代課教師仍在西部地區,特別是偏遠山區教育中起著推動作用。來自新華網的消息顯示,甘肅省教育部門在2011年的“兩基”迎國檢工作督查中發現,甘肅省目前仍有“代課人員”10611人。既然農村教育及農民工子弟教育暫時還離不開代課教師,就應該讓優秀的、合格的代課教師轉正;即使不給他們“名分”,也應該提高他們的待遇,以“同工同酬”為原則,讓他們的待遇與公辦教師相當。擇校費確實成為了城鎮教育領域中改善公辦教師待遇的一個現實選項。而中西部地區的代課教師,卻成為了近乎“義務奉獻”的廉價勞動力。

2001年以來,國務院統一部署實施了農村中小學危房改造、西部地區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和中西部農村初中校舍改造等工程。2009年,在汶川大地震一週年之際,國務院要求,從當年開始,用三年時間在全國範圍實施校舍安全工程,全面提升中小學校舍抗震防災能力,該工程覆蓋全國城市和農村、公立和民辦、教育系統和非教育系統的所有中小學。但是3年的大限將至,各地工程進展情況不容樂觀。不少省份完不成任務是板上釘釘之事。以廣東為例,截至今年7月,該省平均開工率僅為69%,竣工率為48%。截至目前,山東省26個縣(市、區) 未向校舍安全工程投一分錢,致使部分項目不能按時開工或長期停工。
與此同時,自1989年10月至2004年,希望工程15年間累計接受海內外捐款22億多元,資助250多萬名貧困學生上學讀書,援建希望小學9508所。許多貧困縣的領導認為,希望工程為實現“兩基”(基本實施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目標達標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包括希望工程在內的民間慈善項目,成為了教育經費的有益補充。
《義務教育法》第四十八條提到,國家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向義務教育捐贈。而按照《義務教育法》第二條的規定,“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對於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國家將義務教育全面納入財政保障範圍”,第四十四條規定,“農村義務教育所需經費,由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的規定分項目、按比例分擔”。所以,民間慈善有多麼發達,教育投入缺失就有多麼嚴重。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堅持以輸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確保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
以北京為例,目前,北京約有農民工子弟40萬人,這些孩子有一部分在公立學校讀書,有大約10萬人在150所打工子弟學校接受教育。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公益網完成的《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現狀分析報告》顯示,北京目前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除63所擁有辦學許可證外,其餘都屬於非法辦學。《北京民工子弟學校調查報告》中採集了114所北京打工子弟學校的樣本。其中42所是民辦教師所辦,5所是代課教師所辦,30所是公辦教師所辦,2所是企辦教師所辦,26所學校是非教師所辦(其中13所聘用教師講課),4所是無教師經歷但在民工子弟學校做過教師的人所辦,5所不詳。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公益網創辦人張志強認為,目前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已有一部分成為創辦人牟利的工具。不僅如此,除了少數的學校教學品質有保障,更多的打工子弟學校更像是“掃盲班”。
流動兒童研究專家、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韓嘉玲認為,義務教育應“誰用工誰買單”。義務教育經費並非中央撥付,而由省市一級地方政府承擔,具體落實是由區縣一級撥付。由中央將戶籍所在地經費轉移到居住地支付的方式很複雜,而且並不實際。地方政府切實享受勞動者提供的服務,就應該為他的家庭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義務教育至少不應該推向市場”。
現實是,北京公辦學校對於招收農民工子弟依然存在門檻。甚至存在農民工子女受到區別對待等種種問題,非但沒有解決教育公平的問題,反而會有更多新的問題。如果不能讓每一個打工子女都能獲得上學機會,是不是只能讓更多的打工子弟學校繼續存活下去?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要提倡合理膳食,改善學生營養狀況,提高貧困地區農村學生營養水準。
1997年國家頒布《中國營養改善計劃》,2001年開始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提供“兩免一補””(免雜費、免書本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並逐漸提高補助標準。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這些問題依然呈現複雜化、可操作性差的局面。
2010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組織“貧困地區寄宿制學校兒童營養改善”課題組,完成了西部四省區農村小學生的學校就餐狀況和營養問題的調查,發現學校供餐機制仍未建立,貧困農村學生營養不良問題仍然突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盧邁以印度、巴西等國的學校供餐項目為例,認為目前中國應將學生營養保障方面的立法問題應提上議事日程,政府應承擔起保障貧困學生營養的責任。
2010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已經開始撥款100億元用於“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費補助”,覆蓋了1225萬貧困寄宿生。
2011年,由鄧飛等500多名記者以及國內幾十家媒體,聯合中國社會福利教育基金會發起了“貧困山區小學生免費午餐”公募計劃,其午餐配餐參照國外的學生用餐要求,每份午飯價值3元,至今已為77所學校1萬多孩子提供了免費午餐。這直接推動了2011年10月份國家啟動實施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中央每年撥款160多億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標準為試點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普惠680個縣市、約2600萬在校學生。
免費午餐計劃被譽為“民間力量推動政府決策”的典範。它的目的,就是依靠民間的力量,探索出一種新的運作模式,包括公佈善款數量、組成監督團隊、多人校驗支出等措施,從而向政府提供了及時介入的良好時機。但而近期的台灣免費午餐貪腐事件,引發很多人對政府推行營養補助效果的質疑。聯想到11年前,由農業部牽頭,教育、衛生等七部委聯手推廣國家“學生飲用奶計劃”,結果,事故迭出,最後“學生奶”計劃幾近走樣。於是,輿論中也不乏懷疑政府過於大包大攬以至於濫用納稅人錢財的理性聲音。
對此,教育專家熊丙奇認為,政府是保障義務教育、推進教育公平的主體力量,但是,政府計劃的效率低下,以及可能出現的跑冒滴漏問題,也不容忽視。所以,政府計劃可以購買民間公益機構的公益服務,由其負責完成當地中小學貧困生的營養午餐任務。也可以引入社會力量參與監督,這其中就包括社會公益機構,以及新聞媒體。

校車問題一直困惑著我國學生安全,每次慘痛的校車事故之後,政府部門都發文件、發通知要求各地注意校車安全,2010年,我國還出臺了校車國標。2011年8月,教育部啟動全國中小學校車試點工作,將校車購置、運營維護等各項費用列入地方財政預算。
熊丙奇認為,要根治校車問題,必須把校車預算納入中央財政或者省級財政範疇,納入縣鄉財政則基本上意味著沒戲。據測算,為中小學配備安全的校車,總需費用約600億。這在2012年教育投入達到GDP4%之後,完全可以解決。
當前我國校車經營模式也是多種並存,主要有學校自營、政府購車學校經營、無政府補貼的營利性組織經營、有政府補貼的營利性組織經營等四種模式。
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報告《學校佈局調整與校車系統建設研究》提出了中國校車系統建設的路徑探索。報告指出,我國校車系統的實施,僅僅依靠單一的政府或市場機制也是不現實的,而是要採取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模式,即由政府主導,但政府的責任不是對校車運營的壟斷,而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在整個過程中起引導、管理、監督與檢查的作用。也就是説,政府出錢買服務,各運營公司通過校車系統可以獲得經常的穩定性收益,避免了承擔市場風險。當然,政府也要通過為民間組織和民間機構提供一些優惠政策,鼓勵民間組織參與校車的運營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