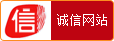從業人員超三百萬的職業生態:我們為什麼要跳街舞
一個從業人員超過三百萬的新興職業生態調查——
我們為什麼要跳街舞
翻滾、位移、踢腿、律動……儘管已經轉向幕後工作很多年,劉震宇每週都會約上幾位街舞隊友,找個場地,跳上幾段街舞。這是一群跳街舞接近20年的“老炮兒”,他們覺得,任何時候都要繼續跳舞,這早已是生命的一部分。
20年來,劉震宇經歷過不被理解的痛苦和尷尬,收穫了街舞帶來的快樂,見證著街舞從小眾逐漸走向大眾化的過程。現在,他也有了一個組織賦予的身份——安徽街舞聯盟秘書長。
眼下,劉震宇正通過組織開展選拔比賽、公益扶貧、技術培訓等活動,向青少年傳授街舞技巧和文化理念。只要聽到街舞音樂,看到孩子們跳街舞,他就立刻覺得熱血沸騰,仿佛回到了那段青春歲月。
街舞源起于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街舞登陸中國,最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流行。近年來,隨著各界的重視和街舞文化的普及,街舞社會影響力不斷攀升。
據統計,目前我國街舞從業人員已超300萬,輻射人群近千萬,大部分是青少年。相關從業者每年組織文化交流、專業賽事等活動近萬場。
曾經,街舞一度被誤解,跳街舞的年輕人曾被打上“叛逆”“壞孩子”等標簽,職業化道路上種種艱難困苦也在考驗著每一位年輕的舞者。多年來,在街舞這個行業裏,有人失敗了,也有人堅持了下來。
他們為什麼如此熱愛街舞,街舞到底帶來了什麼?近日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走進了這個新興青年群體。

街舞青年正在街舞比賽中鬥舞。受訪者供圖
兩天跳了24場舞,只為夢想
2007年,17歲的胡霄飛來到合肥,在一所職業院校就讀,他自學街舞,參加學校表演。20歲畢業時,他找到一份維修電線桿的工作,沒幾天就把工作辭了,他覺得自己還是想跳舞。
因為曾拿過學校比賽的冠軍,胡霄飛去了一家職業舞房,被安排在舞房打雜、掃地,與其他5個人一起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簡易宿舍裏。狹小的空間裏堆滿了雜物,但大夥兒每晚還是會很開心地討論舞蹈技術。
那段時間,胡霄飛經常去小鄉鎮的開業慶典,在很破的舞臺上表演。一跳一整天,6支舞,能收到80到100元的酬勞。“有一次刮大風,背景布被刮倒,砸在自己身上,腿直接卡進舞臺的窟窿……”
“這邊跳著舞,旁邊就是小商小販賣東西,環境很糟。這場剛結束,馬上換衣服去趕下一場。”胡霄飛也很無奈,他覺得,自己是迫於生計。他不願意伸手向家裏要錢,也不敢要錢。
“我們跳舞時,戴著很誇張的頭巾,有人覺得我們像混混。其實他們不知道,跳舞的人都很單純,我們只知道跳舞。”胡霄飛甚至覺得,自己只要能吃飽飯,把舞蹈練好,其他都無所謂。
2010年,胡霄飛離開舞房,來到一家酒吧跳舞。夜裏跳,早上睡覺,下午出去零散帶課,最累的時候,他兩天跳了24場舞,最後連站都站不起來,腰太疼了。
那時,胡霄飛租住在樓梯道裏隔出來的房間,僅有的傢具就是一張床和一個床頭櫃,看不見太陽。餓了就去小攤吃一碗餛飩,一年得搬家七八次。
與胡霄飛相比,劉震宇最大的壓力來自家庭的反對。他自小學習器樂,在省藝校上學時愛上了街舞。聽説他以後想走這條路,父母火冒三丈:“你再跳這個舞,以後我們什麼都不會給你,你是不會有出息的。”
2006年,劉震宇在一場鬥舞比賽中拿了冠軍,受聘到一家專業舞社教跳舞。之後,他更加拼命地練習,參加比賽取得的好成績,堅定了他將街舞當作事業的信心。
然而,2007年的一次意外,讓他左腿脛骨、腓骨斷裂。在醫院拍完片子,劉震宇問醫生,自己以後還能不能跳舞,醫生説:“能走路就不錯了!”
那一刻,他眼淚就流了出來,從那以後他天天哭,“這麼喜歡的東西一下子就沒了”。
劉震宇被送回老家康復治療,在床上躺了半年。他每天都要鍛鍊右腿和手臂力量,做俯臥撐、倒立等動作,復習一些基礎技巧,熟悉舞蹈感覺。
“世界上有很多優秀的舞者單腿跳舞,他們行,我也行!”康復期,他一直沒有放棄訓練。一年後,劉震宇可以實現一隻腿主跳,一隻腿輔助,還獨創出屬於自己的舞蹈風格,在比賽中依舊取得了好成績。

街舞公益課堂活動。受訪者供圖
街舞也是一種社交
“自己喜歡聽歌,享受音樂律動。我覺得其他的運動不像街舞那麼自由,可以無限創造動作,永遠不會覺得枯燥,一直有新鮮感。”在合肥一家媒體工作的張曉夢(化名)跳街舞五年了,每天6點下班後,她會一直跳到夜裏11點。
張曉夢介紹,舞社裏除了以跳舞為業的人,還有很多業餘愛好者,大家相處很愉快,自己有一種社交歸屬感。“舞社裏有律師、公務員、幼師、銷售等各種職業的人,大家因為跳舞聚在一起,在街舞中有所收穫,不是指金錢,而是一種精神上的收穫”。
張曉夢還認為,作為上班族,跳舞可以放鬆自己,讓生活更有趣。“上學時只是跳著玩,現在可以做兼職老師,掙的錢可以用來外出學習,這是一個良性迴圈的過程”。
平時,張曉夢會主動去上網查詢、詢問圈內人士,以了解街舞文化。“文化是舞蹈的一部分,不了解文化就談不上了解街舞。當下,街舞所代表的嘻哈文化越來越流行、時尚,被大眾所接受。”只要不耽誤上班,張曉夢就會出去參加比賽,她覺得比賽也是一種交流,能感受到自己的進步。
從事物流運輸工作的張宜生每天都會在朋友圈分享街舞小視頻。“上初中時,我就讓家人幫我報街舞班。高中時,我就想著大學要學街舞。大學開學第一天,我就在學校裏找街舞社”。
跳了5年街舞,不僅技藝在進步,張宜生覺得自己的性格也發生了變化。“跳舞需要在別人面前展現自己,可以讓人變得自信,不再內向,也間接鍛鍊了社交能力”。
“街舞帶給自己的東西很多,只有享受在其中的人才能體會。”工作後,張宜生還是堅持每天跳舞。雖然每天晚上九十點下班,他還是會去舞房跳一會兒,哪怕是一個小時,也很滿足。“這就是對街舞的執念”。
讓街舞變得陽光起來
“以前,把家裏桌子椅子挪開,就開始學習跳街舞。”2002年,鄧海涵第一次接觸街舞,就意識到自己已經選好了未來的路,甚至不想高考。“舞房的人都趕我走,不讓我進門,讓我把高考考完,再來跳舞”。
後來,鄧海涵考上了專科,但是沒去讀。2006年年初,他走上職業舞者道路,但是比賽、食宿、報名都要花錢,他卻沒有經濟來源,只好跑去服裝店上班,邊打工邊跳舞。
“像別人説的那樣,自己確實叛逆過,不愛聽家長説的話。剛接觸街舞那幾年,我覺得自己和別的孩子‘不太一樣’,除了穿著打扮,更多的是追求無拘無束的狀態,不願意接受管教。”鄧海涵回憶,很多夥伴都覺得,跳街舞的人很新潮,也很有面子。“總之,就是與眾不同”。
“不過街舞讓我學會堅持,我要把這個東西弄懂、弄透,必須要鑽下去。”這種堅持,讓鄧海涵看見了陽光。
“當街舞被更多人認識時,我們需要傳播更多正能量,編創更多中國特色文化的街舞作品,用中文流行歌曲配樂,或者加入中國元素,比如戲曲、武術。”除了跳舞,有時候鄧海涵也在思考,如何讓別人可以看到街舞中的中國色彩,讓街舞成為一張文化名片。“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年輕街舞人需要堅持,要真正了解街舞和中國文化”。
這些年的經歷也讓鄧海涵意識到,培養街舞人的社會責任感很重要。很多年輕舞者對於人際交往、社會法則都還不太熟悉,“街舞從業者能接觸很多年輕人,你能向他們呈現多少關於街舞的內涵,是你本身的綜合素質所決定的。比如一個人舞跳得非常棒,但是大字不識一個,他可能沒辦法做好推廣和傳承。”鄧海涵説。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也推動了街舞文化的傳播和普及。2018年,網路綜藝《這!就是街舞》等節目一經播出,引爆全民討論街舞的熱潮,節目中出現的新名詞“震感舞”“地板舞”被年輕人所熟知。
“現在街舞發展態勢很好,希望社會各界都能看到街舞青年積極陽光、朝氣蓬勃的一面,也希望更多熱愛街舞的青年能走上更大舞臺。”鄧海涵説。
街舞能當飯吃嗎
2005年,17歲的張博成來到合肥一個舞團學習,一學就是5年。他覺得,自己要做點事情,“給家裏人一個交代”。2012年,他向家裏要了1萬塊錢,和一個舞團合夥人在學校外開了一家工作室。
“其實就是租了學校旁邊一間50多平方米的門面,掙不了幾個錢,夠自己生活,也讓自己和朋友能有個練舞的地方,順便收點學費填平房租。”張博成説。
那時候,他和朋友一起到學校裏面發傳單,去大學裏免費表演。“給10個人發傳單,最多有兩三個人來報名,都是大學生,一學期20多節課,最多收費400多元”。
2015年,因為生意慘澹,張博成的工作室倒閉了,利用暑假,他在十幾家舞蹈機構教課,還上之前的欠債和虧損。
後來,張博成又在另一所學校對面重新開了一家培訓機構。他義務去學校社團上推廣課,給學生表演,教學生比賽技巧。他覺得,做這些並不是為了宣傳自己,就是想帶動更多年輕人學習街舞。
2013年以後,街舞培訓機構越來越多,張博成也積累了很多經營的經驗。2016年,他重整旗鼓,新開了一間300多平方米的培訓機構。
“以前的工作室裏,只有木地板、鏡子、音響。現在,文化墻、舞蹈教室等硬體設施一應俱全,舞蹈培訓也規範化、體系化、垂直化。”張博成覺得自己成了一名真正的街舞“主理人”。
在街舞行業,常見的“主理人”是指運營並管理街舞培訓機構的人,根據業內分工,還有街舞賽事助理人、街舞媒體主理人、街舞文化産業主理人、街舞影像團隊主理人等。
“招生對象很多是小學生,把小孩教好了,讓家長看到孩子的自信陽光,是自己的使命。”在張博成看來,學街舞的人越來越年輕化,自己的責任重大。
“對於主理人來説,教學是根本,是街舞推廣的重要環節。只要把教學做好,口碑就會好,街舞培訓行業也會越來越好。”張博成表示,自己會一直將街舞培訓做下去。
成為街舞“主理人”是很多街舞青年最理想的職業選擇。然而在網路上,有很多人認為,“跳街舞是吃青春飯,不是長期穩定的職業”。劉震宇對此並不認同。
“街舞是有生命線的,從學習跳舞到參加比賽,再到培訓機構老師,到賽事評委,到機構主理人,職業舞者可以一步一步成長。現在行業發展越來越好,機會也越來越多,也可以橫向發展一些相關文化産業。”劉震宇説。
“對於年輕舞者來説,首先技能和本領要過硬,才能在行業裏立足,不然可能連生活費都掙不來。”鄧海涵則認為,漫長的職業道路上,年輕的舞者需要為自己投資更多,不僅僅是金錢,還有時間和精力。
他感慨,能真正堅持下來的,一定是對這個行業極度熱愛的人。
“跳街舞,能否考大學?”劉震宇時常會接到家長的諮詢。據他介紹,中國舞蹈家協會街舞委員會推出了街舞考級制度,這讓學員有了一定的參照體系。但是,國內普通高校和藝術類院校中,專門開設街舞專業和街舞方向的還很少,如果高校能夠從普及街舞藝術教育出發,為熱愛街舞的學生開闢暢通的學歷晉陞通道,那麼街舞會與民族舞、芭蕾舞一樣,成為學生升學的專業目標。
從單打獨鬥到找到“組織”
2009年,鋼板拆除,劉震宇的腿差不多康復了。養傷期間,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未來。之後,他組建了安徽霹靂舞聯盟,希望為熱愛跳舞的青年搭建一個相互交流的平臺。
2013年,讓劉震宇和同行感到振奮的是,中國舞蹈家協會街舞委員會成立了,“協會對整個街舞群體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行業正規了,跳舞愛好者找到清晰的組織構架,大家能夠把跳舞當成事業來幹,街舞也慢慢開始市場化了。”作為協會下屬的安徽街舞聯盟秘書長,劉震宇介紹道。
“行業在發展,自己責任感也更重了。”劉震宇一直也在思考:電影明星、足球明星都很火爆,如何能將“街舞IP”越擦越亮,讓街舞行業找到新的突破口,讓街舞變得越來越家喻戶曉。
作為一個新興青年群體,街舞從業者也吸引了各級團組織的關注目光,他們為街舞青年提供學習交流、展示才華和激發創造力的平臺。劉震宇等人參加過“新時代·藝起來”公益課堂、青年街舞大賽、“築夢新時代”街舞快閃等活動,讓街舞藝術走進偏遠山區和貧困農村,被更多青少年所熟知。
今年4月,經當地團組織推薦,劉震宇和同事來到井岡山參加全國街舞聯盟骨幹“青社學堂”專題培訓班。“培訓期間,學習了三灣改編的歷史,聆聽幾位革命烈士子女的故事分享,突然覺得,創作思路被打開了,人生目標更明確了”。
課下,劉震宇帶領同組學員用街舞編排了舞蹈《飛奪瀘定橋》,將紅色主題和街舞藝術結合起來,在場的老藝術家嘆為觀止,當場提出,邀請這群年輕人在更大的舞臺上展演。
劉震宇意識到,“真正的藝術是沒有邊界的,街舞的舞臺其實可以更寬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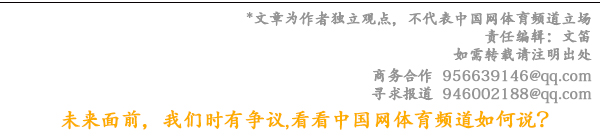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734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