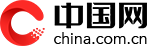姜院子內的木雕門窗
每個人的記憶都有模糊的時候,你越抽絲剝繭,想弄得一清二楚,其結果往往一塌糊塗。在縣城住了多年,現在離開它,隔了一層薄薄的時空,記憶卻像一湖靜水,驟然澄澈了。
老家叫滎經縣,名字經常被人念錯,會將“滎”字念作“Xing”,滎陽的滎。秦末漢初,劉邦項羽爭天下,兩人打累了,曾以鴻溝為界,劃定地盤。鴻溝在哪兒?就在滎陽。
但在這裡,“滎”字得念“Ying”。滎經之名是明代就有的,但在明代之前的戰國時期,就以“嚴道”的大名屹立在廣袤的川西。
川西人的性格,摻著任性與灑脫。直接的佐證是,解放前本地多袍哥,他們有句口頭禪“袍哥人家絕不拉稀擺帶”,意思是“你得耿直,關鍵時刻你不能掉鏈子,要撐住場子”。
但在平常日子裏,卻沒那麼多驚天動地。人們要生活,生活需要一個空間,而這個空間就是縣城。
打鐵街
打鐵街是個綽號。就如人一樣,從小到大,難免會被各種綽號包圍。只不過,有的綽號屬惡作劇,叫來令人厭煩,有的綽號則帶著讚美,讓人喜歡。打鐵街這綽號,應屬於後者。
打鐵街
打鐵街在滎經縣城西面,現在的路標上,這裡屬人民路西一段。但如此費事的叫一條街,不符合滎經人爽利的個性,即便時事遷移,人們也依舊稱這裡為打鐵街。
民國時,小縣處在茶馬古道要衝上,一段時期內,政府又大張旗鼓搞公路建設,不少鐵製品用量激增。一來二去,街上竟冒出多家鐵匠舖子,叮叮噹當的打鐵業,也成了整條街的産業支柱。
興盛的反義詞,必然是衰敗,打鐵街的諸多鐵匠舖就相繼衰敗了。如今,鐵匠這個詞,幾乎被冷藏,在商品化社會中,人們也不再需要鐵匠。作家莫言有篇小説叫《月光斬》,裏面有個神奇的故事——某個鐵匠家庭,父子三人為打制一把曠世寶刀而先後殞命,結果令人唏噓,故事更讓人稱奇。
我見過不少鐵匠,但從沒見他們打過什麼寶刀,刀倒是有,只不過是鐮刀,是菜刀。在打鐵街,如今只有街西頭還僅存一家鐵匠舖。主人姓朱,人稱朱鐵匠。朱鐵匠打鐵,他故去的爹也打鐵,到他兒子這代,依舊打鐵。三代人,在近百年的時間內,守著一方爐火,叮噹作響。
中國人的審美意趣,向來追求沖淡平和,蕭瑟淡遠。一身腱子肉的鐵匠,揮汗如雨的打鐵畫面,是不能引起人們關注的。歷史上,魏晉名士嵇康曾做過鐵匠,但他也沒有堅持下去。世人説到鐵匠,也只説這是世間三大最苦職業之一。長久以來,鐵匠躲在一個角落裏,為鐵器時代做著貢獻,為冷兵器的歷史奉獻汗水。他們能見諸史冊者,卻唯有歐冶子、幹將等寥寥數人。
打鐵街上僅存的一家鐵匠舖
打鐵街的鐵匠舖,靠父子二人支撐。兒子四十五六,是個黝黑的中年漢子,打鐵的活計他全包圓。老子七十開外,打鐵早沒了氣力,但嘴巧、面善,最適合去市集賣刀。每日清晨,風箱一拉,火苗竄出,“鐺鐺鐺”的打鐵聲就會準時響起。選鐵、下料、抽剛、開鋼口、加剛、磨刀……十幾道工序,上萬次捶打,一千多度的高溫,只為一把菜刀的橫空出世。
鐵匠舖的吵鬧,襯托著打鐵街的靜謐。
如今,這裡應算是一條“老人街”了,年輕人遠走高飛,只剩一堆花甲耄耋,頂著懶懶的暖陽混日子。老朱鐵匠還在忙,他騎一輛舊三輪,載一車寒光閃閃的菜刀,數十載裏風雨無阻,往來于鐵匠舖與集市間。
有人問:“您老這麼大年紀,還忙咧?”
老朱鐵匠答:“沒法子,要幹飯嘛。”
老朱鐵匠健談爽朗,打了一輩子鐵,閱刀無數,經他手鍛造的菜刀,數不勝數。有一回經過打鐵街,我問他:“手藝傳不傳?”
他冷冷一笑,啐口痰,説:“傳,傳個屁,兒子也奔五的人了,孫子去打工了。”
再問爐火旁那中年漢子,他抬頭笑笑,便只顧埋頭敲打,叮噹聲聲,嘴巴嚴嚴的,像是有心事,又像是太專注了。
打鐵街上,還有剃刀匠、修鞋匠、石匠等,一人一個故事,一人也像一本書。對於他們,你要麼一頁不翻,翻開,就被迷住了。
姜院子
在滎經縣城,姜院子的名氣能和縣醫院、電影院等齊名。不少人眼中,姜院子是個大雜院,于我來説,姜院子卻是個神秘地帶。
姜家後人
少年求學時,小學學校離姜院子僅百米之遙,每日上下學,這裡是必經地。年少無知,喜好遊戲玩鬧,往姜院子一鑽,偌大的院落,就化為捉迷藏的樂園。有次,一名同學拿了根半米長的鋼棒,威風凜凜,好不嚇人。誰料,沒過多久,竟被老師捉住。一番逼問後,同學急了,眼裏憋淚,只説是姜院子拾的,再無多話。老師聽後,大怒,並告誡全班同學,不許再去姜院子遊戲。
我至今認為,這位同學説了謊。在我印象裏,姜院子哪來的鋼棒器械。這裡住的,也都是正經人,且是上了年歲的老人。即便鋼棒是在姜院子得到,但這又與大院何干?老師的禁令,只會促使我更為好奇。
年歲逐增,姜院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從破敗大雜院中突圍,搖身一變,成了地方文化的見證,邊茶貿易的注腳。姜院子是明清古建,佔地近兩千平方米,房屋數十間,人口鼎盛時過百。這大院的主人,以製作邊茶起家,並憑著一條雅安通往藏區的茶路,奠定了一方巨富的實力。
姜家“裕興號”舊址
解放前,姜院子的光彩已然暗淡,解放後,這裡更成了一眾百姓雜居的場所。慶倖的是,姜家的故事沒有湮沒,這裡還住著一位姜家後人,名叫姜琳,他年近九旬,卻耳聰目明,談及家族往事,至今仍如數家珍。
無事時,姜琳會在院子裏曬太陽,懶懶地坐著,抬頭看看藍天,再低頭瞅瞅週遭的房舍。房舍裏,有清代的木雕門窗,天井裏,有石頭刻成的俊俏奔馬。一陣迷糊後,姜琳睏了,在夢裏,他似乎回到了八十年前,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姜家仍是縣內首富,每日制茶、販茶的工人在前院進進出出,一股清澈的茶香甘冽悠遠,至今回蕩在他的心頭。
許多年前,一條艱辛漫長的茶路穿城而過,在這條路上,有一個閃光的亮點,就是姜家大院,人們也稱為姜院子。在這僻遠的縣城,姜家曾是這裡的明星,姜琳也是這個明星家庭的小少爺。他們富甲一方,出手闊綽。他們製作的茶磚成為民族間交流的紐帶,並讓藏區同胞每日不離,為之傾倒。
即便是現在,姜院子仍是滎經縣城的重要地標。這不僅因它傳奇的過往,也源於它有著龐大的體量。在曾經逼仄的縣城內,一個老舊院落,竟能佔據如此大的空間,這是不簡單的。也因姜院子的寬闊敞亮,這裡還成了我輩少年時的常去之地。
那時的我們,天真爛漫,看到姜院子裏懸挂的牌匾,常會心生好奇,什麼“裕國興家”,什麼“光緒丁醜年”,這些辭藻一個也不知,半個也不解。二十年過去了,孩童雖長大成人,但姜院子三個字,卻牽引著我對故鄉的無盡想像。(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