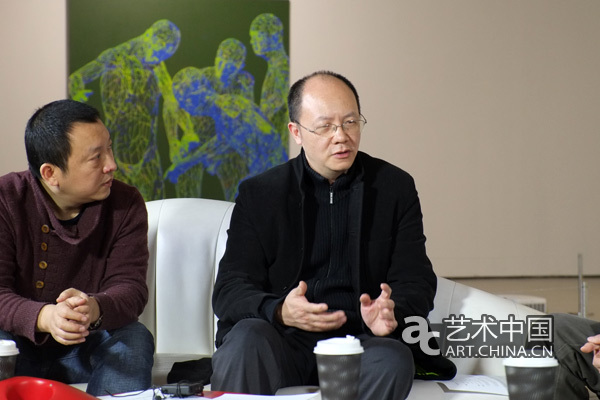
參展藝術家、中央美術學院繆曉春教授在發言中
許柏成:其實數字藝術脫離不開科技以及對於藝術思想內涵的表達,那三位老師怎麼看數字藝術裏面科技和藝術相互之間的這種平衡關係?
繆曉春:我覺得每個時代肯定有它嶄新的技術,藝術家有這樣一個責任或者義務去嘗試新的技術去做他的作品,但就像你剛才説的,技術最重要的是跟思想結合起來,要反映它最原始最根本的想法,所以我也特別喜歡那種看起來技術並不是太領先,但是還是反映了很深刻的思想的東西。就像白南準做的對著電視機的一個佛,這個技術現在看來已經很簡單了,但是這件作品給我的印象一直非常深刻,我一直覺得它是白南準最好的作品之一,很簡單的一個技術,但是實際上有非常深刻的東西在裏面,你可以做各種各樣反覆的解讀。
我們用新的媒體新的技術來做這個作品,其實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一旦這個技術過時了,你到底還有多少東西是能感動觀眾的,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大浪淘沙,幾十年或幾百年以後我們現在的這些技術,説起來都會是不值得一談的東西,但是真正能夠打動人的東西才是會留在藝術史上的。
張小濤:我補充一下,做新媒體、做數字藝術最怕的是炫技,你看這些孩子多半學完這個就去做商業去了,真正留下來做當代藝術的其實需要一種傳統的、千年不變的東西,我覺得這個是靈魂。比如説影片的這種穿透力,藝術中的人性、神性、獸性等等。我做數字媒體的時候,同時對考古特別感興趣。我做的第二個片子《迷霧》,是和重鋼、重慶的城市變遷和工業現代性以及物欲是有關聯的,在這個課題下我其實在用動畫語言數字藝術在去圍繞課題去完善。然後比如説做《薩迦》,其實是和藏傳佛教有關係,包括我現在做的這個動畫電影,其實和我當年的青春期和一個城市的這種90年代的巨變,中國社會家庭的這種,個人的這種創傷、社會巨變。我覺的有一點需要説明的是共性,其實你越掌握了技術,你越不應該炫技,比如我看老繆的“布魯蓋爾”和“最後審判”,其實他是從西方美術史裏面來的養料,為什麼用數字媒體來做這種宗教題材和美術史的內容?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不變的。甚至有時候我更願意在做數字媒體的同時看一些傳統的東西,昨天晚上我還在看牧溪、法常,包括擔當、八大,這些類古代的、很傳統的畫家,在今天你依然會很感動,我覺得這一點是不變的。
媒介永遠變,但是我覺得不變的是做數字媒體的一個課題、一個方法、一個系統。自己的體系、邏輯和語言有沒有一個比較深的脈絡,這是做數字媒體應該非常警惕的東西,否則很容易走向炫技。軟體每天都在更新,就像人不可能永遠漂亮,你會蒼老,但蒼老也可以有蒼老的味道,是另外一種境界。我覺得這種懷疑和警惕,在新媒介裏面是一個雙刃劍的地方。今年我還報了我們學校的項目,是巴蜀石刻在義大利博物館的一個項目,我也是借鑒了《薩迦》的元素,就是用考古學和新媒體的這種還原,數字藝術怎麼去探尋古代,做一些這種邊緣學科的連接,我覺得可能這些也是有一些可能性的。因為只是從本系統裏面找,我覺得非常困難,這還是一個思維的問題。
許柏成:王老師您作為一個學者和策展人您怎麼看?
王端廷:就他們剛才談的,已經談得非常的好了,技術是一個方面,藝術家永遠面對的是人的心理、生命等一些本質性的問題。一個藝術家生活在那個時代,他一定要發現和解決他那個時代所特有的問題,這個就來自於藝術家的他的修養、他的觀念、他的敏感、甚至於他的悲憫之心。他對自己的個體生命在這個時代,在這個社會中所遭到的各種各樣的遭遇,既出自個人,同時又帶有普遍性的一些精神層面的內涵的一種發掘和揭示,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就是為什麼數字技術運用在最前衛的可能是電子遊戲,但是電子遊戲為什麼不能作為人的一種精神産品來看待?就是因為它缺少一種深刻的內涵。當然我們不是説所有遊戲都是淺薄的,但是它的職責不是在於揭示人的心靈。數字藝術致力於發掘人的心理,表現人的心理,解決人的心理上的一種慰藉功能等一些問題,這是超越媒介的,是所有的藝術家都要面臨的一個問題。我想無論用什麼樣的技術手段,在這個方面做得好就能成為優秀的藝術家。
許柏成:張小濤老師的《量量曆險記》裏面,曾經有很多的場景出現馬遠夏圭,繆曉春老師剛剛提到白南準佛像和電視的作品,這種東方意識和數字藝術的這種結合是不是會産生一種很特殊的風格?
張小濤:其實這個我覺得是揮之不去的,它在你的血液裏面,不用講趣味、形式感或是對語言的迷戀,我們看到這個東西就會感動。在幾千年的文脈當中有這個線索,我覺得它是比較內在的,就像太極拳一樣綿延,就是你的思維方式。所以你看像日本的物派,它同時對西方的極簡,以及貧窮藝術、大地藝術有吸收,日本會出物派,和它的這種枯寂美學、東方美學和傳統文脈是比較一致的。我看馮夢波這一次的作品,其實也是在修正這種過度的技術化或西方化的一些新媒體概念,我覺得只要是藝術家內心是有感受的,有自己文化的源頭,就是可以的,甚至你看台灣的藝術家比我們做的更加有東方韻味。這次我在蘇州的個展,名字叫做《空影》,其實來源於我做《薩迦》那個開篇的藏傳佛教那個手印,那個陰影和空的東西。我覺得只要你在那個文化當中生長,它就像鴉片和毒素一樣,你是擺脫不掉的。我覺得這個是越到後來越擺不掉,是這個樣子的。
繆曉春:其實一開始做《虛擬最後審判》的時候,因為當時是用一個數位的模型取代了裏面所有的人物,那個時候就突然感覺面對那樣的一個畫面,因為是同一個人,沒有審判者與被審判者之間的差別,我有一種惶恐不安的感覺,他們突然變成了同一個人,同一類型的人。我最後是用佛教的眾生平等來解釋他們,你看這些人是一樣的身份,一樣的性別,最後就已經根本就沒有西方宗教裏面那種審判與被審判的差別,所以用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就接受了它,而這個完全是東方的一種哲學觀,或者是宗教裏面才有的一種東西,這是從內容上來説。第二個從形式上來説,08年的時候,在做三維動畫的時候我還有一個很大系列,就是《北京手卷》,《北京手卷》就是用數字來處理所有的拍攝的圖片來做成像國畫一樣的東西。那就是説,雖然我們沒有用筆墨紙硯,只是用軟體,但最後呈現出來的東西還完全是跟傳統藝術當中的這種東西一脈相承的。那就是説,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繼承傳統藝術,用數字化的方式來跟傳統産生一個聯繫。所以這種聯繫應該是一種內在的、一種脫不掉的一種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