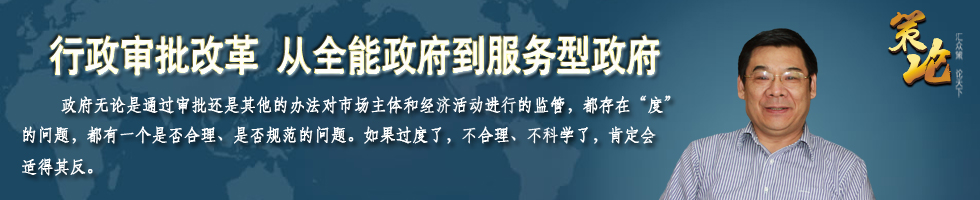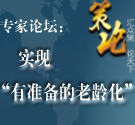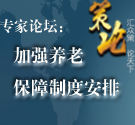輿論坐標
以論對策
監管“後置”有助釋放社會主體的能量
清理審批並不是不要監管,只不過是改變和調整了規制的方式,將一些事項的監管從前置變成後置,在釋放各類企業和社會主體能量的同時,也加大他們自我約束的責任。對那些事關社會公共利益的事項,政府還要發揮專家的作用,發揮行業自律的作用,要請他們對一些事情來設定標準,徵求意見,進行評估。 [詳細]
行政審批改革需要加強“效能監督”
目前,監察系統也參與到改革中間了,因此應該加強對行政審批效率、效果的監管,加強服務中心或者服務大廳的制度建設,通過審批效能監察進一步加大對審批改革的壓力。目前來看,最根本的就是不僅要公佈已經調整和取消的項目,還非常需要去公佈那些仍然保留下來的審批項目和今後增加的審批項目。 [詳細]
行政審批項目改革應該有張有弛
放鬆規制在我國的具體體現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但另一方面,監管和審批應該有張有弛,“張”的部分則應該保持力度,堅持社會公益守護責任。而食品安全領域就是一個需要加強的審批監管領域。此外環境和生態保護方面,以及不可再生的珍惜資源開發和利用方面,也需要加強審批監管。 [詳細]
做好制度銜接 轉型“服務型”政府
政府不能全能管理,所以也就不能進行事無巨細的審批規制,這對“政企分開”沒有絲毫好處,對政府和市場分開也同樣有害無益,否則市場經濟就難以為繼。行政審批改革,很多審批權要取消,要下放,從上面往下放,從政府裏面往外放,那麼就需要新的承接主體,而且是有承接能力的各類主體。所以,與審批改革和職能轉變相關的社會組織建設問題、社會治理機制問題,都相應進入社會管理創新的議程。 [詳細]
文字直播
中國政府網近日公佈了《國務院關於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取消和調整314項行政審批項目。對此,中國網觀點中國記者專訪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公共管理學部副主任馬慶鈺。
中國網:馬慶鈺教授,您好。這一次行政審批改革的社會背景是什麼?
馬慶鈺:總的來説,社會上有一種比較普遍的反映,説政府職能的轉變不夠到位,一直拖著計劃經濟的尾巴。雖然從1988年就提出轉變政府職能,但是一直到今天,二十多年的時間,實際上計劃經濟的味道仍然很濃,審批過多過繁就是其中主要表現之一。
所以説,適應市場經濟需要,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確實要有更加實質性的動作。那麼推進審批改革,審批項目的清理、梳理就是必不可少的。
作為一個政府,他有很多職能。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職能就是要對市場過程和社會活動進行監管,包括了對社會和市場上各種各樣的主體活動的監管,主要為了是保證市場秩序,保證經濟活動的規範,保證市場和社會過程中的公平性,保證社會消費環境的安全,總之是保證公共利益不受損傷。這種政府的職能叫做規制和監督。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不能缺少這項職責。
但是政府對市場和經濟與社會活動的規制和監管是一個過程,其中有不同的做法和手段,有的是事前控制,有的是事中的監督,有的事後的追償與懲罰。不同的做法産生的結果不一樣。而審批顯然是事前的規制和控制。大量政府管理實踐證明,傳統的行政管理時代都傾向於採用前置性審批控制的做法。而在1980年以後的全球性行政改革中,各國政府逐漸放棄以往的做法,開始更多的放鬆前置性規制,轉而採取事中監管的做法,這是政府管理中的一個新趨勢。現在的和傳統的兩種不同的規制監管做法之間,對經濟與市場的成本和效率確大不一樣。我國也受到國際社會經驗的影響,也有直接的實踐經歷。知道哪個更有利和更有效。這是一個大的背景。
中國網:過於複雜的行政審批制度,會給社會帶來了哪些負擔?
馬慶鈺:政府無論是通過審批還是其他的辦法對市場主體和經濟活動進行的監管,都存在一個“度”的問題,都有一個是否合理、是否規範的問題。如果過度了,不合理、不科學了,肯定會適得其反。第一,過分複雜的審批規制會增加審批的行政成本,給納稅人增加負擔;第二,過分苛刻的審批會把市場“統死”,會把社會的活力扼殺掉;第三,更為可怕的後果是,過多過繁的審批還會增加公共權力部門和官員尋租腐敗的機會。對經濟與社會發展來説會造成很大的損害。
中國網:為什麼監管本身很容易過度?
馬慶鈺:這與公共權力的本質特性有關係。無論是對政府部門這樣一個整體,還有對公共權力的個體持有者來講,在履行公共職能和追求公共利益中,都難免會受到自身利益的困擾,這就是所謂的“經濟人理性”影響。官員也是人,人都有自利性。而且實際情況還證明,不僅官員個人,就是權力部門作為整體,也會有追求自己的好處最多,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因此,如果在欠缺其他一些約束性、限制性、監控性條件的情況下,公共權力在使用審批權的時候,很可能就走向極端,就會出現審批過多過濫的情況,就會出現損害企業和公眾的情況。
其實很多國家在這方面都有一些教訓,包括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其社會制度在設計上應該是很現代化的,民主法制也非常健全,即便是這樣。他的規制和審批也曾經讓社會不堪重負。在1980年前後開始的全球行政改革之前,很多發達國家也一直存在很嚴重的政府管理問題,規制過剩和過分是其中之一,嚴重損害了市場和企業的活力,而且中間産生了很多“尋租”問題。比如在美國有個非常極端的例子,1975年,美國洛克菲勒旗下有一家俄亥俄石油公司,要從西海岸鋪設石油管道到東海岸,在投資立項過程中,它竟然需要經過140個部門的審批門檻,需要加蓋700個印章。這個公司努力爭取了50個月,也就是4年零2個月,每個月化100萬美元,總共花了5000萬美元,結果才得到了250個批准的蓋章。照這個速度,他們還需要努力將近8年才能過完這些關口,而且還要再花去9000萬美元。公司最終知難而退,損失巨大。
聯繫到我們國內,類似事情,也到處可見。嚴重程度也不在其下。浩繁嚴苛的審批規制幾乎無所不在,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
中國網:從這一次審批項目的取消和調整內容上來看,有哪些特點是從前沒有的?
馬慶鈺:從國務院這個層面上來講,這次取消和調整審批項目接近2500項,佔到了69.3%,對投資領域、對社會事業領域,還有對非行政審批項目進行了更加有廣度和力度的清理。顯示出政府職能轉變的決心。非常值得關注有兩個:一個是國務院這輪審批清理體現了“三個凡是”精神:凡是公民自己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社會組織行業組織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採用事後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凡是以部門規章、文件等形式違反行政許可法規定設定的行政許可,都要要限期改正。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新一輪審批清理特別注意為實體經濟、民間投資和小型微型企業發展掃清審批障礙。比如發改委下放了10億元到20億元的投資項目、200萬噸到500萬噸的專用港口泊位項目的審批許可權,商務部下放了18項涉及外商投資服務業領域的審批許可權,證監會取消了證券公司設立集合資産管理計劃計劃的審批等;比如社會事業領域,教育部對中小學教材編寫的審批、對高校研究生院的設置和撤銷的審批都予以取消,新聞出版署對刊物出增刊、廣播電視的記者採訪資格的審批都取消了,衛生部對公園、體育場館、公共交通工具的衛生許可已經取消;比如在非行政許可項目領域,發改委、農業部、水利部已經取消了商品糧基地水利工程投資計劃、組建公益性水裏工程建設項目法人的審批,林業局取消了天然林保護工程省級實施方案的審批,等等。
總的來説,將會有利於社會資本主導性和市場和社會主體的主導性,可以盤活現有資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企業、社會組織等各類法人、地方政府更加有自己的獨立性和煥發一些活力,不要統得過死。
中國網:在審批項目的調整過程中,怎樣防止走向另一個極端,出現“一放就亂”的局面?
馬慶鈺:調整審批項目確實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選擇,一些審批項目放開之後,可能會面臨一些問題。比如説中小學的教材編寫,事關教育導向和價值引領,一些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事項,涉及到是非、道德和倫理問題。要防止放開了以後出現的胡編亂造,就要把前置監督往後放。也就是説,“進門”的時候可以不管,但做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主管部門要對各類主體的行為及其後果要保持監管責任。清理審批並不是不要監管,只不過是改變和調整了規制的方式,將一些事項的監管從前置變成後置,在釋放各類企業和社會主體能量的同時,也加大他們自我約束的責任。對那些事關社會公共利益的事項,政府還要發揮專家的作用,發揮行業自律的作用,要請他們對一些事情來設定標準,徵求意見,進行評估。
中國網:在行政審批改革的落實過程中,肯定會觸及到一些人,或者一些集體的利益,阻力主要會來自哪?
馬慶鈺:監管本身是一個“瓶頸”,有“瓶頸”的地方都會有“尋租”。之前已經進行的五輪審批制度改革,一方面,看到了來自於公共權力部門自身的那種自覺性和進步性;另一方面,也存在著消極性和阻力。在政府內部自上而下還有一些差別。從中央國務院這一級來説,顯然希望大幅度推進,而且力度和決心都很大。但是到各個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那裏,情況就不一樣了,各部門有自己的審批許可權,甚至某些部門有一二十項審批權,在社會上權威有影響,大家都來買賬。現在的審批清理和改革,對這些機構部門是一種削弱,在積極性上會不一樣,有的甚至會有不同形式的消極和抵觸。總之,阻力主要來自權力部門自身。
中國網:該如何處理這些阻力?
馬慶鈺:我們現在做的還是如何推進改革的問題。一方面,這種推動力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就這次改革來講,改革由中央推行下去以後,很快在各地方政府産生了效應,比如廣東省委省政府積極跟進,在原來探索基礎上採取擴大和深入的措施,有很強的示範效應。其他的一些省份,也都紛紛進行審批項目的大規模清理,國務院也會有一些督導檢查組對改革成果進行督導檢查。
另一方面,來自於市場主體和社會的輿論也構成了強大的推動力。市場的過程本身也會對政府行為産生擠壓作用,大家的抱怨、合理訴求,市場經濟的發展等,對審批改革都會産生巨大推動作用。
最後,行政審批改革在深化行政改革中,也是主要議題之一。因此行政改革的整體推進也會不斷強化這方面的要求和內容,這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推動力。
中國網:剛才説到廣東省的一些試點地區,已經著手開始做改革了,現在效果如何?
馬慶鈺:廣東是屬於我國改革的前沿。在審批改革方面也走在前面。應該説他們的做法與市場經濟的要求是比較靠近的;而在社會上,行政審批改革的社會效果也比較好,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社會生活與經濟活動的一些要求,尤其是對社會資源的盤活,有很明顯的推進效果,對一些事業單位、社會組織、行業組織,通過審批項目的清理和改革,放鬆不該有的約束,調動各類組織法人的積極性,讓行業性組織來進行行業性自律,起到了一些內部監督、行業監管的作用,對消費者權益也發揮了保護作用,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社會管理創新。
中國網:通過試點地區的改革實踐,是否發現行政項目審批改革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馬慶鈺:現在已經做出調整的是314項審批項目,大家開始關注後面還會有些什麼項目被取消或是調整。
社會公眾已經注意到,所取消或者調整的審批項目一般與審批部門的利益大小成正比。這個大眾的主觀看法也不一定靠譜。但是確實有一定關聯性。好多取消掉的項目或者是非常過時或者是沒有存在價值。比如,放開外國人到國內來狩獵的問題,我們會發現這個項目的取消其實沒有多大意義。由此讓人們想到,對那些更具有關聯性、要害性的審批事項的改革會有更大的意義。所以應當對審批事項的放于留進行社會公開,讓大家來評價。
還有,在行政審批改革中,需要進一步加強“效能監督”。目前,監察系統也參與到改革中間來了,因此應該加強對行政審批效率、效果的監管,加強服務中心或者服務大廳的制度建設,通過審批效能監察進一步加大對審批改革的壓力。目前來看,最根本的就是不僅要公佈已經調整和取消的項目,我認為,還非常需要去公佈那些仍然保留下來的審批項目和今後增加的審批項目。
中國網:為什麼要公佈沒有放開的審批項目呢?
馬慶鈺:公佈出來方便大家評價,已經調整的這些審批項目是否有必要,已經公之於眾,其社會意義和經濟發展價值有目共睹。但是,規制和監管是一個動態拖成,因而就需要“動態調整”。有些項目撤消了,隨著環境變化和經濟方式調整,有的地方可能還需要增加審批規制。鋻於影響很大,所以要接受透明監督。
我認為,很重要的透明主要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已經調整的和取消的,這個已經公佈了,社會反響很積極;第二部分是還有一些沒有進行調整或取消,而被保留下來的;第三部分是今後需要增加的審批項目。特別是後面兩部分內容非常需要公開,只有透明和公開才能讓社會參與監督,審批才能合理。
中國網:有沒有一些行業或者領域反而應該加強審批和監督的?
馬慶鈺:監管和審批應該有張有弛,“弛”的是什麼,“張”的是什麼這個前面已經説到,而“張”的部分則應該保持力度,堅持社會公益守護責任。我認為,我們的食品安全領域就是一個需要加強的審批監管領域。此外環境和生態保護方面,以及不可再生的珍惜資源開發和利用方面,也需要加強審批監管。
中國網:這些方面的監管似乎並沒有達到讓群眾放心的程度?
馬慶鈺:在這些保持審批的領域,法律法規圈劃了幾個方面。一個是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環境安全的;再一個涉及到公共資源開發利用的;再一個涉及産品和服務提供者的資質的;還有就是有關消費安全的標準和規範的;還有一個就是企業主體資格的。我們這裡所説的食品健康衛生的監管這一塊,就涉及到消費者的安全。還有一個就是環境生態,我們現在面臨的局面也非常嚴峻,好多企業説實話講,只顧增加自己的利潤和收益,不顧對社會公眾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好處自己得或者大部分自己得,但造成的環境破壞和生態損失卻推給外面,讓國家和社會公眾給它們承擔成本,這是非常不公平的。還有一個涉及到公共資源開發裏面有些稀缺資源,特別像礦産、石油天然氣以及還有一些稀有金屬等戰略資源。在這些領域裏,我認為審批還是不要輕易放開的,需要繼續保持政府審批監管的張力。
中國網:你認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對整個的行政體制改革的意義在哪?
馬慶鈺: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攻克政府職能轉變的制高點》,我認為,行政審批改革是行政體制改革當中很重要一個內容。因為政府和社會,政府和企業,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相互之間一直存在模糊的情況,需要以行政審批改革作為“抓手”來予以界劃和澄清。政府不能全能管理,所以也就不能進行事無巨細的審批規制,這對“政企分開”沒有絲毫好處,對政府和市場分開也同樣有害無益,否則市場經濟就難以為繼。
現在不管怎麼樣,我們正在一步一步推行這個領域的清理,把一些政府不該有的管制權力拿掉,或者是逐步削弱。只要堅持這樣的理念和照此做下去,我們就離政府職能轉變的目標就一步步靠近了。如果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剩下的30%的審批項目在合理前提下在放開到20%甚至是10%,那麼可以想像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主體,市場裏各種各樣的生産者,科技經營者還有那些流通領域的經營主體,他們的活力就釋放出來了,市場經濟潛能會得到進一步的發掘。
中國網:在行政審批制度這個落實當中,除了政府在做出努力的同時,其他社會領域需要也配合跟進做哪些方面的完善?
馬慶鈺:首先,我認為,因為很多領域的行政審批權已經放開了,所以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需要進一步調整,以和審批改革對接。
其次,在政府的監察體系裏,效能監察需要跟上,去對行政審批進行監督和評估,比如我們的服務中心,服務大廳這方面就應該進一步完善,因為這是政府的一個“窗口”,這裡展示著政府的形象,這自然很重要。有一些行政審批權取消了,但是還有一些保留下來了,服務大廳審批中心這部分應該按照“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本著成本節約和物有所值的原則建設好,既不要浪費,也不要不足。
第三,要發展政府職能轉變的“二傳手”。因為行政審批改革,很多審批權要取消,要下放,從上面往下放,從政府裏面往外放。那麼就需要新的承接主體。而且是有承接能力的各類主體。比如某方面行為主體的資質管理,就需要行業組織和行業專家要有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能力。如果這樣的主體不夠,政府轉變職能的戰略目標就很難實現。所以,與審批改革和職能轉變相關的社會組織建設問題、社會治理機制問題,都相應進入社會管理創新的議程。
第四,上下級政府也有責任做好銜接工作。因為一些行政審批權的下放,從上一級政府到省級,省級又到了縣級,這個銜接也要做好,縣級政府作為審批窗口,應該合乎“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基本精神。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的行政審批改革,相對來講,肯定是越往後難度越大。迄今為止政府已經取得重要改革成果。但是社會對政府的審批清理和改革抱有很多期待。我相信十八大以後,政府在這方面一定會有進一步舉措和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