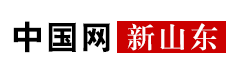

當陽光照進柴房 《宣言》響徹東方
(報告文學)
作者:徐錦庚《光明日報》( 2021年06月18日 1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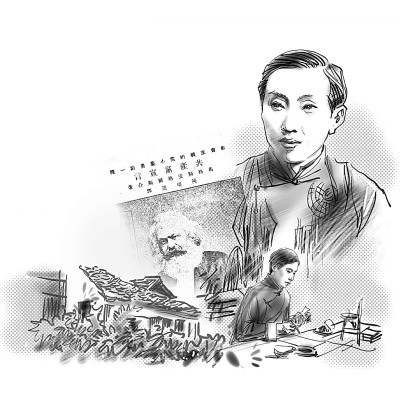
陳望道(1891—1977),浙江義烏人。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先驅,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者,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早年求學于金華中學、之江大學。1915年赴日本留學。1919年夏回國任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同時投身新文化運動。1920年翻譯出版《共産黨宣言》第一個完整的中文譯本。在復旦大學任教近五十年,1952年任復旦大學校長至去世。郭紅松繪
【中國故事】
1920年2月中旬。這天黃昏,一條杭州來的客貨混裝船,沿著浦陽江溯流而上,緩緩靠上黃宅碼頭。一個身手敏捷的年輕人,身子一縱,從船上跳下。年輕人身著長衫,留著三七分頭,眉間開闊,眼眶凹陷,鼻梁堅挺,嘴唇棱角分明,手拎一隻舊皮箱。
皮箱有些分量,年輕人換了一隻手,撩起長衫前擺,掖在腰間,邁開步伐,朝山谷快步行走。夕陽下,兩側群山一陰一陽,陰面深黛,陽面金黃。山這邊,是浦江縣。山那邊,是義烏縣。他的家鄉分水塘,就在半山腰的埡口。
這位年輕人,便是陳望道。
自我革命
一別經年,陳望道發現,家鄉雖然年味濃濃,卻掩飾不住暮氣沉沉,鄉親們眼睛渾濁空洞,舉止緩慢遲滯。是生活粗糲所致?還是這世道暗無天日,讓他們看不到希望?陳望道心裏沉甸甸的。
大半年前,有感於國內局勢混亂、國民沉淪,他激憤寫就《擾亂與進化》,發表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此時,他想,《擾亂與進化》寫的,雖是泛泛國民,何嘗不是寫自己父母,還有分水塘的父老鄉親?看來,自家的命運,分水塘的命運,是與泱泱中國的命運係在一起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浙江一師任教期間,陳望道唸唸不忘社會改造,在《校友會十日刊》撰文,呼籲廢除舊制度、改換新制度。沒想到,有朝一日,這事兒會落到自家頭上。
這天上午,陳望道正在收拾行李箱,有人在門外喊:“重陽伯在嗎?”鄉親們把陳望道的父親陳君元尊稱為“重陽伯”。
陳望道走出房門,見是一個小老頭,扶著一把鋤頭,倚在大門上,朝裏面探頭探腦,一看到他,滿臉綻出笑容:“喲,是參一啊,多年沒見,還這麼白白凈凈。”陳望道原名參一,在日本留學時改的名。
小老頭皮膚黝黑,滿臉皺紋,約莫五十開外。陳望道覺得面熟,一時想不起來,只好茫然應著,“進屋坐坐吧。”
“不了,站著就行。”小老頭有些拘謹,“不認識了?我是先塘的張水財呀。”
“哎呀,是水財哥啊,快快進來!”陳望道跨前一步,要拉張水財的手,張水財慌忙後退一步,擺擺手,“不了,不了,我還要去幹活,説幾句話就走。”
先塘村是陳望道外婆家,張水財比陳望道略大幾歲。陳望道去外婆家玩時,常跟著他上樹摘果、下河摸魚。一晃幾年不見,才30齣頭,竟衰老得不敢認了。
陳望道一把拽住張水財胳膊,用力握住他的手,這才發現,他手掌像鋼銼。
張水財趕緊抽出手:“我手上凈是灰,別弄臟了你。”
陳望道毫不介意,問道:“水財哥,你沒外出做生意?”
“做啥生意……”張水財訕訕地笑著,有些不自在,“我是你家的佃戶。”
“啊?!”陳望道大吃一驚,“你自家不是有田嗎?怎麼成我家佃戶了?”
“唉!”張水財長嘆一聲,“前幾年,為給我爸媽治病,把田都賣了。”
“這樣啊!”陳望道十分關切,“老人病治好了?”
“唉!都走了。”張水財又長嘆一聲,“我是人財兩空,只好租你家的田。”
陳望道默然片刻,忽然想起:“你找我爸有事?”
“這個……”張水財撓撓頭,面露難色,“我家孩子多,日子本來就緊巴巴。前些天,縣裏來徵丁,不去當兵的,要交徵丁稅,我家只我一個壯勞力,離不開,只能交稅。今年年成不好,稻穀歉收,這一交,谷桶就見底了,只夠勉強過個年。所以,想來向重陽伯求個情,能不能減減租。”
陳望道急忙問:“你要交多少稅?”
張水財苦著臉:“要交三成田租。”
陳望道心裏一沉。自古以來,村裏就有規矩,租佃三七分,東家得七分,佃戶得三分。佃戶糧食本來就不多,再交徵丁稅,無異於雪上加霜。想不到,苛捐雜稅這麼重,鄉親們活得這麼苦,怪不得衰老得快!他問道:“你想減多少?”
“我和幾個佃戶商量過了,想求重陽伯減兩成,這樣勉強能挨到夏收。他們抹不開面子,托我來求情。”張水財説。
“走,我領你去找我爸。”陳望道説罷,轉身在前面走。
祠堂裏,陳君元正同幾位宗親議事,看到陳望道走進來,就説:“參一啊,我們正商量祭祖的事呢,你來得正好,給出出主意。”
陳望道朝幾位長輩道一聲安,垂手對父親説:“爸,水財哥有事求您。”
張水財碎步趨前,低聲下氣地説明來意。
陳君元吸著煙,瞇著眼,沒吭聲。
“減租?”一位長輩接過話茬,“我家的佃戶也説要減租,我沒答應。交稅是按收成定的,我家交的稅更多,如果再減租,一大家子喝西北風啊?”
“我家佃戶也提了,我也沒答應。”旁邊一位長輩附和。
“小戶人家家底薄,經不起折騰。大戶人家家底厚,省著點就過去了。”陳望道人朝著父親,話説給幾位長輩聽。
“什麼話!”一位長輩不樂意了,“小家有小家的難,大家也有大家的難。自古以來,這租田交租,天經地義。租不起,可以不租嘛。”
陳望道微微一笑,不緊不慢,遞上一頂高帽子:“我問過了,以前年成不好時,老輩人也給佃戶減過租。幾位長輩都是善人,向來慈悲為懷、憐貧惜弱,老輩人的這份善心,想必也傳承下來了。”
聽了此話,幾位長輩面面相覷,一時語塞。
沉默一會兒,一位長輩脧陳君元一眼,踢過皮球:“重陽哪,你是族長,這破規矩的事,還得你拿主意。凡事得講個理兒,講個公平,對吧?七里八鄉,戶看戶、村看村,都盯著呢,不能光拍腦袋,要看看左鄰右舍。不然的話,一碗水沒端平,別人會戳脊梁骨。”
陳望道聽出話裏有話,接過話頭:“爸,三伯説得對。這是積德行善的事,如果見危不助、見死不救,別人會戳脊梁骨的。”
三伯一聽著急了,趕緊説:“我的意思是……”
陳望道打斷他的話:“三伯深明大義,教導得對,我記住了。誰家沒個急事難事?我們應該互幫互助,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能光顧自己吃肉,也要讓別人喝點湯。今後,我要向各位長輩學習,多幫幫別人,多積德行善。”
三伯幹咳一聲,尷尬地笑笑:“參一啊,你這幾年洋墨水沒白喝,我説不過你。還是讓你爸拿主意吧。”
“是,是。三伯説得是,聽我爸的。”陳望道就坡下驢,對著父親,“爸,您説呢?”
陳君元白了兒子一眼,拔出煙嘴,沉吟片刻,説:“是啊,大家説得都在理。小家有小家的難,大家也有大家的難,凡事要講個公平。我看,要不就折中一下,減一成,行不?”
幾位宗親對視了一下,不情願地點點頭:“好吧。這已經不少了。”
“爸,您看……”陳望道有些失望。
陳君元手一舉,阻止兒子往下説,轉向張水財:“你看呢?這樣行不?”
“欸,欸!好,好,我這就去告訴他們。”張水財哈著腰,轉身欲走。
“等等。”陳君元想了想,補了一句,“你家人口多,如果糧食不夠,我給你賒些,明年再扣。”
“欸,欸!那敢情好。這個年,我可以過安穩了!”張水財大喜過望,朝陳君元鞠了一躬,扛起鋤頭,樂顛顛走了。
待幾位宗親走後,陳君元朝兒子狠狠瞪一眼:“哼,這幾天,整天聽你説這革命、那革命。這下倒好,先革起老子的命來了!今後,家裏的虧空,你給填上!”説罷,一跺腳,背著手,氣呼呼地往家走。
“是,是,我來填,我來填!”陳望道吐一下舌頭,連忙跟上。
寒夜孤燈
庚申春節過後,陳望道惦記著翻譯《共産黨宣言》的事。
陳望道留日歸國後,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半年。因“一師風波”,年前憤然離開杭州,去了上海。邵力子把他介紹給戴季陶,戴季陶又引他見了陳獨秀。倆人鄭重託付他翻譯此書。戴季陶説:“別看這麼薄薄一本,要準確翻譯,難度不小。你試譯一下,譯成後,我就在《星期評論》上連載。”
要翻譯,得找個僻靜地方。哪合適呢?他轉悠到柴房,眼睛一亮,騰出一塊空地,擺上兩條長凳,擱塊木板當桌。
吃過晚飯,陳望道來到柴房,點上一盞煤油燈。漆黑的小屋,霎時光亮起來。他把英日版本《共産黨宣言》和參考資料擺在案板上。
煤油燈光昏黃搖曳,陳望道攤開兩個譯本。雖然他中文功底深厚,兼修英文和日文,留日期間大量接觸社會主義,但細細研讀後,仍感到十分棘手。這時,他才理解,為什麼戴季陶説請他“試譯”。
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讓陳望道頗費躊躇。他在紙上寫了劃,劃了寫,絞盡腦汁,反覆修改,最後敲定為:“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産主義。”
油燈下的陳望道,並沒有意識到,他鄭重寫下的這句話,在民眾心裏回蕩了數十年!直到22年後,在延安窯洞的另一盞油燈下,共産黨的理論家博古反覆推敲,才將“怪物”改為“幽靈”,把“徘徊”改作“遊蕩”。
日譯本中的漢字詞彙,陳望道沒有完全照搬。最明顯的,是對國名的翻譯。日譯本中,國名採取音譯,這是舊式譯法,他採用現代的國家名稱。有一個國名,日譯本稱“和闌”。開始,他譯作“荷蘭”,但對照英譯本,發覺不對。反覆琢磨後,他得出結論:日譯本譯錯了,正確的國名應是“丹麥”。
得益於深厚的中文功底,陳望道注重在韻律節奏、直白易懂、生動形象上下功夫。如“同業組合”“被雇職人”,他換成簡短的“行東”“傭工”;“陣營”“渣滓”“革命要素”,他換成形象的“營寨”“贅疣”“革命種子”。這麼一換,想像力和理解力大增。一些原本抽象難記的詞,如“生産機關”“社會組織”“農業的革命”,他換成具象易懂的“生産工具”“社會的狀況”“土地革命”,既易懂,也易記。特別是“土地革命”,此概念融入《共産黨宣言》思想後,使《共産黨宣言》猶如教科書,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産生直接的現實指導作用,影響廣泛而深遠。
為了體現鮮明的立場,使《共産黨宣言》更具號召力、戰鬥性,他還增加一些更為尖銳的詞彙,體現更為激烈的鬥爭立場。如,表示兩種階級對立狀態時,日譯本用的是“相敵視”,他改為“對壘”。分析資産階級發展狀況時,日譯本用的是“沒落”,他換成“傾覆”。
陳望道發現,日譯本中的一些詞彙,偏重於書面語,嚴謹有餘,不易傳播。於是,他有意識口語化。如,將“戰栗”譯為“發抖”、將“精神”譯為“智識”。現在,“智識”已很少用,“精神”倒是常見,但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智識”是個高頻詞,知識界無人不曉。
陳望道注意到,英譯本的第三人稱代詞“they,their”,日譯本卻變成第一人稱代詞“吾人,吾人の”,即中文“我們,我們的”。他心生狐疑:兩位日譯者翻譯時,為什麼要轉換人稱呢?是無意的敘事視角轉變,還是特意的立場轉換?
對兩位日譯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彥,陳望道並不陌生。他想,他們轉換人稱,絕不是無意,肯定是特意。因為,他倆都是著名的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視自己為共産黨人,使用第一人稱,更能表達立場。
“那麼,我是忠於英譯本,還是像兩位日譯者,表達鮮明立場呢?”陳望道一邊哈著氣,給凍僵的手取暖,一邊原地轉著圈,陷入深思:兩位日譯者,都是我仰慕的對象,他們信仰社會主義,視自己為共産黨人,我雖然還不是共産黨人,但他們的信仰,就是我的追求,我也應該朝這個目標前進,早日做一個共産黨人!
“對,我也要表達鮮明立場!”陳望道立刻坐下,拿起毛筆,鄭重寫下“我們”“我們的”。
早春的江南山區,春寒料峭,晚上寒氣逼人。每天晚上,家人都要給他準備兩樣東西,一是火熜,二是湯婆子。火熜暖腳,湯婆子暖手。
靠著這點溫暖,伴著不熄油燈,陳望道熬過一個個長夜,反覆推敲每一個詞、每一句話,力求既準確、又通俗。實在睏了,收攏筆墨紙硯,打開鋪蓋卷,將書案當床板。
“十大綱領”,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常被人段落翻譯。陳望道發現,日英譯本完全相同。他譯完之後,隱隱約約,總覺得不對勁。
哪不對勁呢?他一會兒站起,一會兒坐下,苦思冥想。這種感覺,若隱若現,稍縱即逝,就像空氣中有道光,他一伸手,明明抓住了,又倏然不見了。如此多次反覆,攪得他心神不寧,無法繼續進行。
“我就不信,今晚非要找到你!”陳望道發起狠來,筆一撂,起身又轉起轱轆。油燈下的身影,一會兒長,一會兒短,一會兒圓,一會兒扁。
漸漸地,窗戶開始發白,天破曉了。油燈慢慢暗淡,燈芯昏昏欲睡。陳望道忽然覺得,自己就像這根燈芯,也快熬幹了。他俯下身子,“噗”一聲,吹熄燈芯。
燈芯熄滅的一剎那,陳望道心裏,忽然冒出一束亮光:“十大綱領”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指導性,可以在實踐中照方抓藥,但在兩個譯本中,都是採取“名詞化”的敘事性翻譯,感染力和號召力都打了折扣。
“我們為什麼要翻譯《共産黨宣言》?難道僅僅是為理論研究,僅僅是宣揚政治主張?不!是為了指導行動、付諸實踐,儘快改變舊中國的面貌,改變中國人的命運!”陳望道的思緒如電閃雷鳴,似暴風驟雨,“對!應該採取‘動詞化’的施事性翻譯,把‘十大綱領’變成可複製、可實施的措施,增強其理論的行動推力,激活它的革命實踐性!”
此時,天已大亮。晨風中,飄來一陣炊煙味,肚子受不住誘惑,“咕咕”叫起來。他貪婪地吸了幾口,端坐下來,添水研墨,輕蘸墨汁,靜心屏息,筆下行雲流水。
“吱呀。”門開了,母親張翠婠拎著籃子進來,取出粽子、紅糖,擺在案桌上。
陳望道迫不及待地夾起一隻,張嘴往裏塞。張翠婠心疼地説:“慢點,蘸著糖吃,別噎著。”
過了一會兒,她在門外輕聲問:“紅糖夠不?”
屋裏回答:“夠了,夠了!”
又過一會兒,張翠婠探頭進來,小心問:“甜不?”
“甜,甜!”
張翠婠近前一看,紅糖好好的,感到奇怪:“咦,咋沒蘸紅糖?”
陳望道抬起頭來。兒子這一抬頭,把母親嚇得不輕,連退兩步:“你嘴上黑乎乎的,啥東西?”
“沒啥呀。”陳望道抹了一把嘴,“咦,怎麼儘是墨汁?”低頭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原來,自己稀裏糊塗,竟然蘸著墨汁吃粽子!
“你呀你,著魔了!”母親又好氣,又好笑。
轉眼到4月底。這天上午,當一縷陽光投進柴房時,陳望道擱下筆,長吁一口氣:終於完成了!
《共産黨宣言》問世時,馬克思30歲,恩格斯28歲。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時,比馬克思小1歲,比恩格斯大1歲。
錯印封面
一天傍晚,陳家正在吃晚飯,門外有人喊:“陳先生,陳先生,有你的電報!”
電報是星期評論雜誌社發來的,邀請陳望道去擔任編輯。他帶上譯稿,告別家人,興衝衝趕往上海,直奔星期評論雜誌社。
陳望道正欲上樓,忽然傳來男人哭聲。三樓陽臺上,圍坐著5人,哭者正是戴季陶,另外4人在勸慰。有倆人他見過,叫李漢俊、沈玄廬,是雜誌社主力。另倆人,一位面龐瘦削、梳著背頭,一位戴副眼鏡、剃著光頭。戴季陶止住哭,介紹了一番。原來是沈雁冰、李達。
坐下後,陳望道才知原委。
原來,《星期評論》創刊一年來,刊登了不少觀點激進的文章,社會各界反響熱烈,發行量有十幾萬份。當局十分忌憚,截留各地寄給編輯部的書報信件,又沒收編輯部寄出的雜誌。自47期以後,當局乾脆勒令禁止。他們正在商量,打算出滿53期後,6月6日停刊。
陳望道四下打量,過道上,角落裏,堆滿《星期評論》舊刊。他忽然想起來,打開皮箱,取出厚厚一沓稿紙,“糟糕,我的譯稿咋辦?”
“本來是要在刊物上連載。現在看來,連載是不可能了。”戴季陶接過來,瀏覽了一遍,露出讚許神情,“譯得非常好!刊物沒能連載,真是可惜了。”
李漢俊讀過大量馬克思原著,深知《共産黨宣言》的重要性,曾動過翻譯念頭,自忖中文功底不夠而作罷,聽説陳望道翻譯好了,十分吃驚,接過來,邊看邊叫好。
陳望道沒趕上編輯刊物,卻趕上給刊物收攤子,幫著李漢俊,把雜誌拿到街上,避開警察,悄悄分發給市民。待收拾停當,已是6月27日。
雜誌社編輯俞秀松,是陳望道在浙江一師的學生。晚上,陳望道找到他,把《共産黨宣言》譯稿和日、英文譯本交給他,托他帶給陳獨秀,請陳獨秀校閱把關。
俞秀松不敢怠慢,第二天上午,來到陳獨秀寓所,將譯稿鄭重交給陳獨秀。
陳獨秀看罷譯稿,連連稱好:“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基礎薄弱,沒有本像樣的理論書指導,怎麼行?這譯稿可是及時雨啊!”
他找到李漢俊:“陳望道立了大功,把《共産黨宣言》翻譯出來了,你這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好好看看,幫忙潤色潤色。”
李漢俊説:“我已經先睹為快了,只是不知如何處理。別看這本書字數不多,翻譯難度可不小,有很多新名詞,我自感力所不逮,不敢動手。望道了不起!”
“是啊,有志者,事竟成。”陳獨秀感慨不已:“你尚且知難而退,望道不事張揚,卻終成大事,就更值得欽佩了。你多費點心,幫他把把關。”
對陳望道的才學修養,陳獨秀大為讚嘆。此時,新青年雜誌社正需要編輯,他覺得陳望道堪擔重任,便邀請陳望道擔任。
1920年8月,上海共産主義小組成立,這是上海第一個共産黨組織。小組發起人共有8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楊明齋、李達,陳獨秀任書記。小組成立後,把出版《共産黨宣言》譯本列入計劃。
這天,陳獨秀約陳望道和李漢俊等人碰頭,商議出版譯本的事。
李漢俊撓撓頭:“現在局勢趨於緊張,《星期評論》也被迫停刊了,公開出版《共産黨宣言》會有麻煩。”
陳望道眉頭緊鎖:“是啊,上海的華界在軍閥統治下,租界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哪能容忍《共産黨宣言》公開印刷發行?”
李漢俊接著説:“還有一個難題,到哪籌集出版經費呢?”
“錢的事,我想辦法。”陳獨秀踱著步子,“聽説維經斯基帶來一筆共産國際經費,我找他商量。”
維經斯基是蘇共中央和共産國際代表,這年春天秘密來華。聽説要出版《共産黨宣言》中文譯本,維經斯基當即拍板:“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是我們的工作內容之一。給你們一筆經費,你們乾脆建一個印刷所,今後還要經常印資料呢。”
陳獨秀、陳望道等人立刻張羅起來,在拉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裏12號租了一間房子,秘密開設又新印刷所。
這天,陳獨秀和陳望道、李漢俊等人來到印刷所。《共産黨宣言》剛印出,散發著油墨清香。
這是一本小32開的小冊子,高18.1釐米,寬12.4釐米,封面是水紅色的,中央印有大幅馬克思半身坐像。在書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原著者:馬格斯、安格而斯;翻譯者:陳望道;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
翻開書本,裏面無扉頁,無序言,無目錄,內文共56頁,每頁11行,每行36個字,採用繁體字和新式標點,用5號鉛字豎版直排。
“哎呀,糟糕,印錯了!”眼尖的陳望道驚叫一聲。陳獨秀仔細一看,可不是嘛,封面上,印著“共黨産宣言”!
“快停下,快停下!”陳望道連忙朝印刷工人喊。可是已經晚了,500冊已經裝幀好。
“怎麼辦?毀掉重印?”幾個印刷工人慌了。
“不行!”陳獨秀搖搖頭,“我們本來就缺經費,這樣太浪費了。” 陳獨秀思忖片刻,果斷決定,“再印500冊,這批書就不要出售了,全部免費贈送。把封面重新排版,下個月再印1000冊,封面改成藍色的。”
他們並沒有料到,這一錯誤,卻為後人鑒別這個版本的《共産黨宣言》提供了鐵證。
譯本出版後,陳望道寄贈給魯迅和周作人,請他們指教。
魯迅讀後,對周作人説:“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麼‘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作者:徐錦庚,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其長篇報告文學《望道——<共産黨宣言>首部中文全譯本的前世今生》即將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共産黨宣言》傳播年表
1847年12月至1848年2月
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時撰寫《共産黨宣言》全文(德文),並於1848年2月1日完稿。
1848年2月
英國倫敦“工人教育協會”首次匿名出版《共産黨宣言》德文全文單行本,全書共23頁。4至5月,德文再版30頁本在倫敦刊行,成為後來各版本的基礎。
1872年6月
新的德文版在萊比錫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合寫了序言。此版本及其後版本都以《共産主義宣言》為名。
1905年底
朱執信(署名勢伸)在《民報》第二號上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第一次簡要介紹《宣言》的寫作背景、基本思想和歷史意義。
1919年4月
李大釗、陳獨秀主編《每週評論》第十六號“著”專欄內刊登成舍我譯《宣言》第二章最後部分及十條綱領全文。
1920年
陳望道在浙江義烏將《宣言》全譯為中文。同年8月,譯本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初版刊行。9月,該社再版,糾正了初版封面的錯誤。
1921年7月
中國共産黨成立。
1930年
上海華興書局出版華崗據英文版翻譯的英漢對照本,第一次準確譯出“全世界無産階級聯合起來!”
1936年
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談到自己1920年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時説,有3本書建立起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一本便是《共産黨宣言》。
1938年8月
成倣吾與徐冰在延安據德文版翻譯《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1943年8月
博古在成、徐譯本基礎上參照1939年俄文版加以校訂,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新譯本並在各根據地發行。
1958年至今
中央編譯局組織專家對《宣言》進行重新譯校,陸續出版多個中文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