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的圖像天地在16、17世紀經歷過一場革命。國際藝術市場誕生於安特衛普;它解開了客戶對藝術家的束縛,迫使藝術家開始就未知的地點、未知的客戶進行創作。結果,新的繪畫品類-如風景畫、靜物畫等等-得以確立。與此同時,印刷技術的發展也使得人們能夠大量複製圖像,為今日的環球化圖像文化奠下了基礎。

N° 27Rubens Lamentation on the Dead Christ

N° 1 Adriaen Brouwer

N° 40 Claerbout, Untitled

N0 53 Tuymans, Visitors gu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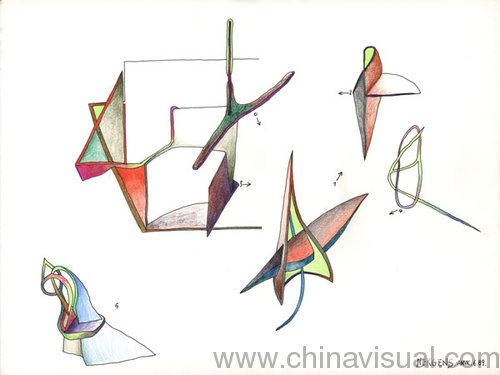
N°- 76-19 Kerckhoven, Anne-Mie, Nowhere
我們在今日的世界,能充分體驗到人被圖像淹沒的狀況。我們生活之所在,處處顯現著大眾傳媒與大眾消費。來自同一個地區的藝術家,曾經是催生大眾傳媒的重要因素,而如今他們當中卻有許多人故意與大眾傳媒拉開距離。他們針對圖像別開進路,循此探究其界限何在,引領我們對圖像産生高度意識。這些探索者跟他們在16、17世紀的先輩一樣,特別注意尋常風月、微不足道的事物,告訴我們細微得近乎不存在的東西正是一切。
倡議
安特衛普非盈利協會“新加坡-安特衛普”(新安會)
策展人
巴特·德巴爾、保羅·胡維、迪爾特·若堯斯達拉爾、赫威·陶斯
出借單位
安特衛普皇家美術館
安特衛普帕拉丁-莫瑞圖斯博物館/印刷廠
安特衛普當代美術館
總體協調
路克·德尼斯
上海美術館
李磊 -張晴 -華怡 -阮彬彬
展出地點
上海美術館(2009年5月1日至6月21日)
安特衛普當代美術館(MuHKA)館長巴特·德巴爾先生談到:“這些60及70年代“偏弱意圖”式藝術家的作品,妙處不在於延續褪除可見物象的做法-畢竟,沿這條路往下走,只會演變成概念藝術。他們實際上是突破了早期前衛派的第二個沒影點,也就是將圖像撤離早期抽象派給予它的可辨認性。20世紀初走這條路線的早期抽象藝術原本被稱為“具體藝術”,注重繪畫之舉動,即施油彩于畫布之行為的原始體驗本身,藉此傳達繪畫與現實之間的聯繫。諸如拉烏爾·德基瑟、蓋伊·米斯、楊·孫荷文等藝術家在60年代無非是將此激進化,高揚繪畫的內在性。至於傑夫·戈依斯之輩,則是在社會關係中探求同樣的內在性。
我們認為這些藝術家都是先驅人物,因為他們揭示了一點:除了諸多夢幻工廠為我們投射的圖像空間以外,我們尚有別的可能。他們的傑作顯出十足的物質性,幾乎可算是“反圖像”,或窺探角落,或望向畫作的邊緣之外。儘管大眾傳媒化現象具有苞括萬象的氣勢,促使我們以為當中涉及了所有的圖像,上述低調表現、“偏低叫牌”式的韻致卻使我們得以發現:我們其實能夠自由建構屬於自己的圖像。它的意向和衝擊力可以與主導標準不同,但仍可被稱為“圖像”。
諸如路克·圖曼斯、大衛·克拉爾博等當代藝術家正是採取這樣的姿態,將“圖像”重新設定為一種特殊的場域。場域中的主角,無非是些幾乎無法感知、只能在對圖像本身的體驗中獲得感知的東西。
我們或許可以説:今日提出這些重大圖像問題的藝術家所處的境況,類似他們當地中世紀晚期及現代早期的先輩。這些作為藝術先聲的前人被迫創設屬於自己的一套圖像體系-這在當時是可以做到的,因為那個時代有特定的世界觀,以經濟展望為推動力。到了今天,由經濟因素所驅動的極權主義式圖像大體系早已成形(而且是從過去那個體系演變過來的!),卻使得人們在世界觀的問題上變得盲目。然而,面對這樣的一個大體系,還是有人高揚個性化的亮點,就藝術的現在與過去持續開展另類可能的空間。我們在這裡正是營造了一個古今相互映照的局面。
在映照的彼此雙方之間,作為可複製機制的圖像自有它的空間,也就是夾在兩股藝術思考洪流中間的大眾傳媒空間。這兩邊各自選擇了借助感知和媒介意識來實現個性化。我們是否能夠將雙方的意向結合在一起呢?它們各自塑造意識的個性化表現,或許同樣都是最重要的貢獻,但兩邊合而為一自然也將醞釀出雙倍的力量。”
我們是有可能從這裡出發,回歸到籠罩社會的圖像空間那裏的。經此進路形成某種圖像文化,大可強化圖像在社會上的可能性,並且刺激有意識的圖像創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