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守望:一直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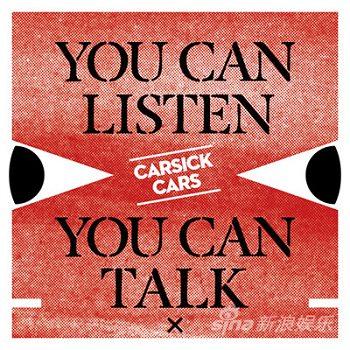
Carsick Cars新專輯《You Can Listen,You Can Talk》封面

張守望癡迷于彈琴

張守望與他心愛的吉他
(逆音 記者/趙叢 攝影/趙大寶 湯庭)“北京地下音樂——‘非北京’的驕傲是22歲的搖滾神童張守望。”美國古典音樂評論家Alex Ross在他的一篇名為《中國古典音樂的大躍進運動》的評論文章裏如是説道,“我第一次去北京D22酒吧的那晚,他表演了一首獨奏曲,穩定的嗡鳴聲之上是狡猾的極簡主義的模式,有意識地從安靜、簡單的和聲滑向陰暗的半音階領域。張守望以歷史悠久的齊柏林飛船樂隊的手法,用(他之前小心涂過樹脂的)小提琴弓演奏吉他。”
在過去的4年裏,張守望已以出眾的音樂才華及多元化的風格成為了北京新聲力量最傑出的代表。隨著今年1月他跟沈靜的WHITE組合向美國先鋒作曲家Glenn Branca致敬的第一張專輯的發行,我們知道了Maybe Noise這個由國內獨立唱片公司兵馬司成立不久的噪音子廠牌,而張守望自己作為廠牌負責人還在挖掘和發現更多的新聲音;而隨著他的搖滾樂隊Carsick Cars與嘎調樂隊一起歷時39天跨越15個城市的公路巡演——“偉大航路”的結束,我們也曾迎來過那次巡演令人激動萬分的謝幕演出以及Carsick Cars的第二張正式專輯《You Can Listen,You Can Talk》。
樂手檔案:張守望(Carsick Cars)
Carsick Cars 演出、新專輯以及成長
逆音:在那次“偉大航路”的巡演過程中,有什麼好玩或尷尬的事讓你記憶深刻?
張守望:最刺激的一次是我們在香港演完出一堆人坐巴士回賓館,我以為有人會拿我的效果器箱子,但是下車之後我問我的箱子呢然後沒人答應我,才發現箱子落在巴士上了,當時我腦子一下子就蒙了,如果箱子丟了接下來的巡演就沒法繼續。然後當地的一個朋友帶著我一起追那輛車,大概追了十分鐘最後追上了,當時跑得特別快,有點像電影情節,旺角黑夜什麼的。後來和當地人説起來,他們都覺得驚奇,因為那種巴士通常跑的很瘋狂,能追上是個奇跡。
逆音:對其中哪一站的印象最深?
張守望:其實對每站印象都挺深的,可能最深的是武漢那站,因為當時最後一首歌是跟AV大久保還有嘎調一起演了一首《I Wanna Be Your Dog》,還平生第一次“跳水”了。
逆音:然後那站之後還有類似于after party的演出,是嗎?
張守望:對,是在吳維開的Wuhan Prison(武漢監獄),特別好玩的一個小酒吧,在VOX底下。它旁邊有一古著店,裏面就是個小酒吧,你可以在上面隨便彈琴唱歌什麼的。我們在底下演了一點不插電的歌。嘎調詹盼演了好多原來哪吒的歌,小怪物去天國還有圈,我唱了自己寫的《Dead Flower》。
逆音:看到05年8月底王悅(前挂在盒子上樂隊主唱)對你們做的一個採訪,問你們最成功和開心的演出是哪次,你當初説的最成功的是向Joy Division致敬的那場,最開心的是第一次在學校公開排練,現在已經過去4年了,紀錄一定也被刷新了,現在在你看來最成功和開心的演出是哪次?
張守望:可能有點多,因為演出實在太多了。現在想成功可能就是剛剛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的音樂節,因為對於我來説它是歐洲最好的音樂節,有特別多我們特別喜歡的樂隊來演,比如Neil Young、Sonic Youth、My Bloody Valentine。要説最開心,現在回想起我們剛開始排練內會兒確實特別好玩。
逆音:在國外演出最深的感觸是什麼?你感到國內國外音樂場景甚至是文化場景最大的區別在哪兒?
張守望:其實在國外演出本質上跟在國內沒什麼差別,觀眾的反映跟國內的區別不太大,如果是好的音樂的話他們都會喜歡的。區別可能就是不管是從設備還是音樂節的服務來説都更專業一點吧,尤其各種細小的方面。比如説我們在瑞士演出,那個音樂節特別溫馨,所有音樂節的服務人員會自己做飯給我們吃,工作人員和樂隊都沒有距離。音樂場景的區別還是挺大的,在國外各種音樂類型早就有人玩過,新的樂隊如果沒有創新,很難有機會被觀眾聽到。而國內獨立音樂才剛剛起步,觀眾的欣賞層次也是有限的,這是本質的區別。
逆音:最憧憬去哪兒演出?
張守望:可能還是紐約吧,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去過那兒演出。我去過紐約兩次每次都是待了一個月,都是自己的演出,但還是希望Carsick Cars可以一起去。我們計劃十一月初會去,有可能參加CMJ音樂節。
Carsick Cars - 《You Can Listen, You Can Talk》
逆音:説説第二張專輯所呈現的氣質吧?
張守望:第一張專輯特年輕和熱血,有點不管不顧的。寫那些歌的時候是十九歲,可能有的歌都是上高中時候寫的詞,現在四五年過去了,幾個人都在成長,環境也在變,肯定新專輯的東西會更沉澱一點也更成熟。説到歌詞,我寫歌詞都是一瞬間的感受,可能每個人對歌的理解都有不同,比如説標題“You Can Listen, You Can Talk”可以去形容很多很多你身邊的事情。
逆音:封面的意思?我們討論了一下,説覺得封面是一張人臉,兩個大大的眼睛在監視著你,如果説它就是一張人臉的話,我注意到在嘴的位置是一個小叉子,其實是説你根本就沒法做到“You can listen,you can talk”的狀態,是嗎?
張守望:對,當時設計的時候有這個考慮,而且設計的時候考慮到有的人會看到有兩張臉向不同的方向看,也有一些寓意在裏面。那張專輯封面確實有一些偶然性,但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有很多種解釋。
逆音:我注意到Carsick Cars絕大多數歌都用的是第三人稱,目前我只能想到歌曲《Invisible Love》不是,這是在創作表達上的特別考慮嗎?
張守望:其實我用很多第三人稱寫歌是受魯迅的影響比較大,他很多散文或者短篇基本上都使用第三人稱。可能第三人稱對我來説更容易一點,去寫一個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比寫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更客觀。
逆音:之前聽過這麼一個説法,製作人是樂隊的另一個成員。來説説新專輯的製作人Warton Tiers吧!説説這次合作,你們交流順利嗎?
張守望:我認識Warton Tiers是因為他在美國先鋒作曲家Glenn Branca的《十三號交響》裏面打鼓,他之前也跟Glenn Branca同是Theoretical Girls樂隊的成員,他是鼓手。Theoretical Girls是我最喜歡的樂隊之一,對我影響也挺大的。我第一次見他給他聽我們第一張專輯的Demo,當時有一些溝通。他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音樂人,也參加過特別多紐約特別牛逼的樂隊的專輯製作,當時知道能跟他合作確實挺興奮的。我們錄音的時候他花了非常短的時間幫我們找到了我們想要的聲音,因為畢竟他除了是個製作人外也是個特別牛逼的音樂人,他很注重什麼是樂隊想要的,而不會把想法強加給你,整個錄音都特別順利。
逆音:跟上一張專輯相比,新專輯有哪些突破或者説是新嘗試?
張守望:有些歌裏我們加入了黑管、小提琴還有笛子,還有新專輯最後一首歌完全沒有吉他、貝司和鼓,就是風琴跟唱,對於我們來説都算是新的嘗試。另外,Warton Tiers在《Invisble Love》裏彈了鋼琴,他混音的時候在一天的盡頭里加了吉他,可能是混著混著混high了就自己加了好多吉他。
逆音:樂隊成立4年了在心態上有無變化?
張守望:最開始的時候還是像寫第一張專輯時候的心態,不管不顧什麼都不怕,因為我們就是一個新的樂隊。做第二張的時候肯定就會考慮我們能做出什麼新的東西能有什麼突破,畢竟去國外演出看了特別多好的樂隊,有一種競爭感,覺得我們能做得比其他樂隊更好,做出一些更新的東西,這是最主要的心態上的變化吧。
關於守望這個人
逆音:最早是怎麼接觸到搖滾樂的,聽的第一張搖滾專輯是什麼?
張守望:第一張我聽的是邁克爾-傑克遜,第一次買的磁帶。之後老去CD店買朴樹、張震岳、花兒什麼的,前些日子在朋友車上聽花兒覺得還能勾起些上初中時候的回憶。後來接觸的第一張國外的是Smashing Pumpkins,之後開始聽Nirvana、地下絲絨、Sonic Youth,第一次聽地下絲絨之後就覺得必須要組一個特別牛逼的樂隊。
逆音:又是什麼時候開始學吉他的?
張守望:其實大概我十四五歲時我媽送了我把吉他,之後我去新街口跟一個玩金屬的人學了兩節課,他教我彈小草什麼的,學了兩節我就不去了,因為我覺得彈吉他特別沒勁,我指的是以他那種方式,但當時他讓我覺得所有的人可能都是那麼彈的,然後我就把吉他放那兒了好幾年沒彈。再後來我聽了地下絲絨,發現吉他原來是可以這麼彈的,之後就自己琢磨也沒跟別人學。
逆音:什麼影響了你?文化、音樂、樂隊或者人?
張守望:影響我的人太多了。其實美國文化對我挺大的,不管是地下文化還是當時的垮掉的一代,還有美國的流行文化,對我影響都特別大。
逆音:除了音樂,平時還喜歡幹些什麼?
張守望:我之前比較喜歡攝影,拍一些黑白的照片。但後來因為得自己衝膠捲自己放大,花的時間實在太多了,就不拍了。
逆音:一般拍些什麼?
張守望:我特別喜歡拍建築,特別有幾何感的建築。
逆音:生在一個物質跟資訊更豐富的時代,我們得到很多東西都更容易了,比如説絕大多數專輯在網上都能下載,你怎麼看待網路下載?會不會很懷念人們平常所説的“打口碟的時代”?有時候我就會覺得,那種靠自己一點點發現的更珍貴。
張守望:可能很多人會有你這種感覺吧,但我覺得有網路還是能節省你很多時間,因為你想要的東西可以很快就能找到。有打口的時候雖然會有你説的那樣每次發現一個新東西可能會比現在更興奮一點,但是那樣花的時間會很多。而且我覺得現在樂隊靠賣CD也完全掙不了錢,網路是個特別好的平臺去推廣你的樂隊。包括這次在巴塞羅那演出,臺底有很多人會唱我們的歌,這完全就是myspace的功勞。有一個西班牙大哥,他跟台下一直唱我們的歌,演完之後他碰到我們説你們是日本最牛逼的樂隊,然後我們説我們是中國的,他也特別驚訝地説不好意思什麼的。
逆音:你在去年為北京新樂團作曲的《西直門車流燈》,這算是在新的音樂領域上的第一步,説説創作跟這首歌首演時的感受吧。
張守望:當時新樂團找我作這曲,我之所以願意去做是因為對我來説是個新的嘗試,因為以前從來沒做過類似這種把音樂寫在譜子上讓專業樂手去演奏的音樂。當時我挺興奮的,也花了特長時間買了很多書去學,了解一下到底應該怎麼做,因為之前可能我有很多的想法但沒法把它實現到譜子上,或者把它告訴給別的樂手怎麼去演奏。首演的時候挺成功的,那些樂手特別棒,也特別理解我那首曲子,我覺得當時演出的觀眾也都挺喜歡那首曲子的。
逆音:你已經先後跟Glenn Blanca、Blixa Belgard、John Mayer、Manuel Gottsching、Elliott Sharp、Alvin Curran這些大師級的先鋒音樂家或製作人有過合作了,他們之間的不同之處肯定有很多,有沒有發現他們之間共通的地方?
張守望:當然每個音樂人肯定都有特別大的不同點,但我覺得他們共通的地兒是人都特別好。包括Sonic Youth、E.N.樂隊的Blixa Bargeld和Elliott Sharp,我覺得人在某一個領域能做到一定地步,肯定人都特別好,他們明白怎麼做人,才有人格魅力。
逆音:用一句話或一個詞來分別形容一下Carsick Cars和WHITE吧。
張守望:Carsick Cars還是搖滾樂吧,畢竟那些根源的東西都是搖滾樂。WHITE,用一個詞就是實驗。
逆音:除了Carsick Cars跟WHITE兩個樂隊外,你也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吃聲音”、“先鋒音樂節”及“四把吉他”這樣的噪音即興演出,能在搖滾跟先鋒音樂中找到平衡點嗎?
張守望:我覺得他們對我來説是互相影響的。如果我只玩Carsick Cars,我可能會局限在搖滾的框架裏了,玩WHITE的時候我會有好多其他的想法,我可能會覺得這個可以用在Carsick Cars上。我覺得對於WHITE來説,形式雖然不是搖滾樂,但是是有搖滾樂的能量在裏面的。
|

